第三節(jié) 陳夢(mèng)家與《漢簡(jiǎn)綴述》
——以考古學(xué)為中心的考察
我們?cè)谇懊鎯晒?jié)已經(jīng)論及王國維、勞榦二人在簡(jiǎn)牘研究方面的成就。羅振玉、王國維合著的《流沙墜簡(jiǎn)》,開簡(jiǎn)牘研究之先河。勞榦繼之,所著《居延漢簡(jiǎn)考釋》,堪稱居延漢簡(jiǎn)研究集大成之作。但是,王國維、勞榦的簡(jiǎn)牘研究,僅局限于排比事類,與文獻(xiàn)相比勘,或者考訂某些字詞,或片斷的歷史事件,仍然沒有擺脫把簡(jiǎn)牘新材料視作歷史研究的工具的傳統(tǒng)窠臼,停留在以簡(jiǎn)證史的層次。盡管沙畹已經(jīng)認(rèn)識(shí)到了簡(jiǎn)文筆跡的相似性,王國維在《流沙墜簡(jiǎn)》的附表中曾對(duì)敦煌諸燧相當(dāng)于簡(jiǎn)上何等級(jí)的治所,作過初步的推定,馬衡也曾經(jīng)試圖用坑位來編次居延漢簡(jiǎn),但限于條件,他們只是意識(shí)到考古學(xué)在簡(jiǎn)牘研究中的重要性,并沒有完全將考古學(xué)納入簡(jiǎn)牘研究范圍之內(nèi)。只有到了陳夢(mèng)家,這種局面才得到了徹底的改變。現(xiàn)在研究者順著陳夢(mèng)家所開創(chuàng)的方法,根據(jù)原簡(jiǎn),用最新的技術(shù),重新攝影,再利用新近的考古報(bào)告及研究,校正舊釋文,出版了更完善可靠的版本,使得居延漢簡(jiǎn)對(duì)漢史研究的貢獻(xiàn)增加許多。
簡(jiǎn)牘既然屬于考古遺物,那么考古學(xué)的理論和方法也同樣適用于簡(jiǎn)牘研究,并且一旦簡(jiǎn)牘研究劃歸以考古學(xué)為中心的考察范圍,就不僅拓寬了簡(jiǎn)牘研究的深度和廣度,而且也指明了簡(jiǎn)牘學(xué)的方向,以史證簡(jiǎn),為簡(jiǎn)牘學(xué)成為一門獨(dú)立學(xué)科,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理論基石。因此可以說,陳夢(mèng)家的《漢簡(jiǎn)綴述》是簡(jiǎn)牘學(xué)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巨著。周永珍說:"如將漢簡(jiǎn)研究分作兩個(gè)階段:從本世紀(jì)初漢簡(jiǎn)大量出土到50年代末作第一階段;自60年代開始至今為第二階段。在研究方法上,從第一階段以研究單個(gè)的簡(jiǎn),擴(kuò)大到研究整冊(cè)或同類的簡(jiǎn);在研究?jī)?nèi)容上,從第一階段以文字考釋為主的研究,轉(zhuǎn)入到從屯戍檔案的角度到作全面的整理與分析;使?jié)h簡(jiǎn)的研究大大提高了一步。"[1] 而陳夢(mèng)家正是從第一階段轉(zhuǎn)到第二階段的關(guān)鍵人物。
一、《漢簡(jiǎn)綴述》:簡(jiǎn)牘學(xué)與考古學(xué)結(jié)合的典范
陳夢(mèng)家(1911-1966),祖籍浙江上虞,生于江蘇南京,著名的歷史學(xué)家、古文字學(xué)家和考古學(xué)家,畢業(yè)于中央大學(xué)法律系。他早年喜愛文學(xué),與徐志摩、聞一多等人,是"新月派"后期頗有影響的年輕詩人,出版了《夢(mèng)家詩集》、《鐵馬集》、《夢(mèng)家存詩》等專集,還編了一冊(cè)《新月詩選》,先后任西南聯(lián)合大學(xué)、清華大學(xué)教授,1952年調(diào)至中國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員。陳夢(mèng)家由研究古代的宗教、神話、禮俗而治古文字,再由古文字研究轉(zhuǎn)入古代歷史和考古學(xué)研究,在《尚書》、甲骨分期、西周銅器斷代、漢簡(jiǎn)等領(lǐng)域都有精深的造詣。除《漢簡(jiǎn)綴述》外,他還著有《尚書通論》、《殷墟卜辭綜述》、《西周銅器斷代》、《六國紀(jì)年》等多種。
陳夢(mèng)家雖然沒有受過田野考古的專業(yè)訓(xùn)練,但深知考古學(xué)對(duì)于歷史研究的重要意義。早在1937年,他與聞一多等人一起前往安陽,參觀殷墟的最后一次發(fā)掘。四十年代,他在美國講學(xué)期間,較多地領(lǐng)略了西方現(xiàn)代考古學(xué)資料的整理方法。1952年5月,陳夢(mèng)家參加了文化部組織的"雁北文物勘察團(tuán)"。這個(gè)考察團(tuán)分考古、古建筑兩組,前往山西大同云岡、渾源、李峪村和陽高等地進(jìn)行考古調(diào)查。陳夢(mèng)家任考古組組長,撰有《雁北考古旅行的收獲》,記述了這次調(diào)查的任務(wù)和收獲,即勘察了山陰放驛村古城,這是建筑在漢代屯戍哨所廢址上的金代忠州城址;調(diào)查了山陰廣武鎮(zhèn)和陽高縣古城堡的漢代將士墓、大同云岡石窟及其附近造像。收獲較大的是采集了云岡南岸及高山鎮(zhèn)、渾源縣李峪村的史前陶片與石器,還搜集了不少細(xì)石器彩陶,闡明了這一地區(qū)包含著多種不同時(shí)代的文化,證明了"西番"銅器發(fā)現(xiàn)區(qū)域很廣,包括青海、甘肅、陜西、山西北部,內(nèi)蒙、河北、東北等地區(qū),斷言狩獵銅壺作于燕和鮮虞,帶鉤師比是由胡人內(nèi)傳的。陳夢(mèng)家還引用裴文中的意見,認(rèn)為細(xì)石器文化大約是中國北方(包括長城以外的內(nèi)蒙古)的一種特殊文化,分布地域極廣,自東北沿蒙古至西北一帶均有發(fā)現(xiàn),當(dāng)發(fā)源于西伯利亞的貝爾加湖地區(qū),并指出鄂爾多斯時(shí)代似乎較晚,約當(dāng)中國歷史上商代、直到漢或更晚。[2] 1952年,院校調(diào)整后,陳夢(mèng)家被調(diào)到中國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多次去考古現(xiàn)場(chǎng)參觀,熟悉考古學(xué)的基本方法。因此,陳夢(mèng)家能夠按照考古學(xué)的要求,發(fā)揚(yáng)金石學(xué)的傳統(tǒng),推陳出新,盡可能科學(xué)地整理大量考古發(fā)掘物及非發(fā)掘出土的資料,在某些研究領(lǐng)域(如甲骨卜辭、殷周銅器、漢晉木簡(jiǎn)等),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1959年7月,武威磨咀子六號(hào)漢墓發(fā)現(xiàn)《儀禮》簡(jiǎn)冊(cè),次年6-7月間,陳夢(mèng)家被中國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派往蘭州,協(xié)助甘肅博物館整理武威出土的漢簡(jiǎn),并做進(jìn)一步的研究,寫了釋文、校記和敘論。同時(shí),他還對(duì)此墓所出的日忌、雜占簡(jiǎn)以及18號(hào)墓出土的王杖十簡(jiǎn)也做了考釋,后經(jīng)反復(fù)修改,于1962年定稿為《武威漢簡(jiǎn)》一書出版。
與此同時(shí),陳夢(mèng)家還負(fù)責(zé)《居延漢簡(jiǎn)甲乙編》的編纂工作,并以此為契機(jī),他的研究興趣遂從甲骨文、金文銅器方面轉(zhuǎn)到了漢簡(jiǎn)研究領(lǐng)域,對(duì)居延、敦煌、酒泉等地所出漢簡(jiǎn)進(jìn)行了大規(guī)模的整理和研究,其中包括對(duì)居延漢簡(jiǎn)的出土地點(diǎn)、額濟(jì)納河流域的漢代烽燧遺址的分布排列,以及簡(jiǎn)牘形制的考索。直到1966年逝世為止,他僅用了三年多的時(shí)間,共完成14 篇論文,約30萬字,5 篇已經(jīng)發(fā)表,后結(jié)集成《漢簡(jiǎn)綴述》,由中華書局1980年出版。
將歷史學(xué)、古文字學(xué)、考古學(xué)應(yīng)用于簡(jiǎn)牘研究,是陳夢(mèng)家《漢簡(jiǎn)綴述》的最大特色,尤其是與考古學(xué)的結(jié)合,標(biāo)志著簡(jiǎn)牘學(xué)科的正式形成。所謂簡(jiǎn)牘研究與考古學(xué)的結(jié)合,主要是指結(jié)合發(fā)掘報(bào)告對(duì)出土簡(jiǎn)牘內(nèi)容進(jìn)行綜合考釋時(shí),研究當(dāng)?shù)氐臍v史地理情況,這在居延等邊塞遺址出土的簡(jiǎn)牘研究中尤為重要,如對(duì)整個(gè)居延烽燧遺址的分布定位,即屬于考古學(xué)研究的范疇。陳夢(mèng)家《漢簡(jiǎn)所見居延邊塞和防御制度》,就是利用考古發(fā)掘報(bào)告所寫的杰作。這一方面與陳夢(mèng)家考古學(xué)意識(shí)密不可分,同時(shí)也是發(fā)掘報(bào)告等原始記錄陸續(xù)刊行公布的結(jié)果。由于考古技術(shù)和方法的落后,加之斯坦因等人并不是受過專門訓(xùn)練的考古學(xué)家,因此,他們?cè)谖鞅睒翘m、敦煌所獲的漢晉木簡(jiǎn)并不是按照嚴(yán)格意義上的科學(xué)考古學(xué)方法發(fā)掘的,除了記錄簡(jiǎn)牘的大致出土地點(diǎn)外,根本沒有關(guān)于層位的記載。即使斯坦因等人的考古探險(xiǎn)記錄,如《中亞與中國西陲考古記》、《亞洲腹地考古記》、《中亞古道紀(jì)行》等,譯成中文傳入中國的時(shí)間已經(jīng)很晚了。再如居延漢簡(jiǎn)是1930年中瑞西北科學(xué)考察團(tuán)在內(nèi)蒙古額濟(jì)納河流域發(fā)現(xiàn)的。這是漢代張掖郡居延、肩水兩都尉所屬邊塞的屯戍文書。這批簡(jiǎn)牘是在幾個(gè)重要地方加以試掘所獲,有的則是地面采集到的。但是,負(fù)責(zé)發(fā)掘事宜的瑞典考古學(xué)家貝格曼(Folke Bergman)沒有及時(shí)公布這批木簡(jiǎn)的發(fā)掘報(bào)告,無法確定出土地點(diǎn),因而居延漢簡(jiǎn)研究只能停留在考釋字詞等低層次上,無法深入。出土地點(diǎn)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yàn)樗c出土簡(jiǎn)牘有著必然的聯(lián)系。遺址的地理沿革、性質(zhì)用途和一切考古現(xiàn)象,是簡(jiǎn)牘文書的社會(huì)歷史背景,對(duì)于簡(jiǎn)牘的斷代、綴合及內(nèi)容的研究,意義重大。直到1956--1958年,居延漢簡(jiǎn)的發(fā)掘報(bào)告(貝格曼原稿)終于由索馬斯特羅姆(Bo Sommarstrom)編成《內(nèi)蒙古額濟(jì)納河流域考古報(bào)告》,在斯德哥爾摩出版發(fā)行。此前的1945年,貝格曼《蒙新考古報(bào)告》也公諸于世。這些原始資料的相繼問世,為居延漢簡(jiǎn)的研究指出了新方向。陳夢(mèng)家根據(jù)瑞典新出版的考古報(bào)告,并參考考古研究所從西北科學(xué)考察團(tuán)舊檔中找到的采集標(biāo)記冊(cè)及其他可以補(bǔ)充的資料,如斯坦因《中國沙漠考古記》等書和沙畹《中國古文書(斯坦因第二次所獲)》、馬伯樂(H Maspero)《中國古文書(斯坦因第三次所獲)》、孔拉第(A Canrady)《斯文·赫定在樓蘭所發(fā)現(xiàn)的中國和其他文物》以及中國學(xué)者王國維的《流沙墜簡(jiǎn)》、張鳳《漢晉西陲木簡(jiǎn)匯編》、夏鼐《新獲之敦煌漢簡(jiǎn)》、黃文弼《羅布淖爾考古記》等著作,查明了居延漢簡(jiǎn)的全部出土地點(diǎn),并以此作為重新整理居延漢簡(jiǎn)的基礎(chǔ),即后來出版的《居延漢簡(jiǎn)甲乙編》的主體部分。該書發(fā)表了照片和經(jīng)過重新修訂的釋文,同時(shí)注明了簡(jiǎn)的出土地點(diǎn)。陳夢(mèng)家親自為《居延漢簡(jiǎn)甲乙編》撰寫了兩個(gè)附錄,即(1)《居延漢簡(jiǎn)的出土地點(diǎn)與標(biāo)號(hào)》,對(duì)30個(gè)地點(diǎn)出土的漢簡(jiǎn)情況及486個(gè)標(biāo)號(hào)的歸屬作了詳細(xì)的說明;(2)《額濟(jì)納河流域烽燧述要》,有選擇地描述貝格曼考古報(bào)告的主要內(nèi)容,說明出土漢簡(jiǎn)遺址的基本情況,對(duì)張掖郡塞燧系列作了一次較有系統(tǒng)的敘述,并附以插圖和地圖。這是一種全新的研究方法。陳夢(mèng)家所完成的此項(xiàng)工作,"為用考古學(xué)方法科學(xué)地研究居延漢簡(jiǎn)準(zhǔn)備了良好的條件,使?jié)h簡(jiǎn)研究從此進(jìn)入一個(gè)新的發(fā)展階段。"[3]
陳夢(mèng)家在整理漢簡(jiǎn)的過程中,已經(jīng)注意到了考古學(xué)的作用。他特別強(qiáng)調(diào)了以下幾個(gè)問題:第一,關(guān)于出土地的問題,即遺址的布居、建筑構(gòu)造以及它們?cè)跐h代地理上的位置。他首先根據(jù)貝格曼的考察日記和索馬斯特羅姆編印的調(diào)查報(bào)告,作了《額濟(jì)納河流域障隧綜述》,然后又依據(jù)出土地排列"郵程表"和"居延候官·部候·燧次表",將候、候長、隧長三級(jí)官吏及其治所排列成表,清理出三者之間的隸屬關(guān)系。同時(shí)他還對(duì)河西四郡的設(shè)置年代、漢武帝時(shí)期障塞的設(shè)置、西漢都尉和居延地理沿革等問題,都作了詳細(xì)的探討。第二,關(guān)于年歷的問題,陳夢(mèng)家利用漢簡(jiǎn)資料排列"漢簡(jiǎn)年歷表",可以恢復(fù)西漢實(shí)際使用的歷法。第三,關(guān)于編綴簡(jiǎn)冊(cè)和簡(jiǎn)牘的尺度、制作問題。陳夢(mèng)家在整理武威儀禮簡(jiǎn)冊(cè)和王杖簡(jiǎn)冊(cè)時(shí),曾復(fù)原了九冊(cè)儀禮簡(jiǎn)和王杖詔書。他認(rèn)識(shí)到各種簡(jiǎn)牘都有一定的尺度和制作方法,而居延漢簡(jiǎn)為遺址所出,不同于武威墓葬簡(jiǎn),大多是拆散之簡(jiǎn),如同甲骨文一樣,如何綴合這些散亂無序的簡(jiǎn)牘,便成為整理者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關(guān)于甲骨綴合,陳夢(mèng)家說過:"甲骨文分裂破碎,為求文例的研究,及窺見卜辭的完整記載,甲骨綴合實(shí)為最急切、最基礎(chǔ)的工作"。[4] 簡(jiǎn)牘的綴合同甲骨類似,與考古學(xué)密切相關(guān)。陳夢(mèng)家根據(jù)內(nèi)容、年歷、出土地、尺度、木理、書體等編綴成不同的薄冊(cè),如此便可以掌握較為整齊的檔案卷宗,有利于歷史研究。第四,關(guān)于分年代、分地區(qū)、分事類研究與綜合研究的問題。陳夢(mèng)家認(rèn)為兩者不能截然分開,而是要互相利用,根據(jù)出土地點(diǎn)、年歷推測(cè)與編冊(cè)成組,有可能分地區(qū)、分年代,進(jìn)而分事類研究,但要住意不同的情況,如居延和骍馬都有屯田的記錄,但其制度卻不盡相同。前者明顯推行了代田法。居延已行與未行代田法也不盡相同。居延、肩水兩都尉所屬燧名相同而異地,都要加以區(qū)別,然后才可綜合不同年代和地區(qū)的漢簡(jiǎn),互相糾定,全面研究漢簡(jiǎn)中記載的官制、奉例、年歷、烽火制度、律法、驛傳、關(guān)郵等問題,并與文獻(xiàn)相比勘,用以了解漢代社會(huì)、經(jīng)濟(jì)、軍事諸方面的歷史。上述陳夢(mèng)家強(qiáng)調(diào)漢簡(jiǎn)研究中應(yīng)該注意的四項(xiàng),其中一、三項(xiàng)即屬于考古學(xué)的范疇,第四項(xiàng)則是方法論。"簡(jiǎn)牘學(xué)方法論,要求掌握歷史、考古、文獻(xiàn)、文檔、文字等多學(xué)科的理論方法,結(jié)合簡(jiǎn)牘實(shí)際,綜合和創(chuàng)造性運(yùn)用,形成自身的方法體系。"[5] 盡管從嚴(yán)格意義上說,他還沒有建構(gòu)一套完整而有系統(tǒng)的理論框架,但簡(jiǎn)牘學(xué)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已初具雛形。因此,《漢簡(jiǎn)綴述》標(biāo)志著簡(jiǎn)牘學(xué)科的正式形成。
其后,陳夢(mèng)家將考古學(xué)貫注到整個(gè)漢簡(jiǎn)研究之中。他利用漢簡(jiǎn)資料及實(shí)地調(diào)查所得,繪制了"額濟(jì)納河流域漢代亭障分布圖",并與遺址相結(jié)合,恢復(fù)了張掖太守轄下兩個(gè)都尉系統(tǒng)(居延、肩水)的布局及其結(jié)構(gòu)。為此,他根據(jù)不同出土地所出簡(jiǎn)分為四表:郵書表、函檢表、南書北書表和郵站表,推定七候官和兩都尉在塞上的序次及其相當(dāng)位置,訂正了《漢書·地理志》的錯(cuò)誤記載。如《漢志》在居延縣下云"都尉治,"而今考定居延都尉府在破城子,而不是居延城。因此陳夢(mèng)家說:"肩水都尉及縣,居延都尉不設(shè)于居延縣,皆西漢之制。而作《地理志》者似用較晚所行之制,故不相同。兩漢與王莽時(shí)期,邊塞的組織當(dāng)有所更易。我們所論述者既本諸漢簡(jiǎn),只能代表西漢武帝以后制。"[6] 其他如兩漢奉給制度也截然有別,西漢時(shí)曾兩度益奉,故同一等級(jí)官吏的月奉錢前后不同。而"班固《漢書·百官公卿表》所代表的,往往是班固當(dāng)時(shí)理解的西漢之制,不盡符合不同年代稍稍改易的地方,其例與《地理志》相同。"[7] 將西漢的政治制度、地理沿革當(dāng)作不斷變化的動(dòng)態(tài)來考察,而不是一成不變的靜態(tài),這正是陳夢(mèng)家漢簡(jiǎn)研究超越前人的關(guān)鍵所在。
陳夢(mèng)家漢簡(jiǎn)研究除了利用考古學(xué)知識(shí)外,還廣泛征引各種文獻(xiàn)、銅器、碑刻、封泥、印璽上的銘文加以補(bǔ)充,因此,對(duì)于西漢晚期和東漢初年的邊塞官制,提供了比較詳細(xì)的系統(tǒng)。如對(duì)漢代烽燧制度的研究,就是在王國維等人成果的基礎(chǔ)上,又根據(jù)以下材料:(1)出土于居延、敦煌和玉門的所有漢簡(jiǎn)的有關(guān)部分;(2)近人對(duì)于漢烽燧臺(tái)遺址的考察記錄;(3)《墨子·備城門》篇以下并其漢、唐間文獻(xiàn);(4)唐代的烽式和其他記載唐代烽制的文獻(xiàn)。因此,陳夢(mèng)家廣征博引,嚴(yán)密考證,所得結(jié)論能夠?qū)χT家之說有所修正和補(bǔ)充,將漢簡(jiǎn)研究提高到一個(gè)新階段。而《漢簡(jiǎn)所見居延邊塞與防御組織》一文,則將全部居延漢簡(jiǎn)中有關(guān)防御系統(tǒng)設(shè)置的記載排比類推,又征引《漢書》、《續(xù)漢書》及《漢官儀》、《漢舊儀》和《漢官七種》等大量文獻(xiàn)資料,考察了張掖郡兩都尉的結(jié)構(gòu)及其所屬,所關(guān)連的其他機(jī)構(gòu)的分布位置,并且論及了不同等級(jí)機(jī)構(gòu)官吏之間的隸屬關(guān)系,論證詳盡,無懈可擊。其他如對(duì)漢武帝設(shè)河西四郡和居延、玉門邊塞的具體年代,居延的地理沿革,玉門關(guān)和玉門縣的所在,兩漢時(shí)期全國各地建立都尉的情況,分別作了嚴(yán)密的考述。盡管某些論斷被更多的考古新材料和新的研究成果所修正,如居延城的位置、佐史、鄉(xiāng)嗇夫職權(quán)的確定、燧即火炬而非積薪說,居延都尉府在破城子等,都有值得商榷之處,但是,陳夢(mèng)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對(duì)于開創(chuàng)簡(jiǎn)牘研究的新紀(jì)元,具有重要的指導(dǎo)意義。
年代學(xué)也是考古學(xué)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漢簡(jiǎn)研究之前,陳夢(mèng)家從事甲骨文研究時(shí),曾片面地注重于文字的分析與尋求卜辭中的禮俗,后來,因?yàn)樽髁算~器斷代的工作,才覺得應(yīng)從斷代入手,全面研究卜辭,遂寫了《甲骨斷代學(xué)》四篇,后又寫作《西周年代考》、《六國紀(jì)年》等關(guān)于年代學(xué)的文章。他說:"年代是歷史的尺度,而先秦史的研究,尤須對(duì)此先有明確的規(guī)定,然后史事才可有所依附。"[8] 商務(wù)印書館1956年出版的萬國鼎編,萬斯年、陳夢(mèng)家補(bǔ)訂《中國歷史紀(jì)年表》,其中有陳夢(mèng)家根據(jù)《商殷與夏周的年代問題》而編排的比較詳細(xì)的《夏商周年代簡(jiǎn)表》與《殷年代簡(jiǎn)表》。他在"重編敘"里說:"準(zhǔn)確簡(jiǎn)明的歷史年表,不但是從事研究教學(xué)歷史、地理、考古和其他學(xué)科必要的工具書,也是文物工作者、圖書館工作者、博物館工作者、文化館工作者、編輯工作者等所不能缺少的工具書。"[9] 因此,陳夢(mèng)家將對(duì)年代學(xué)的研究與考古學(xué)、古文字學(xué)結(jié)合起來,對(duì)漢簡(jiǎn)材料作仔細(xì)的分期考訂,并得到天文歷法專家錢寶琮先生等的協(xié)助,重新推排漢代的歷譜。《漢簡(jiǎn)年歷表敘》即是漢簡(jiǎn)年代學(xué)的研究成果、。這篇文章以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的漢簡(jiǎn)為主,輔之以文獻(xiàn)記載,如宋人劉羲叟《長歷》、清代汪曰楨《歷代長術(shù)輯要》、近人陳垣《二十史朔閏表》,以及實(shí)物銘文、金石碑刻等,分作漢簡(jiǎn)年歷、漢代紀(jì)時(shí)、漢代占時(shí)、測(cè)時(shí)的儀具三節(jié),廣泛探討了漢代年表與朔閏表、兩漢歷術(shù)、漢簡(jiǎn)年歷表、漢代時(shí)刻、時(shí)辰、時(shí)分、五夜、一日之始、干支紀(jì)時(shí)以及式、日晷儀器等許多問題,對(duì)漢代施行的歷譜作了實(shí)錄的證明,即不僅限于采用歷術(shù)推步,佐以《漢書》等兩漢史料為證,而是從西北屯戍所中兩漢官文書木簡(jiǎn)以及其他金石資料,這就避免了使用文獻(xiàn)因傳抄、重印而導(dǎo)致月名和日序干支稍有訛誤的情況。因此,陳夢(mèng)家所排列出的兩漢年歷,較之前人研究,如勞榦在《居延漢簡(jiǎn)考釋》的"考證之部"中對(duì)漢代年歷問題的論列,董作賓《漢簡(jiǎn)永元六年歷譜考》所作的考證,有更大的權(quán)威性。"這種從考古學(xué)著眼,以斷代為綱,進(jìn)行全面研究的方法,也貫串在他對(duì)漢簡(jiǎn)研究的工作中。為了研究古史,還曾專門致力于年代學(xué)的研究,從夏商的積年、西周年代考,一直到六國紀(jì)年表,為研究古代史建立了一個(gè)完整的年代標(biāo)尺。"[10]
二、開辟簡(jiǎn)冊(cè)制度研究的新領(lǐng)域
簡(jiǎn)牘研究與考古學(xué)的結(jié)合還包括對(duì)古代簡(jiǎn)冊(cè)制度的綜合研究,全面總結(jié)古代簡(jiǎn)牘的制作、書寫、編連、使用方法等特征,揭示古代法令中對(duì)簡(jiǎn)牘使用制度的不同規(guī)定。如詔書、法律文書、經(jīng)籍等用簡(jiǎn)尺寸,有助于區(qū)分與利用出土簡(jiǎn)的年代和內(nèi)容。簡(jiǎn)牘作為戰(zhàn)國至魏晉時(shí)期主要的書寫材料,上承甲骨卜辭、鐘鼎銘文,下啟紙張和印刷的發(fā)明與使用,是中國文化的重要載體。"不僅中國文字的直行書寫和自右至左的排列順序淵源于此,即在紙張和印刷術(shù)發(fā)明之后,中國書籍的單位、術(shù)語以及版面上所謂"行格"形式,也是根源于簡(jiǎn)牘制度而來。"[11] 因此,陳夢(mèng)家對(duì)漢簡(jiǎn)的制作材料,經(jīng)典和其他簡(jiǎn)策的長度,簡(jiǎn)札的刮治、編聯(lián)、繕寫和削改,每支簡(jiǎn)容納的字?jǐn)?shù),簡(jiǎn)冊(cè)上的篇題、頁數(shù)和尾題,全篇寫成后的齊簡(jiǎn)和收卷,以及錯(cuò)簡(jiǎn)、標(biāo)號(hào)、書體和字形等問題,都作了詳細(xì)的研究、探討,為探究中國書籍制度的起源與發(fā)展,使簡(jiǎn)牘學(xué)成為一門獨(dú)立的學(xué)科,準(zhǔn)備了必要的條件。這與陳夢(mèng)家早年甲骨文字研究有關(guān),他在《殷墟卜辭綜述》中說:"作此書時(shí),注意到兩件事,一是卜辭文獻(xiàn)記載和考古材料的結(jié)合;二是卜辭本身內(nèi)部的聯(lián)系。"[12] 即根據(jù)字體、卜人、用材、前辭形式、稱謂、祭法和記時(shí)等方面的分析,參閱有關(guān)甲骨的出土坑位,對(duì)卜辭進(jìn)行斷代。由此看出,他所研究的對(duì)象已不是單純的甲骨文字,而是兼及甲骨品種、修治方式、背面的鉆鑿形態(tài),甚至無字甲骨了,研究方法也從文字的考釋和史料的整理,進(jìn)一步發(fā)展到以考古學(xué)為基礎(chǔ)的研究。同樣,在整理研究青銅器時(shí),陳夢(mèng)家不僅注意銘文,還觀察其形制、紋飾、功能和冶鑄技術(shù),即首先確定分期前不同時(shí)期的標(biāo)準(zhǔn)器,輯錄出土點(diǎn)及組合關(guān)系。尤為重視科學(xué)發(fā)倔所獲的成組青銅器。他根據(jù)銘文中同人、用地和同事等內(nèi)部聯(lián)系,把若干獨(dú)立的青銅器聯(lián)系起來,使分散的銘文得以在內(nèi)容上互相補(bǔ)充,前后串連,從而使金文材料變?yōu)槭妨稀j悏?mèng)家把研究甲骨文、青銅器的方法運(yùn)用到漢簡(jiǎn)之中,克服了以往的研究者均把簡(jiǎn)牘作為歷史研究工具的偏向。他們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是帶有文字的實(shí)物,擺脫不了傳統(tǒng)金石學(xué)的囿縛,因而導(dǎo)致大量無字簡(jiǎn)的棄置,這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簡(jiǎn)牘學(xué)的研究?jī)?nèi)容。而陳夢(mèng)家卻獨(dú)辟蹊徑,從文獻(xiàn)檔案學(xué)與考古學(xué)相結(jié)合進(jìn)行探索,其《從實(shí)物所見漢代簡(jiǎn)冊(cè)制度》即是對(duì)簡(jiǎn)牘本身進(jìn)行研究的突出成果。
武威磨咀子六號(hào)墓出土的竹木簡(jiǎn)多為成篇的經(jīng)書,且首尾完整不缺,葉數(shù)順接,文字清晰。陳夢(mèng)家利用這批材料,詳細(xì)而具體地考定漢代的簡(jiǎn)冊(cè)制度,彌補(bǔ)了文獻(xiàn)之缺漏,并證實(shí)了史書記載的不足或錯(cuò)誤,極大地豐富了簡(jiǎn)牘研究的內(nèi)容。例如,關(guān)于簡(jiǎn)牘的編綸,《說文》、《獨(dú)斷》僅言"二編",而從武威出土竹木簡(jiǎn)實(shí)物來看,可以有一至五道編綸,這足以彌補(bǔ)文獻(xiàn)所未及。再如簡(jiǎn)牘的書寫材料和工具,唐代以來的學(xué)者,習(xí)于紙筆之事,皆有錯(cuò)訛。唐人賈公彥在《周禮?考工記》疏中以為"古來未有紙筆,則以削刻字,至漢雖有紙筆,仍有書刀,是古之遺法也"。宋代的王應(yīng)麟在《困學(xué)紀(jì)聞》中也說:"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于方策,謂之削。"直到清末葉德輝還認(rèn)為:"大抵秦漢公牘文,多是刀刻,故《史記》稱蕭何為秦之刀筆吏。"[13] 他們都誤認(rèn)為"筆即削",將筆、削混為一談。居延、武威等地都發(fā)現(xiàn)有毛筆、丸墨,因此,簡(jiǎn)牘是用毛筆蘸墨書寫的,而絕非用刀刻的,刀則是用于削改寫錯(cuò)之文字,糾正了長期以來的謬傳。四川成都出土的"講學(xué)畫象磚"上,門生各捧竹簡(jiǎn)在下面凝神靜聽,其中有一人腰間帶了一把書刀,也是用來刻畫或刪改簡(jiǎn)上的文字。[14] 雖然此前,王國維已撰有《簡(jiǎn)牘檢署考》論及簡(jiǎn)冊(cè)制度,但此文作于王氏考釋流沙墜簡(jiǎn)之前,王國維未見簡(jiǎn)牘實(shí)物,只是以文獻(xiàn)證文獻(xiàn),因而存在不少失誤。如文中所說"上古簡(jiǎn)冊(cè)書體自用篆書,至漢晉以降,策命之書亦無不用篆者","簡(jiǎn)策之文,以刀書或以筆書"以及對(duì)不同文體用簡(jiǎn)長度的規(guī)定"秦漢簡(jiǎn)牘之長短,皆有比例存乎其間,間自二尺四寸,而再分之,三分之,四分之,牘則自三尺(槧),而二尺(檄),而尺五寸(傳信),而一尺(牘),而五寸(門關(guān)之傳)。一均為二十四之分?jǐn)?shù),一均為五之倍數(shù),此皆信而不征者也。"[15] 等,驗(yàn)之于實(shí)物,都是片面甚或是錯(cuò)誤的。陳夢(mèng)家則是在整理武威《儀禮》簡(jiǎn)的基礎(chǔ)上寫成的,他根據(jù)出土實(shí)物,試圖復(fù)原簡(jiǎn)冊(cè)的原貌,并附述其對(duì)于后世書籍制度的影響。較之馬衡《中國書籍制度變遷之研究》,又前進(jìn)了一步,對(duì)了解中國書籍制度的起源和演變,幫助極大。陳夢(mèng)家對(duì)簡(jiǎn)冊(cè)制度的研究,是簡(jiǎn)牘學(xué)史上的一場(chǎng)革命,也是簡(jiǎn)牘研究的發(fā)展方向。
陳夢(mèng)家學(xué)識(shí)淵博,文思敏捷,加上具有詩人的想像力,深厚的古文字功底,對(duì)考古學(xué)的熟諳,使得他在漢簡(jiǎn)研究中能夠采用多學(xué)科、多角度、交叉研究的方式,綜合歷史學(xué)、古文字學(xué)、考古學(xué)等學(xué)科優(yōu)勢(shì),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陳夢(mèng)家有很深的體會(huì):"除了方法是最主要的以外,工具和資料是研究古文的首要條件。在工具方面,沒有小學(xué)的訓(xùn)練就無法讀通古書,無法利用古器物上的銘文;沒有版本學(xué)和古器物學(xué)的知識(shí)就無從斷定我們所采用的書本和器物的年代;沒有年代學(xué)、歷法和古地理作骨架,史實(shí)將無從附麗。"[16] 陳夢(mèng)家對(duì)中國古代文物有著一種特殊的情感,40年代在美國講學(xué)期間,他歷經(jīng)艱難、千方百計(jì)地搜集流失在海外的中國青銅器資料,拍攝器形照,并附銘文,記錄尺寸,考查器物的來源,匯集成《流散美國的中國銅器集錄》一書,選錄商周青銅禮器845器,并對(duì)同類的禮器作分型編排。該書資料來源包括各博物館、圖書館、大學(xué)和古董商等公私收藏,表現(xiàn)了赤誠的愛國熱情和執(zhí)著的求實(shí)精神。正是這種強(qiáng)烈的愛國情懷促成他在新中國建立后不久,拋棄優(yōu)裕的生活條件,毅然返回祖國。
關(guān)于搜求之辛苦,他的夫人趙蘿蕤充滿感情地記述道:"他遍訪美國藏有青銅器的人家、博物館、古董商,然后回到芝加哥大學(xué)的辦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資料,打出清樣。就是這樣,周而復(fù)始:訪問,整理,再訪問,再整理。凡是他可以往返的藏家,他必定敲門而入,把藏器一一仔細(xì)看過,沒有照相的照相,有現(xiàn)成照片的記下盡可能詳盡的資料。不能往返的,或路途遙遠(yuǎn)的,或只藏一器的,他寫信函索,務(wù)必得到他需要的一切。……他當(dāng)然也造訪了紐約的所有擁有銅器或銅器資料的古董商,如盧芹齋和其他國籍不同的古董商人,也訪問了美國各地藏有銅器的博物館。只要有可能,他就要把每一件銅器拿在手里細(xì)細(xì)觀察,記下必要的資料。逗留在博物館的時(shí)候,他也順便收集各館的印有中國文物或其他藏品的圖冊(cè)。他和所有藏家、古董商、博物館幾乎都有通信關(guān)系,并留有信件的存底。"[17] 但是在1963年由科學(xué)出版社出版時(shí),由于種種原因,該書并未署陳夢(mèng)家的名字,而是署中國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書名也改為《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青銅器集錄》。
不幸的是,1957年,陳夢(mèng)家被錯(cuò)劃成右派,受到嚴(yán)格管制,政治上的打擊并沒有使他中止學(xué)術(shù)研究,相反,他的漢簡(jiǎn)研究即是在其身心受到迫害、失去自由的情況下完成的。1960年,他前往蘭州整理武威出土漢簡(jiǎn),需要進(jìn)行臨摹、綴合、校刊等技術(shù)性工作,任務(wù)艱巨,但物質(zhì)條件十分困難。時(shí)值盛夏,陳夢(mèng)家在一間倉庫樣工房里工作,不分上下班,晚上還在燈光下用放大鏡俯身看簡(jiǎn),同時(shí)他還承負(fù)著不能個(gè)人發(fā)表文章,不能對(duì)外聯(lián)系的精神壓力,更是說明了他對(duì)待學(xué)問的勤奮與執(zhí)著精神。徐蘋芳高度評(píng)價(jià)了陳夢(mèng)家漢簡(jiǎn)研究成就:"陳夢(mèng)家先生原治甲骨卜辭和金文銅器,1960年起研究漢簡(jiǎn),從研究武威儀禮簡(jiǎn)開始,進(jìn)而研究居延漢簡(jiǎn),主要是結(jié)合考古學(xué)的發(fā)現(xiàn)探討居延邊塞組織和烽燧的分布,對(duì)烽燧制度、居延史地、漢簡(jiǎn)歷譜等都作過研究,僅用三、四年的時(shí)間便撰寫了十四篇漢簡(jiǎn)論文。"[18]
以上三節(jié)分個(gè)案研究的形式,對(duì)王國維、勞榦、陳夢(mèng)家三人的漢晉木簡(jiǎn)研究成就及方法作了概括性的說明。下面六節(jié)以專題討論的形式,分《從秦簡(jiǎn)看秦代的歷史地位》、《簡(jiǎn)帛的發(fā)現(xiàn)與楚文化研究》、《郭店楚簡(jiǎn)與先秦學(xué)術(shù)思想》、《漢簡(jiǎn)所見西北地區(qū)的交通運(yùn)輸及其相關(guān)問題》、《出土簡(jiǎn)帛與文學(xué)史研究》、《漢代邊塞吏卒的文化教育和娛樂活動(dòng)》、《從出土文物看秦漢時(shí)期的民間信仰》七部分,對(duì)70年代以來簡(jiǎn)牘和帛書的發(fā)現(xiàn)對(duì)于學(xué)術(shù)發(fā)展所起的促進(jìn)作用,做詳細(xì)闡述。事實(shí)上,簡(jiǎn)帛所蘊(yùn)涵的價(jià)值遠(yuǎn)非上述列舉的這幾個(gè)專題所能概括的,尚有待于進(jìn)一步發(fā)掘。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簡(jiǎn)牘和帛書的出土數(shù)量的增多,必將對(duì)學(xué)術(shù)的發(fā)展起更大的推進(jìn)作用。
注釋
[1] 周永珍:《陳夢(mèng)家》,收入《當(dāng)代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名家》,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1989年,第468頁。
[2] 參見傅振倫:《蒲梢滄桑·九十憶往》, 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 1997年,第183--186頁。
[3] 王世民:《陳夢(mèng)家》,收入《中國史學(xué)家評(píng)傳》(下冊(c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706頁。
[4] 陳夢(mèng)家:《甲骨綴合編?序》,修文堂,1956年。
[5] 初世賓:《簡(jiǎn)牘研究與考古學(xué)方法之運(yùn)用》, 第一屆簡(jiǎn)帛學(xué)術(shù)討論會(huì)提交論文,1999年。
[6] 陳夢(mèng)家:《漢簡(jiǎn)考述》,收入《漢簡(jiǎn)綴述》,中華書局,1980年,第25頁。
[7] 陳夢(mèng)家:《漢簡(jiǎn)所見奉例》,收入《漢簡(jiǎn)綴述》,第146頁。
[8] 陳夢(mèng)家:《西周年代考自序》,收入《尚書通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11頁。
[9] 萬國鼎編,萬斯年、陳夢(mèng)家補(bǔ)訂:《中國歷史紀(jì)年表》,中華書局,1978年。
[10] 周永珍;《懷念陳夢(mèng)家先生》, 《考古》 1981年第5期,第474頁。
[11] 錢存訓(xùn):《印刷發(fā)明前的中國書和文字記錄》,印刷工業(yè)出版社, 1988年,第59頁。
[12] 陳夢(mèng)家:《殷墟卜辭綜述》,中華書局 ,1988年,第1頁。
[13] 葉德輝:《書林清話》,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頁。
[14] 重慶博物館編:《重慶市博物館藏四川漢畫像磚選集》,文物出版社,1957年,第20頁。
[15] 王國維:《簡(jiǎn)牘檢署考》,收入《王國維遺書》第九冊(cè) ,上海古籍書店, 1983年。
[16] 轉(zhuǎn)引自周永珍:《懷念陳夢(mèng)家先生》 ,《考古》 1981年第5期.,第474頁。
[17] 趙羅蕤:《憶夢(mèng)家》,《新文學(xué)史料》第三輯,轉(zhuǎn)引自王世民:《〈關(guān)于嗣子壺〉后記》,《文物天地》1997年第2期,第21頁。
[18] 徐蘋芳:《漢簡(jiǎn)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1993年第6期,第58--59頁。
出處:學(xué)苑出版社郭強(qiáng)先生提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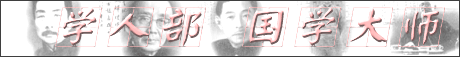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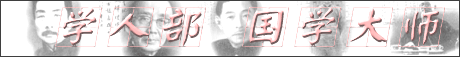

mailto:guoxue@guoxue.com
![]() 010-68900123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