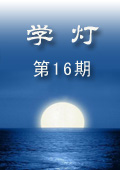
《學(xué)燈》2010年第4期(總第16期)
主 編:李銳 朱清華
周 期:季刊
出版時(shí)間:2010年12月
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與漢字革命
王志平
(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語(yǔ)言研究所)
一、啟蒙思想下的“漢字改革”運(yùn)動(dòng)(1918—1928)
1.錢玄同的“廢除漢字論”
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提出了“文學(xué)革命”的口號(hào),進(jìn)而引出了“漢字革命”的主張。“漢字革命”的緣起要從錢玄同的“廢除漢字論”說(shuō)起。
1918年,錢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號(hào)上發(fā)表《中國(guó)今后之文字問(wèn)題》一文,首先提出:“欲廢孔學(xué),不得不先廢漢文;欲驅(qū)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
他認(rèn)為,“中國(guó)文字衍形不衍聲,以致辨認(rèn)書寫極不容易,音讀極難正確。這一層近二十年來(lái)很有人覺悟;所以創(chuàng)造新字,用羅馬字拼音等等主張,層出不窮。”
他試圖從學(xué)理上證明漢字的缺陷:“中國(guó)文字,論其字形,則非拼音而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識(shí),不便于寫;論其字義,則意義含糊,文法極不精密;論其在今日學(xué)問(wèn)上之應(yīng)用,則新事新理新物之名詞,一無(wú)所有;論其過(guò)去之歷史,則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為記載孔門學(xué)說(shuō)及道教妖言之記號(hào)。此種文字,斷斷不能適用于二十世紀(jì)之新時(shí)代。”“欲使中國(guó)不亡,欲使中國(guó)民族為二十世紀(jì)文明之民族,必須廢孔學(xué),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xué)說(shuō)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
廢掉漢文之后,錢玄同主張采用文法簡(jiǎn)賅,發(fā)音整齊,語(yǔ)根精良的人造語(yǔ)Esperanto(世界語(yǔ))來(lái)代替漢文。由于Esperanto尚在提倡之時(shí),漢語(yǔ)又一時(shí)難以馬上消滅,在過(guò)渡時(shí)期,可用外國(guó)文字,如英文、法文作為國(guó)文的補(bǔ)助。而國(guó)文則限制字?jǐn)?shù),多則三千,少則兩千。
2.學(xué)術(shù)淵源及觀點(diǎn)回應(yīng)
其實(shí),“廢除漢字”的激進(jìn)思想也是其來(lái)有自。據(jù)錢玄同自己后來(lái)說(shuō),他主張文字改革,推行Esperanto(世界語(yǔ)),是受到了李石曾、吳稚暉、褚民誼等人的影響。這些人在巴黎創(chuàng)辦《新世紀(jì)》雜志,宣傳無(wú)政府主義,鼓吹進(jìn)化論。他們也主張“文字革命”:“棄中國(guó)之野蠻文字,改習(xí)萬(wàn)國(guó)新語(yǔ)(即世界語(yǔ))之尤較良文字”。“象形、表意之文必代之以合聲之文,此之謂文字革命。”他們宣稱,“從進(jìn)化淘汰之理,則劣器當(dāng)廢,欲廢劣器,必先廢劣字。”(李石曾)“漢字之奇狀詭態(tài),千變?nèi)f殊,辨認(rèn)之困難,無(wú)論改易何狀,總不能免。此乃關(guān)于根本上之拙劣。所以我輩亦認(rèn)為遲早必廢也。”(吳稚暉)錢玄同在文章中還引用了吳稚暉的原話,斷言“中國(guó)文字,遲早必廢”。
對(duì)于錢玄同“廢除漢字”,采用世界語(yǔ)的激烈主張,陳獨(dú)秀、胡適先后撰文回應(yīng)。陳獨(dú)秀質(zhì)疑錢玄同說(shuō),“僅廢中國(guó)文字乎,抑并廢中國(guó)言語(yǔ)乎?”他認(rèn)為,漢語(yǔ)與漢字性質(zhì)不同,漢字可以廢除,但漢語(yǔ)不可以廢除。“惟有先廢漢文,且存漢語(yǔ),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胡適“極贊成”陳獨(dú)秀的辦法,認(rèn)為“凡事有個(gè)進(jìn)行次序。我以為中國(guó)將來(lái)應(yīng)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單音太多,決不能變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須選用白話文字來(lái)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話的文字變成拼音的文字。至于將來(lái)中國(guó)的拼音文字是否即用羅馬字母,這另是一個(gè)問(wèn)題。”
當(dāng)然,也有贊同錢玄同的。1918年,錢玄同在《新青年》五卷五號(hào)上發(fā)表了《渡河與引路》一文,文后附錄的唐俟(魯迅筆名)通信說(shuō):我是贊成Esperanto(世界語(yǔ))的,“要問(wèn)贊成的理由,便只是依我看來(lái),人類將來(lái)總當(dāng)有一種共同的言語(yǔ),所以贊成Esperanto。至于將來(lái)通用的是否Esperanto,卻無(wú)從斷定。大約或者便從Esperanto改良,更加圓滿;或者別有一種更好的出現(xiàn);都未可知。但現(xiàn)在既是只有這Esperanto,便只能先學(xué)這Esperanto。現(xiàn)在不過(guò)草創(chuàng)時(shí)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獨(dú)木小舟;倘使因?yàn)轭A(yù)料將來(lái)當(dāng)有汽船,便不造獨(dú)木小舟,或不坐獨(dú)木小舟,那便連汽船也不會(huì)發(fā)明,人類也不能渡水了。”
魯迅早年對(duì)漢字改革的看法,還可以從他1921年寫作的《阿Q正傳》里略知一二。他在第一章《序》中說(shuō):因?yàn)椴恢究竟是阿桂還是阿貴,“生怕注音字母還未通行,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國(guó)流行的拼法寫他為阿Quei,略作阿Q。這近于盲從《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語(yǔ)言雖然詼諧,但是魯迅贊成漢語(yǔ)拼音化的態(tài)度已經(jīng)躍然紙上了。
其實(shí),錢玄同的改革主張是經(jīng)過(guò)深入考慮的。他認(rèn)為,只改漢字的形式,采用所謂簡(jiǎn)字、羅馬字之類的拼音文字,而不廢漢語(yǔ),是極為困難的。“中國(guó)語(yǔ)言文字,極不一致,一也;語(yǔ)言之音,各處固萬(wàn)有不同矣,即文字之音,亦復(fù)紛歧多端,二也。”這在當(dāng)時(shí)牽涉到兩個(gè)問(wèn)題。第一,文言與白話不一致;第二,各地方音不統(tǒng)一。“言文、音讀不統(tǒng)一,即斷難改用拼音。”事實(shí)上,也只有在白話文運(yùn)動(dòng)和國(guó)語(yǔ)運(yùn)動(dòng)取得成功之后,漢語(yǔ)拼音方案才能提上議事日程。
3.傅斯年的回答
錢玄同還指出,漢文根本上尚有一無(wú)法救療之痼疾,則單音是也。單音文字,同音者極多,改用拼音,如何分別?對(duì)此,傅斯年的回答是:漢語(yǔ)不是純粹的單音節(jié),漢字絕對(duì)應(yīng)當(dāng)用拼音字母代替,漢語(yǔ)也絕對(duì)能用拼音字母表達(dá)。
1919年,傅斯年在《新潮》一卷三號(hào),發(fā)表了《漢語(yǔ)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談》一文,大肆咒罵“中國(guó)文字的起源是極野蠻,形狀是極奇異,認(rèn)識(shí)是極不便,應(yīng)用是極不經(jīng)濟(jì),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進(jìn)而提出了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看法。文章的內(nèi)容分五個(gè)方面:(1)“漢字應(yīng)當(dāng)用拼音文字替代否?”他認(rèn)為:“絕對(duì)的應(yīng)當(dāng)!”文字是表現(xiàn)語(yǔ)言的工具,工具就要求方便,漢字難學(xué)、費(fèi)時(shí)、難寫,效用低,遠(yuǎn)不如拼音文字方便。(2)“漢語(yǔ)能用拼音文字表達(dá)否?”他認(rèn)為:“絕對(duì)的可能!”漢語(yǔ)不是純粹的單音節(jié),以詞為單位,可以用拼音文字表達(dá)。(3)“漢字能無(wú)須改造,用別種方法補(bǔ)救否?”他認(rèn)為:“絕對(duì)的不可能!”(4)“漢語(yǔ)拼音文字如何制作?”他認(rèn)為字母以羅馬字母為藍(lán)本,字音用藍(lán)青官話,文字結(jié)構(gòu)以詞為單位。(5)“漢語(yǔ)的拼音如何施行?”
他認(rèn)為:“先從制作拼音文字字典起。”
4.“漢字改革”的討論
從1918年起,錢玄同先后在《新青年》發(fā)表了《中國(guó)今后之文字問(wèn)題》(四卷四號(hào))、《漢字革命之討論》(五卷五號(hào))、《羅馬字與新青年》(五卷六號(hào))等,繼續(xù)鼓吹“漢字革命”。1920年,錢玄同在《新青年》六卷三號(hào)上發(fā)表《減省漢字筆畫的提議》,又在《平民教育》上發(fā)表《漢字改良的第一步——減省筆畫》,主張改良漢字,減省筆畫,推行簡(jiǎn)體字。這時(shí)他的主張也逐漸由采用世界語(yǔ)、反對(duì)羅馬字母之類的拼音文字,轉(zhuǎn)為推進(jìn)國(guó)語(yǔ)、支持羅馬字母的拼音制了。
1918—1923年,關(guān)注漢字改革的刊物,除《新青年》、《新潮》之外,還有《東方雜志》、《學(xué)燈》、《國(guó)語(yǔ)月刊》等十余種。討論的內(nèi)容包括漢字改革、國(guó)語(yǔ)推廣、拼音方案、新式標(biāo)點(diǎn)等,林林總總,不一而足。
5.“漢字改革”專刊
1922年,錢玄同在教育部“國(guó)語(yǔ)統(tǒng)一籌備會(huì)”第四次大會(huì)上提出《減省現(xiàn)行漢字的筆畫案》,由黎錦熙、楊樹達(dá)聯(lián)署。提案全文最終刊登在1923年出版的《國(guó)語(yǔ)月刊》一卷七期“漢字改革號(hào)”特刊上,胡適為本期專號(hào)撰寫了“卷頭言”。
胡適指出,二千年來(lái)的中國(guó)的小百姓不但做了很驚人的文法革新,他們還做了一件同樣驚人的革新事業(yè),就是漢字形體上的大改革,就是“破體字”的創(chuàng)造欲提倡。“錢玄同、黎劭西(錦熙)諸位先生們對(duì)于古來(lái)這些破體字,曾經(jīng)細(xì)細(xì)研究過(guò),認(rèn)為很有理由的改革,不是退化。他們覺得這些破體的‘新字’不是小百姓印曲本灘簧的專有品,乃是全國(guó)人的公共利器。所以他們現(xiàn)在以言語(yǔ)學(xué)家的資格,十分鄭重的對(duì)全國(guó)人民提出他們審查的報(bào)告,要求全國(guó)人采用這幾千個(gè)合理又合用的簡(jiǎn)筆新字來(lái)代替那些繁難不適用的舊字。”
錢玄同在卷頭“附志”中特別說(shuō)明,“字體改簡(jiǎn),只是漢字改革的第一步,只是第一步中的一種方法,而且只是第一步中的一件事;此外應(yīng)該研究的問(wèn)題很多很多。”錢玄同所說(shuō)的第一步,就是專刊上刊登的《減省現(xiàn)行漢字的筆畫案》。在“漢字改革”專號(hào)上,還刊登了蔡元培、黎錦熙、傅斯年、趙元任、沈兼士等人的論文,為漢字改革吹響了號(hào)角。
錢玄同在《減省現(xiàn)行漢字的筆畫案》中指出,現(xiàn)行漢字筆畫太多,書寫費(fèi)時(shí),是一種不適用的符號(hào),是學(xué)術(shù)上、教育上的大障礙。改用拼音是治本的事業(yè),減省現(xiàn)行漢字的筆畫是治標(biāo)的辦法。但是,我們決不能等拼音的新文字成功了才來(lái)改革,所以治標(biāo)的辦法是目前最切要的辦法。錢玄同考察了漢字的歷史進(jìn)化,發(fā)現(xiàn)漢字的字體,在數(shù)千年中是時(shí)時(shí)減省的。他分析了以前簡(jiǎn)體字的八種構(gòu)成方法,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承認(rèn)它們是現(xiàn)行漢字的改良之體。
6.“漢字革命”
同一專號(hào)上刊登的錢玄同《漢字革命》一文更為清晰地表明了他的理論主張:“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guó)語(yǔ)決不能統(tǒng)一,國(guó)語(yǔ)的文學(xué)決不能充分的發(fā)展,全世界的人們公有的新道理、新學(xué)問(wèn)、新知識(shí)決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國(guó)語(yǔ)寫出。何以故?因漢字難識(shí)、難記、難寫故,因僵死的漢字不足表示活潑潑的國(guó)語(yǔ)故;因漢字不是表示語(yǔ)音的利器故;因有漢字作梗,則新學(xué)、新理的原字難以輸入于國(guó)語(yǔ)故。”錢玄同指出,“從漢字的變遷史上研究,漢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絕對(duì)的可能的事。”
從學(xué)理上看,“漢字應(yīng)否革命”已經(jīng)不成問(wèn)題,但是“漢字能否革命”恐怕還有人懷疑。換言之,“國(guó)語(yǔ)能否改用拼音文字表示?”他認(rèn)為,“漢字之根本改革”,“就是將漢字改用字母拼音,像現(xiàn)在的注音字母就是了”。而“漢字之根本改革的根本改革”,“就是拼音字母應(yīng)該采用世界的字母——羅馬字母式的字母”,即國(guó)際音標(biāo)(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錢玄同認(rèn)為,在漢字革命的籌備期內(nèi),還不能完全脫離漢字。他主張這時(shí)對(duì)于漢字“補(bǔ)偏救弊”:(1)寫“破體字”,即所謂“簡(jiǎn)體字”。錢玄同認(rèn)為,凡筆畫簡(jiǎn)單的字,不論古體、別體、俗體,都可以采用。(2)寫“白字”,即今天所說(shuō)的“同音替代字”。(3)有音無(wú)字或漢字表音不真切者,改用注音字母。(4)外國(guó)詞兒,直寫原文。萬(wàn)不得已要譯音,可用注音字母,不用漢字。“音譯”盡量少用。(5)注音字母獨(dú)立施用,與漢字同等價(jià)值。
7.黎錦熙與“國(guó)語(yǔ)運(yùn)動(dòng)”
早在1916年,黎錦熙已經(jīng)認(rèn)識(shí)到要普及教育、開發(fā)民智必須改革中國(guó)文字,于是他和教育界同仁86人等一起創(chuàng)建了“中華民國(guó)國(guó)語(yǔ)研究會(huì)”,積極提倡“國(guó)語(yǔ)統(tǒng)一”、“言文一致”。1917年,“國(guó)語(yǔ)研究會(huì)”委托黎錦熙擬定了一個(gè)《國(guó)語(yǔ)研究調(diào)查之進(jìn)行計(jì)劃書》,詳盡地規(guī)劃了音韻、詞類、語(yǔ)法等三個(gè)方面的調(diào)查研究。1919年,“國(guó)語(yǔ)研究會(huì)”的會(huì)員發(fā)展到九千八百余人,該會(huì)的“國(guó)語(yǔ)統(tǒng)一”、“言文一致”運(yùn)動(dòng),與《新青年》的“文學(xué)革命”潮流完全匯合了。“國(guó)語(yǔ)統(tǒng)一”、“言文一致”的標(biāo)語(yǔ)口號(hào)甚至一度登上了天安門。
1919年,教育部“國(guó)語(yǔ)統(tǒng)一籌備會(huì)”(簡(jiǎn)稱“國(guó)語(yǔ)統(tǒng)一會(huì)”)成立,由張一麐出任會(huì)長(zhǎng),吳敬恒(稚暉)任副會(huì)長(zhǎng)。會(huì)員有蔡元培、胡適、黎錦熙、錢玄同、趙元任、劉復(fù)(半農(nóng))、沈兼士、林語(yǔ)堂、汪怡等172人,下設(shè)“漢字省體委員會(huì)”、“國(guó)語(yǔ)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huì)”、“審音委員會(huì)”、“國(guó)語(yǔ)辭典委員會(huì)”和“國(guó)語(yǔ)辭典編纂處”等機(jī)構(gòu)。同年,黎錦熙撰寫了《國(guó)語(yǔ)學(xué)講義》,最早提出確定現(xiàn)代漢語(yǔ)的語(yǔ)音、詞匯、語(yǔ)法諸標(biāo)準(zhǔn)。
1922年,黎錦熙在“漢字改革”專號(hào)上發(fā)表了一篇長(zhǎng)文《漢字革命軍前進(jìn)的一條大路》,系統(tǒng)深入地研究了拼音文字的“詞類連書”問(wèn)題。在文章中他強(qiáng)調(diào)“詞類連書”對(duì)漢語(yǔ)拼音文字的重要性,認(rèn)為過(guò)去拼音文字的失敗在于不知道實(shí)行詞類連書。他認(rèn)為詞類連書是漢字革命軍通向拼音文字的一條大路,現(xiàn)在認(rèn)清了這條前進(jìn)的大路,就“應(yīng)該大膽地倡言漢字革命,興起漢字的革命軍”。這是詞類連寫問(wèn)題第一次得到比較系統(tǒng)的研究。
8.其他人的研究
在同一期專號(hào)上,趙元任發(fā)表了《國(guó)語(yǔ)羅馬字的研究》,文章回答了反對(duì)羅馬字的十大疑問(wèn),在擬訂“國(guó)語(yǔ)羅馬字的草稿”時(shí),提出了應(yīng)該注意的二十五條原則,并自曝了國(guó)語(yǔ)羅馬字未定的十二個(gè)疑點(diǎn)。文章中指出,拼音文字與語(yǔ)體文(即白話文)運(yùn)動(dòng)、國(guó)語(yǔ)統(tǒng)一運(yùn)動(dòng)是密切相關(guān)、互相依靠的,拼音方案僅僅是針對(duì)“國(guó)語(yǔ)”而非“文言”或者“方言”的。“草稿”相比盧戇章、王照、勞乃宣等切音字時(shí)期和章太炎、吳稚暉等注音字母時(shí)期的任何一個(gè)拼音方案都要完善,為后來(lái)擬定國(guó)語(yǔ)羅馬字方案提供了基礎(chǔ)。
在“漢字改革”專號(hào)上發(fā)表的文章還有蔡元培《漢字改革說(shuō)》。他也主張采用拉丁字母(羅馬字母)。他對(duì)廢除楷書,不采用注音字母,一定要用拉丁字母的理由也作了詳盡的闡述。
9.國(guó)語(yǔ)羅馬字拼音法式
經(jīng)過(guò)社會(huì)的廣泛討論和研究的日益深入,國(guó)語(yǔ)羅馬字的有關(guān)方案也越來(lái)越具體,已經(jīng)有條件制訂一個(gè)統(tǒng)一的國(guó)語(yǔ)羅馬字方案。1913年才誕生的注音字母,1918年剛由教育部公布,還沒幾年就已經(jīng)風(fēng)雨飄搖,朝不保夕了。
1923年,錢玄同、黎錦熙等向教育部“國(guó)語(yǔ)統(tǒng)一籌備會(huì)”提出了請(qǐng)組織“國(guó)語(yǔ)羅馬字委員會(huì)”的議案,由“國(guó)語(yǔ)羅馬字委員會(huì)”具體研究、征集各方意見,“定一種正確使用的‘國(guó)語(yǔ)羅馬字’來(lái)”。大會(huì)最后通過(guò)議案,決議組織“國(guó)語(yǔ)羅馬字研究委員會(huì)”,指定錢玄同、黎錦熙、趙元任、周辨明、林玉堂(語(yǔ)堂)、汪怡等11人為委員。大會(huì)提出,在推廣注音字母的同時(shí),兼用羅馬字母,“將羅馬字母作為國(guó)音字母第二式”;并討論了國(guó)語(yǔ)羅馬字的用途和具體研制的方法與步驟。
1925年,劉復(fù)(半農(nóng))從法國(guó)學(xué)成歸來(lái),在京發(fā)起組織了“數(shù)人會(huì)”,討論語(yǔ)言音韻,成員有劉復(fù)、趙元任、錢玄同、黎錦熙、林語(yǔ)堂、汪怡六人。從1925年至1926年,“數(shù)人會(huì)”開始討論“國(guó)語(yǔ)羅馬字”問(wèn)題。經(jīng)過(guò)一年時(shí)間,
22次討論會(huì),“數(shù)人會(huì)”終于通過(guò)了一份《國(guó)語(yǔ)羅馬字拼音法式》,后以“國(guó)語(yǔ)羅馬字研究委員會(huì)”名義呈交教育部,由教育部“國(guó)語(yǔ)統(tǒng)一籌備會(huì)”作非正式公布。公告中說(shuō),“羅馬字母,世界通用,辨認(rèn)拼切,已成國(guó)民常識(shí)之一”,因此,“定此《國(guó)語(yǔ)羅馬字拼音法式》,與《注音字母》兩兩對(duì)照,以為國(guó)音推行之助。此后增修《國(guó)音字典》,即依校訂之國(guó)語(yǔ)標(biāo)準(zhǔn)音拼成羅馬字,添記于《注音字母》之后,教育、交通、工商各界,如遇需用羅馬字時(shí),即以此種拼音法式為標(biāo)準(zhǔn),以昭劃一而便通行。”
10.國(guó)語(yǔ)羅馬字的推行
1928年,北伐成功,國(guó)民政府遷都南京,教育部改稱大學(xué)院,蔡元培出任院長(zhǎng)。9月中華民國(guó)大學(xué)院正式公布《國(guó)語(yǔ)羅馬字拼音法式》。文告中說(shuō):“該項(xiàng)《國(guó)語(yǔ)羅馬字拼音法式》,是以喚起全國(guó)語(yǔ)音學(xué)者之注意,并發(fā)表意見,互相參證;且可以為《國(guó)音字母》第二式,以便一切注音之用,實(shí)于統(tǒng)一國(guó)語(yǔ)有甚大之助力。特予公布,俾利推廣而收宏效。”
國(guó)語(yǔ)羅馬字正式公布后,國(guó)民政府就開始做推行工作。由于國(guó)語(yǔ)羅馬字拼寫規(guī)則復(fù)雜、難學(xué),妨礙了它的普及和傳播。連知識(shí)分子都感到不容易掌握,就更別說(shuō)平民百姓了。當(dāng)時(shí)的外交部、交通部使用譯音都沒有采納這一方案,在教育部門,更是連小學(xué)都進(jìn)不去。因此,盡管政府在宣傳和推廣方面盡了很大努力,結(jié)果社會(huì)大眾反應(yīng)冷淡,宣傳、推廣一直進(jìn)展不大,“國(guó)語(yǔ)羅馬字”本來(lái)是想取代注音字母的,其命運(yùn)反而還不如注音字母,最終走向消歇了。
二、左翼大眾式的“漢字改革”運(yùn)動(dòng)(1929—1949)
1.拉丁化新文字方案
與“國(guó)語(yǔ)羅馬字”(簡(jiǎn)稱“國(guó)羅”)運(yùn)動(dòng)南北相映的是“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簡(jiǎn)稱“北拉”)運(yùn)動(dòng)。1920年蘇聯(lián)在全國(guó)開展文化掃盲運(yùn)動(dòng),為境內(nèi)的少數(shù)民族語(yǔ)言制定了拉丁化的新文字拼法。1921年,瞿秋白旅蘇時(shí)受此啟發(fā),開始研究漢字拉丁化問(wèn)題。他深入研究了歷史上各種漢字改革方案,草成《拉丁化中國(guó)字》一稿。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再度流亡蘇聯(lián)的瞿秋白與吳玉章、林伯渠、肖三以及蘇聯(lián)專家郭質(zhì)生、龍果夫等,開始了制定拉丁文字方案的努力。經(jīng)過(guò)幾年研究,1929年由瞿秋白撰寫成《中國(guó)拉丁化字母方案》(漢文修訂稿后改名為《新中國(guó)文草案》),在莫斯科出版。
1931年9月,中國(guó)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會(huì)在海參崴開幕。會(huì)議通過(guò)了《中國(guó)文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guī)則》,其中“原則”13條,包括漢字改革各方面的原則問(wèn)題;“規(guī)則”包括“字母”、“拼音”、“寫法”等三方面的規(guī)則。大會(huì)認(rèn)為“中國(guó)漢字是古代與封建社會(huì)的產(chǎn)物,已經(jīng)變成統(tǒng)治階級(jí)壓迫勞苦群眾工具之一,實(shí)為廣大人民識(shí)字的障礙,已不適應(yīng)現(xiàn)在的時(shí)代。”(吳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78年版,第58頁(yè))會(huì)議決定,采用這種拉丁化新文字,一年內(nèi)掃除蘇聯(lián)遠(yuǎn)東華僑工人中的文盲。
2.瞿秋白的“廢除漢字論”
“拉丁化新文字”的主將瞿秋白是主張廢除漢字的,為此發(fā)表了不少抨擊漢字的激烈言辭。他宣稱:現(xiàn)在的普通中國(guó)話,已經(jīng)不是單音節(jié)言語(yǔ),而是多音節(jié)言語(yǔ)。而漢字是十分困難的符號(hào),聰明人都至少要十年八年的死功夫。何況漢字已經(jīng)只有音節(jié)的作用,沒有字眼的作用了。因此中國(guó)的現(xiàn)代白話——普通話,必須采用拼音制度,就是改用羅馬字母,制定一種新的中國(guó)文,完全廢除漢字:“中國(guó)的文字革命必須徹底的廢除漢字。”(瞿秋白《羅馬字的中國(guó)文還是肉麻字中國(guó)文?》,《瞿秋白文集》第二冊(cè)第661頁(yè))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真正造成現(xiàn)代的中國(guó)白話文,才能夠發(fā)展口頭上以及書面上的白話,才能夠完全脫離漢字的束縛——“這種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jì)的毛坑!”(瞿秋白《普通中國(guó)話的字眼的研究》,《瞿秋白文集》第二冊(cè)第690頁(yè))
瞿秋白認(rèn)為舊文學(xué)是“鬼話”、“鬼腔”的文學(xué),而“文學(xué)革命”不徹底,所生出來(lái)的新文學(xué)也成了“非驢非馬”的“騾子文學(xué)”。他認(rèn)為根源就在于沒有實(shí)行“文字革命”。要寫真正的白話文,就一定要廢除漢字,采用羅馬字母。只有從根本上廢除方塊漢字,代之以拉丁化(羅馬化)的拼音文字,才能實(shí)行“文藝革命”。(瞿秋白《論文學(xué)革命及語(yǔ)言文字問(wèn)題》,《瞿秋白文集》第二冊(cè))他受斯大林文字具有階級(jí)性的觀點(diǎn)影響,認(rèn)為漢字不是現(xiàn)代中國(guó)四萬(wàn)萬(wàn)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國(guó)遺留下來(lái)的士大夫——百分之三四的中國(guó)人的文字,“漢字存在一天,真正的‘人話文’——現(xiàn)代中國(guó)文(就是完全用白話的中國(guó)文字)就一天不能夠徹底的建立起來(lái)。”(瞿秋白《學(xué)閥萬(wàn)歲!》,《瞿秋白文集》第二冊(cè)第597頁(yè))
3.魯迅的回應(yīng)
對(duì)于“拉丁化新文字”,魯迅的評(píng)價(jià)是相當(dāng)積極的。1934年,他先后撰文《門外文談》、《關(guān)于新文字——答問(wèn)》、《中國(guó)語(yǔ)文的新生》等,鼓吹“拉丁化新文字”,這些文章均已收入1937年上海三閑書屋初版的《且介亭雜文》一書。
在《門外文談》中,魯迅談到,好一點(diǎn)的如羅馬字拼法,用世界通用的羅馬字拼起來(lái),一詞一串,非常清晰,但“好像那拼法還太繁。要精密,當(dāng)然不得不繁,但繁得很,就又變了‘難’,有些妨礙普及了。最好是另有一種簡(jiǎn)而不陋的東西。”“這里我們可以研究一下新的‘拉丁化’法,……它只有二十八個(gè)字母,拼法也容易學(xué)。……現(xiàn)在在華僑里實(shí)驗(yàn),見了成績(jī)的,還只是北方話。但我想,中國(guó)究竟還是講北方話——不是北京話——的人們多,將來(lái)如果真有一種到處通行的大眾語(yǔ),那主力也恐怕還是北方話罷。為今之計(jì),只要酌量增減一點(diǎn),使它合于各該地方所特有的音,也就可以用到無(wú)論什么窮鄉(xiāng)僻壤去了。”“只要認(rèn)識(shí)二十八個(gè)字母,學(xué)一點(diǎn)拼法和寫法,除懶蟲和低能外,就誰(shuí)都能夠?qū)懙贸觯吹枚恕r且它還有一個(gè)好處,是寫得快。”
在《關(guān)于新文字——答問(wèn)》中,魯迅說(shuō):“當(dāng)沒有知道拼音字之前,就不會(huì)想到象形字的難;當(dāng)沒有看見拉丁化的新文字之前,就很難明確的斷定以前的注音字母和羅馬字拼法,也還是麻煩的,不合實(shí)用,也沒有前途的文字。”“漢字也是中國(guó)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gè)結(jié)核,病菌都潛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jié)果只有自己死。先前也曾有過(guò)學(xué)者,想出拼音字來(lái),要大家容易學(xué),也就是更容易教訓(xùn),并且延長(zhǎng)他們服役的生命,但那些字都還很繁瑣。……這回的新文字卻簡(jiǎn)易得遠(yuǎn)了,又是根據(jù)于實(shí)生活的,容易學(xué),有用,可以用這對(duì)大家說(shuō)話,聽大家的話,明白道理,學(xué)得技藝,這才是勞苦大眾自己的東西,首先的唯一的活路。”又《中國(guó)語(yǔ)文的新生》說(shuō):“和提倡文言文的開倒車相反,是目前的大眾語(yǔ)文的提倡,但也還沒有碰到根本的問(wèn)題:中國(guó)等于并沒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議出現(xiàn),這才抓住了解決問(wèn)題的緊要關(guān)鍵。”“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須除去阻礙傳布智力的結(jié)核:非語(yǔ)文和方塊字。如果不想大家來(lái)給舊文字做犧牲,就得犧牲掉舊文字。走那一面呢,這并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敗,乃是關(guān)于中國(guó)大眾的存亡的。”
4.“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行
1935年12月,中國(guó)新文字研究會(huì)在上海成立。會(huì)議草擬了一個(gè)《我們對(duì)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見》,由文化界名流蔡元培、柳亞子、魯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簽名聯(lián)署。意見書中說(shuō):“中國(guó)已經(jīng)到了生死關(guān)頭,我們必須教育大眾,組織起來(lái)解決困難。但這教育大眾的工作,開始就遇著一個(gè)絕大難關(guān)。這個(gè)難關(guān)就是方塊漢字,方塊漢字難認(rèn)、難識(shí)、難學(xué)。”“中國(guó)大眾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這種新文字,現(xiàn)在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當(dāng)初是在海參崴的華僑,制造了拉丁化新文字,實(shí)驗(yàn)結(jié)果很好。他們的經(jīng)驗(yàn)學(xué)理的結(jié)晶,便是北方話新文字方案。”“我們覺得這種新文字值得向全國(guó)介紹。我們深望大家一齊來(lái)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為推進(jìn)大眾和民族解放運(yùn)動(dòng)的重要工具。”意見書中還提出了推行新文字的六項(xiàng)具體建議。
“拉丁化新文字”的興起,標(biāo)志著“國(guó)語(yǔ)羅馬字”的衰落。三十年代,國(guó)內(nèi)關(guān)于“文言、白話、大眾語(yǔ)”的論戰(zhàn)正酣,“拉丁化新文字”的方案?jìng)骰貒?guó)內(nèi),一時(shí)引起極大關(guān)注。“拉丁化新文字”運(yùn)動(dòng)與“大眾語(yǔ)”運(yùn)動(dòng)逐漸合流,遙相呼應(yīng)。“拉丁化新文字”運(yùn)動(dòng)也風(fēng)生水起,聲勢(shì)浩大。
不過(guò),“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行并不順利,遇到很多難以預(yù)料、無(wú)法克服的困難。固守漢字勢(shì)力的阻礙,注音字母及“國(guó)語(yǔ)羅馬字”支持者的反對(duì),使“拉丁化新文字”的支持者也逐漸修正了自己的主張。1939年7月,上海新文字研究會(huì)發(fā)表了由倪海曙執(zhí)筆、陳望道修改的《拉丁化中國(guó)字運(yùn)動(dòng)新綱領(lǐng)草案》。新綱領(lǐng)主張采用拉丁字母,一方面“反對(duì)立刻廢除漢字的過(guò)左的主張”,同時(shí)“也反對(duì)把漢字看作萬(wàn)古不變、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字靈物崇拜的頑固主張”,相對(duì)緩和了運(yùn)動(dòng)早期的激進(jìn)色彩。隨著抗戰(zhàn)新時(shí)代的到來(lái),“拉丁化新文字”與“國(guó)語(yǔ)羅馬字”二種拼音方案也由相互競(jìng)爭(zhēng)轉(zhuǎn)向最終合作,為建國(guó)后頒布“漢語(yǔ)拼音方案”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5.手頭字運(yùn)動(dòng)
從1933年開始,國(guó)內(nèi)掀起了“大眾語(yǔ)”論戰(zhàn),引起了一場(chǎng)倡導(dǎo)“手頭字”的運(yùn)動(dòng)。所謂“手頭字”,就是在普通群眾中間流行的一種俗體字。錢玄同對(duì)這些“手頭字”很感興趣,但是建議改稱“簡(jiǎn)體字”。1934年,錢玄同在國(guó)語(yǔ)委員會(huì)第二十九次常委會(huì)上提出《搜集固有而較適用的簡(jiǎn)體字案》,由教育部通過(guò),并委托錢玄同等起草《簡(jiǎn)化字譜》。當(dāng)年還出版了杜定友的《簡(jiǎn)字標(biāo)準(zhǔn)字表》和徐則敏的《500俗字表》等。
1935年,上海文字改革工作者組織“手頭字”推行會(huì),選定第一批“手頭字”300個(gè),2月由文化界200人及《太白》、《世界知識(shí)》、《譯文》等5個(gè)雜志社共同發(fā)表《推行手頭字緣起》。同年6月,錢玄同等完成《第一批簡(jiǎn)體字表》草稿,共計(jì)2300余字。他在《論簡(jiǎn)體字致黎錦熙、汪怡書》(《世界日?qǐng)?bào)·國(guó)語(yǔ)周刊》第204期)中探討了“簡(jiǎn)字之原則”,說(shuō)簡(jiǎn)體字所采選的材料,草書最多,俗體次之,行書又次之,古字最少。1935年8月,教育部先行公布了《第一批簡(jiǎn)體字表》,共324字。同時(shí),教育部頒布《各省市教育行政機(jī)關(guān)推行部頒簡(jiǎn)體字辦法》共9條,規(guī)定從1936年7月起,各學(xué)校考試答案,部頒簡(jiǎn)體字,得一律適用。這是歷史上第一批由官方公布的簡(jiǎn)化漢字,標(biāo)志著簡(jiǎn)化字運(yùn)動(dòng)進(jìn)入了新的階段。
除了官方的簡(jiǎn)化字運(yùn)動(dòng)之外,其它民間的簡(jiǎn)化字運(yùn)動(dòng)仍在繼續(xù)探索。1936年10月,容庚出版了《簡(jiǎn)體字典》(4445字),并在燕京大學(xué)開設(shè)了簡(jiǎn)體字課程。同年11月,陳光堯《常用簡(jiǎn)字表》(3150字)出版。1937年5月,字體研究會(huì)發(fā)表了《簡(jiǎn)體字表》第一表(約1700字)。抗日戰(zhàn)爭(zhēng)和解放戰(zhàn)爭(zhēng)期間,解放區(qū)的油印報(bào)刊吸收和創(chuàng)造了許多簡(jiǎn)化字。這些簡(jiǎn)化字隨著民主革命節(jié)節(jié)勝利而風(fēng)靡流行全國(guó)各地,被稱為“解放字”。
6.“漢字改革”的成效
1947年6月12日,教育部召開基本教育預(yù)備會(huì),討論到漢字與拉丁化等問(wèn)題。據(jù)《新聞報(bào)》報(bào)道,“亦有人主張廢除漢字,提倡漢字拉丁化,多數(shù)專家反對(duì),謂我國(guó)各地方言大多不同,倘用拉丁化文字,勢(shì)必分化中國(guó)之統(tǒng)一。我國(guó)數(shù)千年來(lái)之歷史文化,悉以漢字記載,且國(guó)人學(xué)習(xí)漢字,幾無(wú)一感到困難者,倘一旦廢除,無(wú)異斷送我一脈相承之固有文化。”
1949年5月4日,陸志韋在《進(jìn)步日?qǐng)?bào)》的“五四紀(jì)念”中發(fā)表《再談?wù)勑挛淖帧芬晃模闹姓f(shuō)“在老解放區(qū),拼音文字好象推行不開”,“過(guò)去的工作可以說(shuō)是失敗了,至少?zèng)]有完全成功”。陸志韋受到文字階級(jí)性觀點(diǎn)影響,他認(rèn)為漢字的“封建性”阻礙了拼音文字的推廣:“封建文字的鎖鏈又是雙重的”,一是“只許寫文言文”,二是“只許用方塊漢字,不許用拼音文字”。不難看出,陸志韋對(duì)方塊漢字和拼音文字的看法仍然是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以來(lái)的一貫見解。
三、“漢字改革”的前因后果
1.“漢字改革”的思潮
鴉片戰(zhàn)爭(zhēng)之后,中西文明劇烈沖突,有識(shí)之士痛感國(guó)人愚昧落后。光緒十八年(1892),中國(guó)“切音新字”的鼻祖盧戇章在《一目了然初階》自序中說(shuō):“竊謂國(guó)之富強(qiáng),基于格致;格致之興,基于男婦老幼皆好學(xué)識(shí)理;其所以能好學(xué)識(shí)理,基于切音為字……又基于字畫簡(jiǎn)易,則易于習(xí)認(rèn),亦即易于提筆。省費(fèi)十余載之光陰,將此光陰專攻于算學(xué)、格致、化學(xué)以及種種之實(shí)學(xué),何患國(guó)不富強(qiáng)也哉。”后來(lái)盧憨章草成《中國(guó)字母北京切音教科書》,書名旁題一聯(lián):“卅年用盡心機(jī),特為同胞開慧眼;一旦創(chuàng)成字母,愿教吾國(guó)進(jìn)文明。”視拼音文字為進(jìn)步之階。光緒三十四年(1908),勞乃宣向西太后上《普行簡(jiǎn)字以廣教育折》,稱英國(guó)“百人中有六十余人識(shí)字”,因此“民智開啟,雄視宇內(nèi)”。而“中國(guó)文字奧博,字多至數(shù)萬(wàn),通儒不能遍識(shí)。即目前日用所需,亦非數(shù)千字不足應(yīng)用”。因此,“今日欲救中國(guó),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識(shí)之字不可;欲為易識(shí)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進(jìn)呈〈簡(jiǎn)字譜錄〉折》)
其他東西方人士也有類似觀點(diǎn)。日本明治時(shí)期,福澤諭吉有“消減漢字”的看法,南部義籌也提議“廢除漢字”,改用羅馬字。英國(guó)人韋爾斯也說(shuō):“中國(guó)人的頭腦被禁錮在一種那么復(fù)雜、那么困難的文字和思維成語(yǔ)中,使得這個(gè)國(guó)家的精神活力大量消耗在語(yǔ)文學(xué)習(xí)上面。”
但是,以此理由苛責(zé)漢字是極不公平的。1908年,章太炎在反對(duì)提倡“萬(wàn)國(guó)新語(yǔ)”的《新世紀(jì)》諸編輯時(shí)說(shuō):“若夫象形、合音之別,優(yōu)劣所在,未可質(zhì)言。今者南至馬來(lái),北抵蒙古,文字亦悉以合音成體,彼其文化豈有優(yōu)于中國(guó)哉?合音之字,視而可識(shí)者。徒識(shí)其音,固不能知其義,其去象形,差不容于一黍。故俄人識(shí)字者,其比例猶視中國(guó)為少。日本既識(shí)假名,亦并粗知漢字。漢字象形,日本人識(shí)之不以為奇怪難了,是知國(guó)人能遍知文字以否,在強(qiáng)迫教育之有無(wú),不在象形、合音之分也。”(《駁中國(guó)用“萬(wàn)國(guó)新語(yǔ)”說(shuō)》,《民報(bào)》第二一號(hào))
2.教育落后的現(xiàn)實(shí)
不便掃除文盲、普及教育是否定漢字的一個(gè)強(qiáng)有力的理由,這種觀點(diǎn)一直到建國(guó)后的文字改革中都難以消除。
不過(guò),我們可以理解“漢字改革”的先行者那種急于求成的迫切心情,因?yàn)樵缦戎袊?guó)的教育現(xiàn)狀實(shí)在令人絕望和沮喪。據(jù)民國(guó)四年(1915)教育部統(tǒng)計(jì),當(dāng)時(shí)的識(shí)字率僅有7‰,清末恐怕更低。二十世紀(jì)三十年代,識(shí)字率普遍不到4%。即使到1949年新中國(guó)成立,識(shí)字率仍然只有20%,文盲率高達(dá)80%。在如此無(wú)奈的現(xiàn)實(shí)面前,大家只能尋求教育速成的辦法。但這樣一來(lái),卻有意無(wú)意地違背了教育最根本的一條宗旨: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上世紀(jì)五十年代,文字改革專家周有光與天津大學(xué)學(xué)生座談時(shí)談到了掃除文盲問(wèn)題,同學(xué)們認(rèn)為:“遠(yuǎn)水救不了近火,文字改革成拼音文字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實(shí)現(xiàn)的事,到時(shí)拼音固然實(shí)現(xiàn)了,文盲也已所剩無(wú)幾。”(周有光《同天津大學(xué)同學(xué)們談文改》,《光明日?qǐng)?bào)》1957年8月22日)事實(shí)正是如此,到2005年底,全國(guó)普及九年義務(wù)教育和掃除青壯年文盲地區(qū)的人口覆蓋率已提高到95%,文盲率下降到4%以下。但是漢字仍然健在,漢語(yǔ)拼音也沒有成為拼音文字,它的主要作用是給漢語(yǔ)注音,以便于漢字教學(xué)和普通話學(xué)習(xí)。
3.“歐洲中心論”的反思
鴉片戰(zhàn)爭(zhēng)以后,基督教會(huì)乘機(jī)在福建、廣東等沿海地區(qū)開展傳教活動(dòng),由于中國(guó)教民文盲居多,于是一些西方傳教士發(fā)明了所謂“話音字”、“白話字”等來(lái)翻譯《圣經(jīng)》,就是用羅馬字母拼寫當(dāng)?shù)胤窖裕@些拼音文字通稱為“教會(huì)羅馬字”(Romanized
Chinese)。十九世紀(jì)末至二十世紀(jì)初,至少有十七種方言用羅馬字拼音,不同方言譯本的羅馬字《圣經(jīng)》廣為流傳。比如“閩南白話字”,曾有100萬(wàn)人使用。至1987年,福建惠安、廈門、泉州等地,還有17萬(wàn)人使用。“白話字”除了能讀《圣經(jīng)》之外,還可以看“四書”,通家信等。
西方傳教士之所以發(fā)明“教會(huì)羅馬字”,有他們殖民主義的潛在動(dòng)機(jī)。西方有句諺語(yǔ):“字母跟著宗教走。”事實(shí)正是如此。傳教士聲稱,“繁難的漢字是二十世紀(jì)最有趣的時(shí)代錯(cuò)誤!”因此,“必須用羅馬字拼音代替漢字”。“我們并不把它看作一種書面語(yǔ)的可憐的代替品,我們要把它看成一種使西方的科學(xué)和經(jīng)驗(yàn)?zāi)軌驅(qū)σ粋€(gè)民族的發(fā)展有幫助的最大貢獻(xiàn)。”
視漢字為原始,以拼音為進(jìn)步,認(rèn)為漢字最終會(huì)走向拼音道路,這種以文字進(jìn)化定其優(yōu)劣的觀點(diǎn)在十九和二十世紀(jì)的東西方都是相當(dāng)普遍的,由于帶有濃烈的“歐洲中心論”色彩,所以這種觀點(diǎn)今天已經(jīng)很少有人相信了。
4.歷史功過(guò)誰(shuí)人評(píng)說(shuō)
建國(guó)后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務(wù)——簡(jiǎn)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yǔ)拼音方案,基本上是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回響和余波,是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開啟的“漢字革命”未竟事業(yè)的繼續(xù)。從“漢字革命”開始,不少參加過(guò)早期運(yùn)動(dòng)的學(xué)者,在建國(guó)后成為文字改革的生力軍,一些人更是直接領(lǐng)導(dǎo)和參與了有關(guān)文字改革方案的商討和制定。從這個(gè)意義上說(shuō),可以認(rèn)為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開啟的“漢字革命”最終取得了巨大成功,結(jié)出了豐碩果實(shí)。
但是巨大成功的背后,仍然難以掩蓋眾多的粗疏和失誤。這些改革的先行者相對(duì)忽視了漢字的固有特點(diǎn),忽視了漢字在字形辨義方面的重要作用。他們所提出的各種各樣的拼音方案,都難以徹底解決漢語(yǔ)同音字過(guò)多的問(wèn)題。趙元任曾戲?yàn)椤妒┦鲜唱{史》一文,突出了這種尷尬:
石室詩(shī)士施氏,嗜獅,誓食十獅。氏時(shí)時(shí)適市視獅。十時(shí),適十獅適市。是時(shí),適施氏適市。氏視是十獅,恃矢勢(shì),使是十獅逝世。氏拾是十獅尸,適石室。石室濕,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試食是十獅。食時(shí),始識(shí)是十獅,實(shí)十石獅尸。試釋是事。
回顧歷史,展望未來(lái),如何歷史地評(píng)價(jià)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以來(lái)的“漢字革命”運(yùn)動(dòng),當(dāng)前的語(yǔ)文現(xiàn)狀其實(shí)已經(jīng)給了一個(gè)最好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