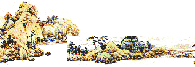|
|
|||
|
荒
|
||||
|
唐
|
||||
|
歲
|
||||
|
月
|
||||
|
□董新芳
|
||||
|
登記號(hào):21-2001-A-(0656)-0115
|
||||||
鑼鼓喧天,爆竹震地,紅旗招展,歌聲如潮。縣城的大街上游行隊(duì)伍高舉著“革命委員會(huì)好”的橫幅,高喊著“堅(jiān)決響應(yīng)偉大領(lǐng)袖毛主席的號(hào)召,實(shí)行革命的大聯(lián)合”的口號(hào),慢慢地向廣場(chǎng)涌來(lái)。今天,紅衛(wèi)縣革命委員會(huì)成立大會(huì)在這里舉行。 廣場(chǎng)的北面搭了一個(gè)主席臺(tái),主席臺(tái)上方牽著一條寬大的橫幅,上寫(xiě)“紅衛(wèi)縣革命委員會(huì)成立大會(huì)”,字大如斗,閃著金光。主席臺(tái)的幕布正中懸掛著偉大領(lǐng)袖毛主席的巨幅畫(huà)像,他老人家微笑著慈祥地望著歡呼的人群。廣場(chǎng)上人山人海,隊(duì)伍排列整整齊齊,昨天還是勢(shì)不兩立的兩大派,夜里聽(tīng)到了偉大領(lǐng)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階級(jí)內(nèi)部,沒(méi)有根本的利害沖突,沒(méi)有理由分裂成為勢(shì)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之后,一夜之間變成了同一條戰(zhàn)壕里的戰(zhàn)友,互相握著手并著肩站在神圣的紅旗下。 太陽(yáng)從東方冉冉升起,照耀著如海洋般的紅旗。高音喇叭里播放著“我們都是來(lái)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gè)共同的革命目標(biāo)走到一起來(lái)了……”這首使人人都感到親切且耳熟能詳?shù)拿飨Z(yǔ)錄歌。在歌聲中,七位身著不同顏色服裝的干部走上了主席臺(tái),端坐在早已排好座次的座位上。在七個(gè)人中,有兩位身著草綠色軍裝,不同的是,有一位閃閃紅星頭上戴,革命的紅旗掛兩邊,他是縣武裝部的政委。而另一位著黃軍裝者則是全縣赫赫有名的造反司令張光春。大會(huì)由張光春主持,主持詞是事先寫(xiě)好的,可能是太緊張或是太激動(dòng)抑或是兩者都有的緣故,他念得不那么通泰。趙書(shū)清宣布縣革命委員會(huì)組成人員名單。革命委員會(huì)主任趙書(shū)清,副主任張光春……宣布完畢,掌聲一片。接著,鑼鼓喧天,鞭炮齊鳴。廣場(chǎng)上彌漫著濃重的火藥味。大會(huì)在“革命委員會(huì)好”,“偉大領(lǐng)袖毛主席萬(wàn)歲萬(wàn)歲萬(wàn)萬(wàn)歲!”的口號(hào)聲中結(jié)束。廣場(chǎng)上的人們踏著《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曲的節(jié)拍喊著口號(hào)離開(kāi)了會(huì)場(chǎng)。 公社革命委員會(huì)成立了。主任是曾躍旗,衡來(lái)山當(dāng)上了副主任。據(jù)說(shuō)趙書(shū)清和張光春堅(jiān)持要衡來(lái)山當(dāng)主任的,而縣革命委員會(huì)另外五位成員堅(jiān)決反對(duì)而未搞成。 槐樹(shù)溝大隊(duì)也成立了革命委員會(huì),由于曾躍旗的賞識(shí),張光源當(dāng)了主任。 槐樹(shù)溝的副業(yè)組改成了副業(yè)隊(duì),越搞越紅火。隊(duì)里的葦子編完了,就到集市上買(mǎi),買(mǎi)回來(lái)后分到各家各戶(hù),各家各戶(hù)編成席交給隊(duì)里,隊(duì)里統(tǒng)一賣(mài)給供銷(xiāo)社。由于能掙到現(xiàn)錢(qián),社員們的積極性空前高漲。 那年,殺完葦子,張光源圍著葦園轉(zhuǎn)了半天,他突然決定給葦園施肥,這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反響。 “給葦子上糞,開(kāi)天辟地,從古到今,咱沒(méi)聽(tīng)說(shuō)過(guò)。”何大流邊往筐里鏟糞邊說(shuō)。 “仰擺著浮水,露球能。莊稼地里糞還不夠,還往葦園里扔。”另一人附和。 “說(shuō)球那么多弄啥?快裝。露能不露能,到時(shí)候就知道了。”二喜手握鉤擔(dān)站在那里等得有些不耐煩。 老悶擔(dān)著兩個(gè)大籮筐來(lái)了,何大流見(jiàn)他的籮筐太大沒(méi)給他裝滿(mǎn)。 “大流叔,堆滿(mǎn)。”老悶說(shuō)。 “娃子,你這籮筐大,堆太滿(mǎn)了挑不動(dòng)。”何大流說(shuō)。 “堆吧,會(huì)挑動(dòng)。”老悶說(shuō)。 老悶的籮筐堆得滿(mǎn)滿(mǎn)的,他挑上肩,鉤擔(dān)壓得忽閃忽閃的吱呀吱呀直叫。常言說(shuō),空手?jǐn)f不上擔(dān)擔(dān)的,擔(dān)擔(dān)的攆不上要飯的。擔(dān)子越重走得越快。老悶的擔(dān)子重,人也年輕,他大步流星,不大一會(huì)兒就攆上了走在前面的二喜。 “二喜叔,走快點(diǎn)。”老悶還故意用他的籮筐撞了一下二喜的籮筐,把二喜的籮筐撞得滴溜溜的轉(zhuǎn)。 “冒失鬼,你走前頭,老叔沒(méi)你勁兒大。”二喜給老悶讓開(kāi)了路。 老悶走在前頭,二喜緊跟在他的屁股后,兩人邊說(shuō)邊走,很快到了北溝的葦園。老悶放下鉤擔(dān),雙手提起籮筐把,手輕輕一旋,籮筐里的糞象一把扇子落在地上。 “來(lái),二喜叔,我?guī)湍闳觥!崩蠍炋崞鸲卜旁诘厣系幕j筐。由于用力過(guò)猛,一砣糞骨碌碌滾進(jìn)了響潭,咚地一聲,清亮而平靜的水面蕩起了道道波紋。“二喜叔,都說(shuō)響潭里有鬼,你說(shuō)到底有沒(méi)有?” “都說(shuō)有,可誰(shuí)也沒(méi)見(jiàn)過(guò)。” “都說(shuō)大腳嬸見(jiàn)過(guò)。” “你大腳嬸跟人家打賭跑來(lái)洗腳,不知道叫啥把腳纏住了,嚇得起身就竄,她也沒(méi)看見(jiàn)。” “說(shuō)過(guò)十二歲就看不見(jiàn)了,小娃子才能看見(jiàn)。二喜叔,十二歲咋都成大人啦?” “那是舊社會(huì),十二歲就娶媳婦了,娶了媳婦就成大人啦。” 老悶不語(yǔ)。 “老悶,你二十多了吧?” “嗯。” “要擱舊社會(huì)你都娶兩回媳婦了。” 老悶黑黑的臉上泛起了紅暈。 “跟老叔說(shuō),想媳婦沒(méi)有。” “……想有球啥用。” “你爹當(dāng)了縣上的大干部,給你娶個(gè)媳婦有球啥難。” “那你跟俺爹說(shuō)說(shuō)。” “你爹當(dāng)了大干部,忙球得仨倆月不回來(lái)一趟,我咋見(jiàn)得到他?” “那你啥時(shí)候見(jiàn)到他跟他說(shuō)說(shuō)。”老悶的目光帶著乞求。 “中,包在老叔身上。”二喜不無(wú)同情地說(shuō)。 “你可記住啊,二喜叔,甭忘了。” 葦園里上過(guò)糞后,張光源又叫社員們把葦園的土地松了松,糞和土攪和在一起,這也是社員們過(guò)去從沒(méi)有做過(guò)的事情。 一場(chǎng)春雨之后,葦筍從被松過(guò)的泥土中毫不費(fèi)力地鉆了出來(lái),根根茁壯,粗如雞蛋。在和煦的陽(yáng)光照耀下如竹筒吹著似的齊刷刷地往上竄。此時(shí),社員們才真正理解了張光源。沒(méi)多久葦子就長(zhǎng)了一人多高,密密麻麻,絲風(fēng)不透。張光源抽調(diào)勞力殺掉細(xì)小的葦子,埋在葦園的周邊。張光源的這一舉措雖然也引來(lái)了不少懷疑的目光,但終久沒(méi)人說(shuō)他是胡來(lái)。幾天大雨之后,埋在地下的小葦子每個(gè)節(jié)疤上都長(zhǎng)出了一撮蒜苗似的嫩芽。葦園擴(kuò)大了。細(xì)小的葦子被剔除后,大葦子有了更大的生長(zhǎng)空間,葦桿長(zhǎng)得更高更粗。葦子豐收了,社員們心里都暗暗佩服張光源。 副業(yè)隊(duì)正忙著編席,這時(shí),衡來(lái)山帶著公社“割尾巴”小組來(lái)到了槐樹(shù)溝。衡來(lái)山的這次到來(lái)不同于前,大躍進(jìn)時(shí)他到槐樹(shù)溝,身份是趙書(shū)清的秘書(shū)。第二次到槐樹(shù)溝是來(lái)送劉左左發(fā)動(dòng)群眾搞“文革”,那時(shí)掛的是公社造反司令部司令的頭銜,而真正的身份是公社民政員。這次的到來(lái),衡來(lái)山的身份變了,不是一個(gè)普普通通的干部而是公社革命委員會(huì)副主任,并帶著兩個(gè)隨行人員。衡來(lái)山是到這里抓反面典型的。在大批資本主義,人人斗私批修的今天,張光源居然敢組織副業(yè)隊(duì)大搞資本主義,就一定有后臺(tái)。他是來(lái)挖根源的。張光源搞資本主義,曾躍旗是知道的。曾躍旗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既不批評(píng)也不制止,任其發(fā)展。縣上割資本主義尾巴抓得那么緊,又是開(kāi)會(huì)又是下文件,可曾躍旗只在公社召開(kāi)的三級(jí)(公社,大隊(duì),生產(chǎn)隊(duì))干部會(huì)上輕描淡寫(xiě)的說(shuō)了幾句,接著就布置什么春耕生產(chǎn)。衡來(lái)山認(rèn)為,曾躍旗是在執(zhí)行資產(chǎn)階級(jí)路線(xiàn),他決定與曾躍旗對(duì)著干。衡來(lái)山向縣革命委員會(huì)主任趙書(shū)清匯報(bào)后,得到了趙書(shū)清的支持。衡來(lái)山專(zhuān)門(mén)成立了一個(gè)“割尾巴”小組,他要挨戶(hù)挨戶(hù)地割,一個(gè)隊(duì)一個(gè)隊(duì)地割,直到徹底割完。衡來(lái)山第一個(gè)點(diǎn)選槐樹(shù)溝是有原因的。他認(rèn)為:第一,槐樹(shù)溝的資本主義傾向明顯,這條尾巴容易抓住。第二,張光源的背后有人支持,那就是曾躍旗,搞張光源的目的是搞曾躍旗。 衡來(lái)山是喝過(guò)墨水的人,割資本主義尾巴是有一套的。他到槐樹(shù)溝的當(dāng)天晚上就叫公社電影隊(duì)來(lái)放了一場(chǎng)電影《春苗》。山村里放電影是十年難逢閏臘月的事,自然人到得很齊。比過(guò)年還要熱鬧。喝了湯,無(wú)論大人還是娃子,都搬著凳子來(lái)到曬場(chǎng),生怕占不到地方。婦女們怕來(lái)晚了,有的連湯也沒(méi)顧上喝,喝了湯的也沒(méi)顧上涮碗,任豬在圈里哼哼,她們也不去喂,早早地跑到了曬場(chǎng)。何五爺那么大一把年紀(jì)也拄著拐棍來(lái)了,跟瘸子何大流坐在一起。曬場(chǎng)上栽了兩根桿子,掛了一塊幕布,天剛黑,電影就開(kāi)始了。白色的幕布上一個(gè)個(gè)活靈活現(xiàn)的人在忙碌著,他們也吃飯,也睡覺(jué),也干活,也開(kāi)會(huì),也批判資本主義…… “咦,現(xiàn)在的人真能,咋著把人弄到那布上去了,你看跟真人一樣。”何五爺自言自語(yǔ)。 “五叔,那就是真人,咋不跟真人一樣。”何大流說(shuō)。 “剛才那閨女說(shuō)的啥?”何五爺指著影幕上的田春苗(電影里的人物)問(wèn)。 “她說(shuō)‘寧要社會(huì)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這話(huà)啥意思?”何五爺弄不明白。 “她的意思是說(shuō),咱們種莊稼要種社會(huì)主義的莊稼,不能種資本主義的莊稼,要是把莊稼種成了資本主義的莊稼,那情愿不要,還不如種成社會(huì)主義的草。”何大流解釋說(shuō)。 “放屁!她閨女家懂啥?不要莊稼要草,那人不都成畜牲啦!”何五爺對(duì)田春苗的胡說(shuō)八道憤憤然。 “五叔……”何大流還要說(shuō)啥,突然幕布上的人影全部消失了。 所有人的眼睛都望著放影機(jī)。這是衡來(lái)山叫關(guān)的。正在人們弄不清是咋回事兒的時(shí)候,喇叭里傳出了衡來(lái)山的聲音: “革命的社員同志們,現(xiàn)在我們開(kāi)個(gè)會(huì),會(huì)開(kāi)完了,接著放電影……” 人群中發(fā)出了嘁嘁喳喳的聲音。有的想走又舍不得,好不容易看場(chǎng)電影,不能看半截,因此只有坐在那里聽(tīng)衡來(lái)山講話(huà)。 衡來(lái)山說(shuō):“革命的社員同志們,剛才電影里田春苗同志的話(huà)大家都聽(tīng)見(jiàn)了,我們種莊稼也要種社會(huì)主義的莊稼,決不能種資本主義的莊稼。現(xiàn)在,農(nóng)村資本主義傾向十分嚴(yán)重,這要引起我們高度警惕。我們這次來(lái)你們村,就是發(fā)動(dòng)大家起來(lái)割資本主義尾巴……”衡來(lái)山還講了資本主義在農(nóng)村的種種表現(xiàn)和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意義,動(dòng)員大家找資本主義的苗頭。 副業(yè)隊(duì)被衡來(lái)山定為資本主義的大尾巴,一刀割了。 張光源被撤職了。 康光辰被趕走了。茶花牽著兒子跟在康光辰的身后,一步一回頭地離開(kāi)了槐樹(shù)溝。茶花的眼里噙著淚水,王彩珠的眼里也噙著淚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