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ffhyjd.com
|
|
 |

左東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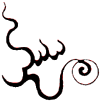
|
新書介紹——《王學(xué)與中晚明士人心態(tài)》 |
|
|
第三章嘉靖士人心態(tài)與王學(xué)之流變 第四節(jié)王畿——三教合一與士人心態(tài)的新變化 二、王畿心學(xué)理論所體現(xiàn)的人生價(jià)值取向 王畿心學(xué)理論所追求的統(tǒng)合圓融特征,從學(xué)術(shù)的角度講當(dāng)然是為了維 護(hù)陽明先生心學(xué)的真實(shí)精神。但從更深層的歷史背景看,他依然是為了回 應(yīng)時(shí)代向士人群體所提出的人生難題。他曾如此描述當(dāng)時(shí)的士人存在狀態(tài) 說:“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為柔愿,下者貪黷奔競以為身謀,不 墮于空虛則流于卑鄙污陋。”(同上卷十三,《先師畫像記后語》)如何糾 正這病態(tài)的士風(fēng),當(dāng)然是他需要考慮的內(nèi)容。從當(dāng)時(shí)學(xué)風(fēng)上看,或傾向于謹(jǐn) 慎恭敬,或偏重于放縱恣肆,如何避免二者的偏差,也是他需要解決的, 于是他提出了“纏繞的要脫灑,放肆的要收斂”(同上卷二,《水西精舍會(huì) 語》)的中行原則。從王畿本人看,他很早便被排除于官場之外,他盡管 有講學(xué)明道的熱情,但如何保持自我在失意的人生境遇中的安定,也是他 繞不過的大題目。因此,王畿的理論思考除了具有學(xué)術(shù)上的需要外,更重 要的是解決人生存在的現(xiàn)實(shí)問題。人生存在問題體現(xiàn)在王畿的心學(xué)理論 中,實(shí)際上便是其人生價(jià)值取向問題。在此一方面,也貫穿了其執(zhí)其兩端 而求其中的圓融思路,具體地講便是,他既不放棄儒家萬物一體的人生責(zé) 任與現(xiàn)實(shí)關(guān)注,又要保持自我的順適與人格的尊嚴(yán),但又不執(zhí)著于其中一 端,而是超越二者,追求一種既可入世又可出世的豪杰人格與圣者境界。 于是,在王畿這里,已經(jīng)沒有入世與出世的對(duì)立,從而也就沒有了儒釋道 的區(qū)別與揀擇。而所有這一切,又都被統(tǒng)一于其良知學(xué)說之下,最終形成 了王畿獨(dú)特的人生價(jià)值理論。 王畿毫無疑問是不能同意脫離現(xiàn)實(shí)而歸于獨(dú)善的人生態(tài)度的,這不僅 可以證之以他終生孜孜不倦地講學(xué)論道、共明圣學(xué)的人生實(shí)踐,還可以在 其對(duì)聶豹、羅洪先的歸寂之學(xué)的批評(píng)中得到充分的證明。聶、羅二人的歸 寂主張當(dāng)然是為了在險(xiǎn)惡的環(huán)境中能保持自我的純潔與安定,但同時(shí)歸寂 也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環(huán)境采取的一種回避態(tài)度,說明了他們對(duì)于環(huán)境浸染的恐懼。 當(dāng)念庵先生高臥山中不出時(shí),王畿便致函相勸說:“吾兄素行超卓,真純 粹白,同志素所信向。乃今閉關(guān)多年,高臥不出,于一己受用得矣,如世 道何?兄見此輩發(fā)心不真,遂生厭離,不如自了性命,于計(jì)為得。且見荊 川出山,大業(yè)未究,遂有所懲,益堅(jiān)遁世。竊計(jì)此亦過矣。大乘禪宗尚不 肯作自了漢。況兄平生種下萬物同體真種子,世間痛癢,素所關(guān)心,天機(jī) 感觸,隨處生發(fā),豈容自已?”(同上卷十,《與羅念庵》)念庵的歸山之 舉與歸寂之學(xué)都不是不可理解的,既然許多學(xué)者的講學(xué)論道以流于口頭而 與人生實(shí)踐無關(guān),那又有何必要再與之加以講論;既然世事已無可救藥, 荊川先生白陪了性命還要遭致非議,那還有什么必要出山去再白送一條性 命?但龍溪先生對(duì)此卻并不予以認(rèn)可,在他看來,既然身為儒者,在任何 情形下都不能自了性命。因?yàn)楦吲P不出盡管可以獲一己受用的人生實(shí)惠, 可是卻放棄了“萬物同體”的儒者精神,放棄了維護(hù)世道的責(zé)任,而如果 不關(guān)心“世間痛癢”,就不能算是一個(gè)真正的儒者。于此可見龍溪進(jìn)取精 神之強(qiáng)烈。但王畿不能自了性命的確切涵意是不能僅僅自了性命,而不是 說不能關(guān)注自我性命,于是,王畿的經(jīng)世便與一般的世俗之學(xué)有了區(qū)別, 那就是既不能重己而輕天下,也不能為天下而失去自我,而是要二者兼顧, 雙重并舉,其關(guān)鍵在于致良知,故曰:“夫儒者之學(xué)務(wù)于經(jīng)世,但患于不 得其要耳。昔人謂以至道治身,以土苴治天下,是猶泥于內(nèi)外精粗之二見 也。動(dòng)而天游,握其機(jī)以達(dá)中和之化,非有二也。功著社稷而不尸其有, 澤究生民而不宰其能,教彰士類而不居其德,周流變動(dòng),無為而成,莫非 ‘良知’之妙用,所謂渾然一體者也。”(《刻陽明先生年譜序》,見《王 陽明全集》卷三七)作為儒者的王畿,絕不能同意將治身與治天下分開的 主張,尤其不能同意“以土苴治天下”的自私主張,而是應(yīng)該既有“動(dòng)而 天游”的瀟灑,同時(shí)又能握其機(jī)以化天下的治功,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化成 天下而不以為功的超越境界,這便叫做“渾然一體”的良知效用。 既然王畿具有如此強(qiáng)烈的儒家參與意識(shí),那他何以會(huì)遭到后人流于禪 的嚴(yán)厲批評(píng)呢?如劉宗周言其“蹈佛氏之坑塹”,“孜孜學(xué)道八十年,猶未 討歸宿,不免沿門持缽。”(《明儒學(xué)案》,《師說》)這當(dāng)然不是毫無根 據(jù)的指責(zé),在王畿的言論中,的確有不少地方公然為佛道辯護(hù),比如:“二 氏之學(xué)雖與吾儒有毫厘之辨,精詣密證植根甚深,豈容輕議?” (《王龍溪先生全集》卷十七,《水西別言》)“三教之說,其來尚矣。 老氏言虛,圣人之學(xué)亦曰虛;佛氏言寂,圣人之學(xué)亦曰寂。孰從而辨之? 世之儒者不揣其本,類以二氏為異端,亦未為通論也。”(同上,《三教堂 記》)“或問莊子之學(xué)。先生曰:莊子已見大意,擬諸孔門,庶幾開點(diǎn)之儔。” (廣理學(xué)備考本《王龍溪先生集》,《諸會(huì)語節(jié)錄》)理學(xué)之改造佛、道以 彌補(bǔ)自身心性論之不足,盡管從宋儒那里已經(jīng)成為普遍的事實(shí),但一般在 口頭上均對(duì)此采取回避的態(tài)度,更有甚者,他們事實(shí)上對(duì)佛、道已染之甚 深,可公開場合卻又對(duì)其大張撻伐,以維護(hù)儒學(xué)的正統(tǒng)性與權(quán)威性。而王 畿在此卻公然替佛、道辯護(hù),對(duì)其不許“輕議”,言世儒斥佛、道為異端 “未為通論”,甚至等莊子為曾點(diǎn),如此的勇氣在龍溪之前也許只有陽明 先生堪與相匹,也難怪會(huì)招致劉宗周的強(qiáng)烈非議了。王畿之如此鐘情佛、 道,當(dāng)然不是偶然的失誤,而是在價(jià)值取向上的與之趨近,那就是他更重 視個(gè)體的存在與受用。在陽明那里,強(qiáng)調(diào)的依然是為學(xué)須有切于身心,即 所謂的“實(shí)有諸己”,其真實(shí)意蘊(yùn)為堅(jiān)定自我的成圣信念與與鼓舞自我的 濟(jì)世熱情。可到了龍溪這里,則變成了如下的表述:“學(xué)原為了自己性命, 默默自修自證。”(同上,《擬峴臺(tái)會(huì)語節(jié)錄》)“吾輩講學(xué),原為自己性 命,雖舉世不相容,一念炯然,豈容自昧。”(《王龍溪先生全集》卷十一, 《與張陽和》)“吾人發(fā)心原為自己性命,自信不惑,雖萬死一生,亦當(dāng)出 頭擔(dān)荷。”(同上,《與趙瀔陽》)在這些表述里,當(dāng)然也包含有陽明先生 所講的那層意思,但如此反復(fù)突出“自己性命”,依然透露出他更為重視個(gè) 體自我的用意,證之以他對(duì)生死問題的格外留意,便更會(huì)得出其看重個(gè)體生 命的結(jié)論。儒家由于從本質(zhì)上講是一種協(xié)調(diào)社會(huì)關(guān)系、強(qiáng)調(diào)社會(huì)倫理的學(xué)問, 因而除了對(duì)祖先的祭祀比較重視外,很少留意個(gè)體的死亡方面,于是遂留 下了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千古名言。但龍溪在與人論學(xué)時(shí)卻屢屢談 及對(duì)個(gè)人生死的思考,他說:“堪破世間原無一物可當(dāng)情,原無一些子放 不下,見在隨緣,緣盡即空,原無留滯,雖兒女骨肉,亦無三四十年聚頭, 從未生以前觀之,亦是假合相,況身外長物,可永保乎?”(同上卷九, 《李克齋》)在此他不僅動(dòng)用了禪宗未生以前的空無理論,而且將儒家極 其看重的人倫親情也予以淡化,已顯示出有異于傳統(tǒng)儒學(xué)的價(jià)值傾向。然 后,他又從對(duì)生的孤獨(dú)轉(zhuǎn)感嘆轉(zhuǎn)向?qū)λ劳龅纳钋嘘P(guān)注,故而說:“衰齡殘 質(zhì),后來光景已無多,,生死一念,較舊頗切。古云平時(shí)明定,臨期自然 無散亂。有生死無生死皆不再計(jì)度中,一念惺惺,泠然自照,縱未能超, 亦任之而已。”(同上卷十一,《答劉抑亭》)他不僅想到了死,而且還想 到了對(duì)死亡焦慮的克服。而若欲消除對(duì)死亡的恐懼,便須認(rèn)真思考人類生死 的真實(shí)內(nèi)涵,于是他又動(dòng)用了莊子的理論:“近來勘得生死一關(guān)頗較明白, 生死如晝夜,人所不免,此之謂物化。若知晝而不知夜,便是溺喪而不知 歸,可哀也已。”(同上卷九,《答耿楚侗》)此處的生死如晝夜、物化、 視死如歸家等理論,全都是從莊子那里轉(zhuǎn)手而來的。借莊子弄懂死之不可避 免的道理后,他開始入手解決此一問題,他說:“生死如晝夜,人所不免。 四時(shí)之序,成功者退。人生天地間此身同于太虛,一切身外功名得喪,何 足以動(dòng)吾一念。一日亦可,百年亦可,做個(gè)活潑潑無依閑道人,方不虛生 浪死耳。”(同上卷十二,《與吳中淮》)龍溪先生畢竟是通達(dá)的,他沒有 走向道教長生不老的荒唐奢望,而是憑借原始道家的內(nèi)在超越理論,希望達(dá) 到與天地合一的超然境界,做一個(gè)“無依閑道人”。然而道家的超越理論 畢竟較為粗糙,不能完全解決龍溪先生的問題,因?yàn)閷?duì)于死亡此一揪心的 人生話題,并不是說忘便可忘掉的,于是龍溪?jiǎng)佑昧溯^道家更為精密的佛 家理論,他說:“人之有生死輪回,念與識(shí)為之祟也。念有往來:念者二 心之用,或善善,或惡惡,往來不常,便是輪回種子。識(shí)有分別:識(shí)者發(fā) 智之神,攸而起,攸而滅,起滅不停,便是生死根因。……儒者以為異端 之學(xué),諱而不言,亦見其惑也。夫念根于心,至人無心則念息,自無輪回; 識(shí)變?yōu)橹寥藷o識(shí)則知空,自無生死。”(同上卷七,《新安斗山書院會(huì) 語》)超生死,絕輪回,這正是佛家立教之本意。龍溪先生通過釋、道融 會(huì),終于建立起了自己擺脫死亡威脅的超越理論。而他這樣做的目的,則 在于成就自我“做個(gè)出世間大豪杰”,并獲得個(gè)體自我的受用,所謂“眼 面前勘得破,不為逆順稱譏所搖,腳根下扎得定,不為得喪利害所動(dòng),時(shí) 時(shí)從一念入微醞釀主張,討個(gè)超脫受用。才有所向便是欲,才有所著便是 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著,便是絕學(xué)無為本色道人。”(同上卷十一,《與 李見亭》)至此我們明白了王畿的學(xué)術(shù)思路:他鐘情佛、道的原因在于要 解決生死問題的糾纏,而解決生死問題的目的又在于獲取個(gè)體自我的超脫 受用,則說王畿相當(dāng)重視個(gè)體人生的價(jià)值應(yīng)該是言有所據(jù)的。王畿此種人 生價(jià)值取向的思想背景可從兩方面來理解,一方面是對(duì)于險(xiǎn)惡政治環(huán)境的 回應(yīng),忘生死意味著排除外在環(huán)境對(duì)自我的心理威脅,這與聶、羅二人的 歸寂為同一思路,所以王畿在釋《易》之艮卦時(shí),認(rèn)為“艮止”之意為: “惟得其所止,是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忘己忘物,而無咎也。”(同上 卷八))此乃從消極面講,可稱之為自保。然同時(shí)又有積極之一面,此可 稱之為求樂或曰受用。王畿對(duì)此曾作過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所謂“無生死執(zhí)吝,與 太虛同體,與大化同流,此大丈夫超脫受用,功成行滿之時(shí)也。”(同上卷 九,《與潘笠江》)“獨(dú)往獨(dú)來,討個(gè)臨行脫灑受用,方不負(fù)大丈夫出世一 番也。”(同上,《與呂沃洲》)此種求樂的追求是嘉靖時(shí)期士人群體中興 起的一種日益強(qiáng)烈的人生愿望,許多士人被從官場排斥出來,在政治上難以 再有作為,于是便轉(zhuǎn)而追求自我身心的安樂,乃是順理成章之事;而且整 個(gè)社會(huì)風(fēng)俗也都在向著追求物質(zhì)與精神的享樂方面發(fā)展,尤其是王學(xué)流行 的南方地區(qū),更是全國最為富庶、風(fēng)俗最為奢靡之地,身處其中的士人自 難免受其影響,王畿當(dāng)然不能無視此種存在而不做出自己的回答。 一面絕不放棄儒家萬物一體的濟(jì)世責(zé)任,一面又要追求個(gè)體存在的價(jià) 值與受用,這既是龍溪之學(xué)求全的特點(diǎn),也是其無法回避的矛盾。按龍溪 本人的學(xué)術(shù)方法,關(guān)鍵就在于如何取其中而使之歸于“圓”了。這不僅難 不倒他,反而是他最能發(fā)揮自身特長的方面,于是他又搬出了早已準(zhǔn)備好 的良知來對(duì)矛盾的兩端加以統(tǒng)合,故曰:“良知者,性之靈,以天地萬物 為一體,范圍三教之樞。”(同上卷十七,《三教堂記》)他很清楚,儒學(xué) 不足以解決生死問題,而“佛氏遺棄倫物感應(yīng)而虛無寂滅以為常,無有乎經(jīng) 綸之施,故曰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同上卷十,《答吳悟齋》)此即 其所言“夫沉空者,二乘之學(xué)也;溺境者,世俗之學(xué)也。”(同上卷三, 《周潭汪子晤言》)若欲經(jīng)世而不溺于境,自適而不沉于空,惟良知能兼而 有之,能兼之的原因在于良知具有超越二者的自然靈明,所以龍溪有詩曰: “三教峰頭一駐驂,俯看塵世隔蒼煙。青牛白馬知何處,魚躍鳶飛只自然。” (同上卷十八,《經(jīng)三教峰》)只有此“魚躍鳶飛”般的自然良知,才是超 越三教的真學(xué)脈。從濟(jì)世之一面講,王畿是如此描述其良知功用的:“大 人之學(xué)通天下國家為一身,身者家國天下之主也,心者身之主也,意者心 之發(fā)動(dòng)也,知者意之靈明,物即靈明感應(yīng)之跡也。良知是非之心,天之則 也,正感正應(yīng)不過其則,謂之格物,物格則知至矣。是非者,好惡之公也。 自誠意以至于平天下不出好惡兩端,是故如好好色而毋自欺,意之誠也。 好惡無所作,心之正也。無作則無辟矣,身之修也。好惡同于人而無所拂, 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其施普于天下而其機(jī)原于一念之微,是故致良知之 外無學(xué)矣。”(同上卷十,《答吳悟齋》)此種思路大致上未越出《大學(xué)》 所列的八條目,同時(shí)還有陽明以正物為致知的心學(xué)色彩,關(guān)鍵在于致良知非 但可以治國平天下,同時(shí)還可以“正心”。所謂“正心”即是“好惡無所 作”,既然無所作,也就不用有意“辟”,也就可以堂堂正正、心地坦然地 做人,此乃謂修身。則此處之修身不僅具道德修養(yǎng)之倫理義,并有心地安 然之心理義,或可稱之為內(nèi)外兼顧,身心兼修吧。從個(gè)體自我之適意講, 則可呈現(xiàn)出如下區(qū)別:“吾儒之學(xué)與禪學(xué)、俗學(xué),只在過與不及之間。彼 視世界為虛妄,等生死為電泡,自成自住,自壞自空,天自信天,地自信 地,萬變輪回,歸之太虛,漠然不以動(dòng)心,佛氏之超脫也。牢籠世界,桎 梏生死,以身徇物,悼往悲來,戚戚然若無所容,世俗之芥蒂也。修慝省 愆,有懼心而無戚容,固不以數(shù)之成虧自委,亦不以物之得失自傷,內(nèi)見 者大而外化者齊,平懷坦坦,不為境遷,吾道之中行也。”(同上卷十五, 《自訟問答》)這便是既不歸于寂,又不溺于境,“平懷坦坦,不為境遷”, 一派灑然而樂之境界,而最關(guān)鍵之處乃在于“內(nèi)見者大而外化者齊”,既 安頓了個(gè)體自我之存在,又未失與物同體之流通,于是便與禪學(xué)、俗學(xué)區(qū) 別開來了。而將上述二方面結(jié)合起來,便是王畿理想的人生境界,他稱此 為自得之學(xué),所謂“自得之學(xué)居安則動(dòng)不危,資深則機(jī)不露,左右逢源則 應(yīng)不窮。”如此便可成為超乎天地之外、立乎千圣之表的大豪杰。王畿曾 以豐富的想象力與詩一般的語言對(duì)此境界作出了描繪:“予所信者,此心 一念之靈明耳。一念靈明從混沌立根基,專而直,翕而辟,從此生天生地, 生人生萬物,是謂大生廣生,生生而未嘗息也。乾坤動(dòng)靜,神智往來,天 地有盡而我無盡,圣人有為而我無為,冥權(quán)密運(yùn),不尸其功,混跡埋光, 有而若無,與民同其吉兇,與世同其好惡,若無以異于人者。我尚不知我, 何有于天地,何有于圣人。外示塵勞,心游邃古,一以為龍,一以為蛇, 此世出世法也。”(同上卷七,《龍南山居會(huì)語》)這顯然是繼承陽明對(duì)良 知之功用的認(rèn)識(shí)發(fā)展而來的,但龍溪之良知已不僅有生天生地,成鬼成神的 生成功能,更重要的是,具備了“天地有盡而我無盡,圣人有為而我無為” 的超越境界,它既有“與民同其吉兇,與世同其好惡”的平凡入世特征, 又有“外示塵勞,心游邃古”的超然胸襟。與佛、道相比,具有其自我解 脫的精神境界,但沒有其決絕世界的消極寂滅;與俗學(xué)相比,具有其關(guān)注 民物,珍惜生命的入世態(tài)度,卻沒有其貪生怕死、為物所役的狹小拘謹(jǐn)。 這便是“所謂不以天下萬物撓己,自能了得天下萬物”(同上卷十二, 《與杜惟成》)的境界。 王畿所說的良知之學(xué)從語言層面看,頗有一些玄而不實(shí)的浪漫特征, 但如果從其立意核心看,實(shí)際上他是汲取了佛、道之空無與儒家之仁體, 從而形成其入世出世而兼?zhèn)涞乃枷胩卣鳌K梅稹⒌乐諢o來破執(zhí)掃跡, 以歸于悟,解決了自我超越世情的難題;同時(shí)他又用儒家之仁來與天下萬 物相聯(lián)通,以達(dá)于治,顯示了儒家現(xiàn)實(shí)關(guān)注的情懷。他曾說:“夫?qū)W莫要 于見性,性者心之生理,萬物之原,其同體于萬物,乃生生不容已之機(jī), 不待學(xué)慮而能,所謂仁也,千圣以來相傳學(xué)脈。”(同上卷十五,《跋徐存 齋師相教言》)有時(shí)他也稱此“仁”之機(jī)為學(xué)之“幾”,其實(shí)就是《易》所 言“生生”不已之宇宙精神。仁之觀念的介入對(duì)龍溪的心學(xué)理論是相當(dāng)重 要的,因?yàn)樗粌H保證了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注情懷,而且也使他的解脫理論未走 向寂滅的沉淪。從現(xiàn)實(shí)關(guān)懷角度言,仁不僅是對(duì)百姓自上而下的治理,更 是愛之順之的同情,所以他說:“學(xué)也者,以萬物為體者也。是故君子之 治也,視天下猶一家也,視天下之人猶一人也,視天下之心猶一心也。譬 諸木之千枝萬葉而一本也,水之千流萬派而一源也,是謂一視之仁。”悟 解了這種“一體之實(shí)學(xué)”,那便會(huì)“因民之生,順民之性”,否則便會(huì)“政 日擾,刑日繁,而治日遠(yuǎn)”。(同上卷十三,《起俗膚言后序》)此已近于 老氏之無為而治,其要在于順民之性。從自我解脫角度言,仁則保證了在擺 脫世俗生死等干擾的情況下而又不失生命的活力,王畿為此曾比較了“任 生死”與“超生死”的區(qū)別。所謂“應(yīng)緣而生,是為原始;緣盡而死,是 為反終。一日亦可,百年亦可,忘機(jī)委順,我無容心焉。任之而已矣。” 通達(dá)是夠通達(dá)了,但卻不免消極了些。而超生死則是:“退以為進(jìn),沖以 為盈,行無緣之慈,神不殺之武,固乎不扃之鑰,啟乎無轍之途,生而無 生,生不知樂;死不知死,死不知悲。”此種超生死的境界非但要有超然 的胸懷,還要擔(dān)負(fù)化成天下的責(zé)任,所謂“無緣之慈”,正是指那“過化 存神,利而不庸”的“無用為用”的大易之道。正是這仁之生生精神的介 入,使王畿的自我解脫理論具備了昂然的生機(jī)。 龍溪以仁為核心的良知之學(xué)從價(jià)值觀上講,實(shí)際上是要求個(gè)體與社會(huì) 達(dá)到一種平衡的狀態(tài),既不為社會(huì)而犧牲個(gè)體,也不為個(gè)體而破壞社會(huì), 從中體現(xiàn)了他持其兩端而求其中 的一貫風(fēng)格,比如他說:“吾人在世所保者名節(jié),所重者道誼。若為 名節(jié)所管攝,為道誼所拘持,便非天游,便非出世間大豪杰。”(同上卷十 二,《與魏敬吾》)既不能丟名節(jié)道誼,又要做超然自在之大豪杰。從這一 思路出發(fā),他接觸到了一個(gè)非常重要的命題,那便是人之自然性情與倫理 名教的關(guān)系問題,對(duì)此他依舊是執(zhí)其兩端,故曰:“性是心之生機(jī),命是 心之天則。口之欲味,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 五者性之不容已也,然有命存焉,立命所以盡性。茍縱其性而不知節(jié),則 天則毀矣。是認(rèn)欲為性,不知天命之性,故曰不謂性也。仁屬于父子,義 屬于君臣,禮屬于賓主,智屬于賢者,圣人屬于天道,五者命之不容已也, 然有性存焉,盡性所以立命。茍委于命而不知返,則生機(jī)息,是認(rèn)數(shù)為命 而不知天性之命,故曰不謂之命也。由前言之以命為重而性歸于命,不可 得而縱也;由后言之以性為重而命歸于性,不可得而委也。”(同上卷三, 《書累語簡端錄》)國內(nèi)的學(xué)者很少有人論及王畿的此種理論,因?yàn)榇硕?br> 話是他在解釋《孟子》“口之于味也”一章時(shí)而生發(fā)的,與孟子的原文相 比,王畿的解釋并沒有太多的新意,所以大家對(duì)此也便未多加留意,而日 本學(xué)者溝口雄三先生卻頗看中此段論述,認(rèn)為龍溪所言之“性”已不同于 宋儒所指稱的“義理之性”,并對(duì)其加以評(píng)述道:“命之天則,是不要讓性 墮入嗜欲放縱之中,或者,不要以先天的規(guī)矩措定去拘束性,在本來的條 理上,盡其性之自然,”并從中看出了“天理流貫中的良知的自活自在的 情態(tài)。”(《中國前近代思想之曲折與展開》第116頁)其實(shí),王畿此種價(jià) 值趨向的兩極性具有非常具體復(fù)雜的現(xiàn)實(shí)背景,他顯示了嘉靖時(shí)期士人群 體矛盾的人性狀況。面對(duì)日益增強(qiáng)的享樂傾向與思想界松動(dòng)的現(xiàn)實(shí),王畿 無論從他人還是從自身,都不能不受其影響,從而要求對(duì)人性的捆綁要有 所放松;但另一方面,士人對(duì)財(cái)富的占有欲望與對(duì)奢靡生活的追求已嚴(yán)重 地浸染了士風(fēng),寡廉鮮恥,唯利是圖,在士人中如瘟疫般到處傳播,若不 加以限制,則朝政的敗壞、官場的黑暗將愈演愈烈,從而達(dá)到不可收拾的 結(jié)局。因而王畿欲平衡兩端的想法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心學(xué)就其實(shí)質(zhì) 而言是一種自我修養(yǎng)與自我解脫的主觀心性學(xué)說,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 響現(xiàn)實(shí),卻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現(xiàn)實(shí),因?yàn)樗鼪]有制度上的保障與可共操作 的統(tǒng)一模式。我們看王畿是如何來使兩端求得平衡而取其中的:“吾人不 守道義不畏名節(jié),便是無忌憚之小人;若于此不得轉(zhuǎn)身法,才為道義名節(jié) 所拘管,又未嘗是超脫之學(xué)。嘗謂為學(xué)而有所忌憚做不得真小人,為善近 名做不得真君子。若真信得良知過時(shí),自生道義,自存名節(jié),獨(dú)往獨(dú)來, 如珠之走盤,不待拘管而自不過其則也。”(同上卷四,《過豐城答問》) 一切又都回到了良知這里,解決名節(jié)與自由的矛盾如此,解決自然之性與倫 理天命之間的矛盾也應(yīng)當(dāng)是如此。王畿當(dāng)然有其前提的規(guī)定,那就是真正 悟得了良知精義時(shí),方可自作主張,然而問題的關(guān)鍵是,有誰來驗(yàn)證是否 真正悟得了良知。如果未能悟得卻又過于自信,豈非正應(yīng)了當(dāng)時(shí)士人的一 種格言:“自以為是,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如果每人都“自生道義,自存 名節(jié),獨(dú)往獨(dú)來”,如何能保證他們?nèi)寄堋安淮泄芏圆贿^其則”? 因而王畿的心學(xué)理論與人生價(jià)值取向便不能不成為一種多指向的開放性 體系,其最終的指向須視為學(xué)者個(gè)人的特點(diǎn)以及它所遇到的時(shí)代如何而決 定。而就王畿的本意講,他是想魚與熊掌而兼得的。 |
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
版權(quán)所有 北京國學(xué)時(shí)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Copyright©2000
國學(xué)網(wǎng)站,版權(quán)專有;引用轉(zhuǎn)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quán)。
國學(xué)網(wǎng)站,版權(quán)專有;引用轉(zhuǎn)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q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