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ffhyjd.com
|
|
 |

左東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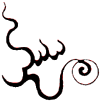
|
新書介紹——《王學(xué)與中晚明士人心態(tài)》 |
|
|
第三章嘉靖士人心態(tài)與王學(xué)之流變 第四節(jié)王畿——三教合一與士人心態(tài)的新變化 一、心學(xué)的內(nèi)部學(xué)術(shù)對(duì)話與王畿的良知觀 王畿(1497—1582),字汝中,號(hào)龍溪,浙江山陰人。他是陽明在世 時(shí)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他也終生以發(fā)揚(yáng)光大師門心學(xué)為己任。他中舉后就 學(xué)于陽明,遂不愿繼續(xù)參加科考,陽明勸之曰:“吾非以一第為子榮也, 顧吾之學(xué),疑信者半,子之京師可以發(fā)明耳。”這才決意前往,遂中嘉靖 五年會(huì)試。因“當(dāng)國(guó)者不悅學(xué)”,便對(duì)錢德洪說:“此豈吾與子仕之時(shí)也?” 二人皆不廷試而歸。嘉靖七年正欲赴廷試,而聞陽明逝世消息,遂奔喪之 廣信料理陽明喪事,然后守心喪三年。直到嘉靖十一年始參加廷對(duì)而中進(jìn) 士,授南京職方主事。(見《明儒學(xué)案》卷十二,《王畿傳》)后又進(jìn)至武 選郎中,給事中戚賢薦王畿學(xué)有淵源,可備顧問,但“夏言斥畿為偽學(xué), 奪賢職,畿乃謝病歸。”(《明史》卷二八三,《王畿傳》)從此便永遠(yuǎn)離 開官場(chǎng),而“孳孳以講學(xué)為務(wù),所至接引無倦色。自兩都吳楚閩越,皆有講 舍,江浙尤盛,會(huì)常數(shù)百人,年八十尤不廢出游。”(李贄《續(xù)藏書》卷二 二,《郎中王公》)由于此種經(jīng)歷,使王畿對(duì)當(dāng)時(shí)各地王學(xué)流派多有接觸, 對(duì)其發(fā)展?fàn)顩r非常清楚,故而他的講學(xué)不是閉門造車,而是在與各個(gè)流派 的對(duì)話甚至爭(zhēng)辯中提出自己的見解的,因此許孚遠(yuǎn)概括陽明之后王學(xué)之演 化說:“姚江之派復(fù)分為三,吉州(鄒守益)僅守其傳,淮南(王艮)亢 而高之,山陰(王畿)圓而通之。”(朱懷吳《昭代紀(jì)略》卷五)可以說, “圓”乃是王畿心學(xué)理論的最突出的特征。 王畿有一段話,充分顯示了此種“圓而通之”的特性,不妨全引如下: 良知宗說,同門雖不敢有違,然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擬議攙和。有謂 良知非覺照,須本于歸寂而始得,如鏡之照物,明體寂然而妍媸自辨,滯 于照則明反眩矣。有謂良知無見成,由于修證而始全,如金之在礦,非火 齊鍛煉,則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謂良知是從已發(fā)立教,非未發(fā)無知之本旨。 有謂良知本來無欲,直心以動(dòng),無不是道,不待復(fù)加銷欲之功。有謂學(xué)有 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體用。有謂學(xué) 貴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nèi)外,而以致知?jiǎng)e始終。此皆論學(xué)同異之見, 不容以不辨者也。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為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 用也。 見入井孺子而惻隱,見呼蹴之食而羞惡,仁義之心本來完具,感觸神 應(yīng),不學(xué)而能也。 若謂良知由修而后全,撓其體也。良知原是未發(fā)之中,無知而無不知, 若良知之前復(fù)求未發(fā),即為沉空之見矣。古人立教,原為有欲設(shè),銷欲, 正所以復(fù)其無欲之體,非有所加也。主宰即流行之體,流行即主宰之用, 體用一原,不可得而分,分則離矣。 所求即得之之因,所得即求之之證,始終一貫,不可得而別,別則支 矣。吾人服膺良知之訓(xùn),幸相默證,務(wù)求不失其宗,庶為善學(xué)也已。 (《擬峴山會(huì)語》,見《明儒學(xué)案》卷十二) 王畿此處的論述方式,頗有佛家之判教性質(zhì),他認(rèn)為其他的良知理論 均有其缺陷,只有他自己的見解才是最為圓滿完善的。以王畿在王門弟子 的位置與其對(duì)各派的了解程度,他也許有資格作出評(píng)判,至于所評(píng)是否正 確,則須視其具體內(nèi)容而定。觀本段文字,王畿的行文主旨在于顧及兩端 而執(zhí)其中,統(tǒng)合各方而歸其一,如寂之體與照之用必須兼顧,如果遺照便 是乖其用,那就是偏,因此他的主導(dǎo)思想乃是“體用一原”、“始終一貫”, 實(shí)際上也就是“圓”。“圓”當(dāng)然是針對(duì)不圓而發(fā)的,而當(dāng)時(shí)王畿所指的 不圓對(duì)象則主要是江右王學(xué)的主修派與歸寂派。主修派以鄒守益為代表, 他認(rèn)為要把握心學(xué)的精髓便不能“忽實(shí)修而崇虛談”,所以他為“惜陰會(huì)” 所作的《惜陰會(huì)約》中說:“凡鄉(xiāng)會(huì)之日,設(shè)先師像于中庭,焚香而拜, 以次列坐,相與虛心稽切居處果能恭否?執(zhí)事果能敬否?與人果能忠否? 居此者為德業(yè),悖此者為過失。德業(yè)則直書于冊(cè),慶以酒;過失則婉書于 冊(cè),罰以財(cái),大過則倍罰,以為會(huì)費(fèi)。”(《東郭集》卷七)此處非但有恭、 敬、忠諸倫理因素之強(qiáng)調(diào),并有相互監(jiān)督之責(zé)任及經(jīng)濟(jì)制裁之措施。此即 為龍溪所言“良知由修而后全”,其結(jié)果將會(huì)“撓其體”。故而雖同是在江 西設(shè)會(huì),王畿為洪都同心會(huì)所作會(huì)約便顯然不同,其所言設(shè)會(huì)原因曰:“但 恐吾人尚從間接承接過去,不能實(shí)致其知,日著日察,以求自得,則所謂 曉然明白者尚不免于播弄精魂,非實(shí)際也。夫不握其機(jī),則大化無從而運(yùn), 不入其竅,則大本無從而立,非借師友夾持啟悟,則未免溺于沉浮,安于 孤陋,大業(yè)亦無從而究。”可直其目的即在“夾持而悟”,故其會(huì)約中無絲 毫勉強(qiáng)措施,反而鼓勵(lì)寬容理解,所謂“議論偶有未合,不妨默體互證, 毋執(zhí)己長(zhǎng)以長(zhǎng)勝心,庶令可保始終,而此學(xué)賴以不墜。”(《龍溪王先生全 集》卷二)完全是自由討論的方式,目的便是求得本體之悟。可知他要糾 正鄒守益的,是只知修而不知悟。而對(duì)于聶豹、羅洪先二人所主張的歸寂, 王畿則認(rèn)為是只知求體而棄其用,同為一偏之論,因而與聶豹爭(zhēng)辯說:“感 生于寂,寂不離感。舍寂而言感,謂之逐物;離感而言寂,謂之泥虛。” (《明儒學(xué)案》卷十二,《致知辨議》)所以,若欲真正把握良知之實(shí),便 要即體即用,體用不分,“良知本體原是無動(dòng)無靜,原是變動(dòng)周流,此便 是學(xué)問頭腦,若不見得良知本體,只在動(dòng)靜二境上撿擇取舍,不是妄動(dòng),便 是著靜,均之為不得所養(yǎng)。”(同上,《東游會(huì)語》)從實(shí)際情形看,王畿 的確是最能領(lǐng)悟王陽明致良知的真實(shí)精神的,盡管黃宗羲言龍溪躋陽明而 為禪,但他還是不得不承認(rèn),王畿“親承陽明末命,其微言往往而在。” (同上)陽明的良知學(xué)說在發(fā)展過程中當(dāng)然有不一致甚至矛盾之處,而就 其主導(dǎo)特征而言,無論是早期的知行合一,還是晚年的致良知,都是強(qiáng)調(diào) 的體用不二,動(dòng)靜無間。王畿不僅繼承了此種學(xué)術(shù)思想,而且將其更加明 朗化。如當(dāng)年陽明在四句教中,有“無善無惡心之體”與“知善知惡是良 知”二句,本來是講的體用二端,但因表述含糊而引起了許多爭(zhēng)議,如今 在王畿這里便明快多了,如:“知是知非而實(shí)無是無非,知是知非者應(yīng)用 之跡,無是無非者良知之體也。”(《龍溪王先生全集》卷八,《艮止精一 之旨》)“蓋良知原是無中生有,無知而無不知。……虛寂原是良知之體, 明覺原是良知之用。體用一原,原無先后之分。”(同上卷二,《滁陽會(huì) 語》)將“無是無非”與“知是知非”同歸于良知之體用,概念得到了統(tǒng) 一,避免了不必要的誤解,而且由此推出了良知“虛明”的特征,從理論的 完善性上來說,的確要?jiǎng)龠^陽明一籌。這便是黃宗羲所指出的:“先生(指 王畿)疏河導(dǎo)源,于文成之學(xué),固多所發(fā)明也。”(《明儒學(xué)案》卷十二) 明清之際的許多學(xué)者都認(rèn)為王畿為學(xué)主悟主無,流入釋、道之中,使 陽明心學(xué)走入歧途。這當(dāng)然不能說毫無道理,但卻不能說是對(duì)龍溪之學(xué)全 面深入的理解。就王畿的本意講,他倒是想極力做到圓滿周全的。比如說 不少人認(rèn)為王畿不重功夫而只講本體,可他分明反對(duì)偏于一方,故曰:“致 知在格物,格物正是致知,實(shí)用力之地,不可以分內(nèi)外者也。若謂工夫只 是致知,而格物無工夫,其流之弊便至于絕物,便是二氏之學(xué)。徒知致知 在格物,而不悟格物正是致其未發(fā)之知,其流之弊便至于逐物,便是支離之 學(xué)。”(同上,《答聶雙江》)正是出于這種考慮,他對(duì)白沙之學(xué)便有自己 的看法,他承認(rèn)明代學(xué)術(shù)的“開端是白沙”,至陽明而大明。(同上,《與 顧沖宇》)但他并未將二者等同,而認(rèn)為白沙不過是孔門別派,其關(guān)鍵在 于白沙只求靜寂,“假靜中一段行持,窺見本來面目,以為安身立命根基”, 這便是“權(quán)法”而非究竟意。而陽明的致良知卻是“不論語默動(dòng)靜,從人 情事變徹底煉習(xí)以歸于玄”,也就是內(nèi)外動(dòng)靜為一,而這才能真正達(dá)到人 生的徹悟。(同上,《霓川別語》)龍溪認(rèn)為這也才真正是圣人之學(xué)。 從此一角度言,“空”與“無”并非是龍溪的最終目的,而是致用之前 提。盡管他多次指出:“空空者,道之體也;”(同上卷六,《致知議略》) “老子曰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同上)但若仔細(xì)體味其“無”之內(nèi)涵, 似有兩種意項(xiàng)構(gòu)成。一是虛之意。他說:“空空即是虛寂,此學(xué)脈也。” (同上)而虛寂的另一面卻是感應(yīng)之用,所謂“虛寂者心之本體,良知知是 知非,原只無是無非,無即虛寂之謂也。即明而虛存焉,虛而明也,即感而 寂存焉,寂而感也;即知是知非而虛寂行乎其間;即體即用,無知而無不 知,合內(nèi)外之道也。若曰本于虛寂而后有知是知非本體之流行,終成二見, 二則息矣。”(《龍溪王先生全集》卷十六,《別贈(zèng)見臺(tái)漫語摘略》)此 “空“此“無”既非無任何內(nèi)容之?dāng)鄿缈眨膊荒塥?dú)立而存在,虛之體的同 時(shí)便是用之明,寂就在感之中,良知具有知是知非的功能便是由于虛寂行乎 其間。王畿曾對(duì)此虛與用之關(guān)系作過多種比喻,或以鏡之虛而能顯其明, 或以口之空而能辨甘苦,或以目之空而能辨黑白,或以耳之空而能辨清濁, 最終歸之于心之空而能辨是非。這是從認(rèn)識(shí)功能上說的,而從境界上說, 虛則體現(xiàn)了圣人與天地同體的胸襟,他說:“老氏曰致虛,又曰谷神,谷 亦虛也。天地間惟萬物,萬物成象于天地之間而無一物能為之礙者,虛故 也。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宰,藐然以一身處乎其間,與萬物相為應(yīng)感,虛 以動(dòng)而出不窮,自然之機(jī)也。”(同上卷十七,《虛谷說》)從語言層面上 看似乎有濃厚的老莊思想色彩,但其目的則是要求具備一種開放的胸襟, 以便與萬物相感通,這其實(shí)又是儒家萬物一體之仁意識(shí)的表現(xiàn)。王畿非常 清楚“世之學(xué)者反以虛之說出于老氏,諱而不敢言”,但他依然敢于冒此 風(fēng)險(xiǎn),是因?yàn)樗钚拧疤斓卮宋唬f物此育,而虛之為用大矣。”(同上) 打通儒釋道而為其心學(xué)體系服務(wù),這正是王畿思想的特征。二是自然之意。 對(duì)此王畿解釋說:“自然之覺即是虛,即是寂,即是無形、無聲,即是虛明 不動(dòng)之體。”(《明儒學(xué)案》卷十二,《致知議辯》)其實(shí),這也是談的良 知之體用問題,在王畿看來,良知雖是自我之主宰,但其本身卻又是空寂 虛無的,在感應(yīng)的過程中,良知固然不能“隨物流轉(zhuǎn)”,因?yàn)槟菍⑹ブ?br> 宰,可又不能離開知覺而有意去把握良知,因?yàn)檫@便是有所“執(zhí)”,而“才 有執(zhí)著,終成管帶”。(同上《答念庵》)所以最佳的狀態(tài)便是忘卻良知主 宰一任其自然而又不違良知天則。用王畿的話說叫做“見在一念,無將迎, 無住著,天機(jī)常活。”(同上《水西別言》)或者叫做“直心以動(dòng),自見天 則。”(同上,《萬履庵漫語》)王畿稱此為“自然良知”,此處的自然包 括了天然現(xiàn)成之本原與自然無礙之感應(yīng)兩個(gè)方面,所以王畿說:“先師良知 之說,仿于孟子不學(xué)不慮,乃天所為自然之良知也。惟其自然之良,不待 學(xué)慮,故愛親敬兄,觸機(jī)而發(fā),神感神應(yīng);惟其觸機(jī)而發(fā),神感神應(yīng),然后 為不學(xué)不慮,自然之良也。”(同上,《致知議略》)此情形猶如珠之走盤, 珠在盤中自然而動(dòng),自由而走,無外力之限制與自身之膠滯,然又決不會(huì) 走出盤外而中止,用孔子的話說即“隨心所欲不逾矩”,而這正體現(xiàn)了王 畿“圓”之特性。 而要達(dá)到本體之虛明與感應(yīng)之自然,就不能沿襲朱子主修主敬的傳統(tǒng) 治學(xué)方法,而必須代之以“悟”。上述所言“不學(xué)不慮”并非是不經(jīng)過任 何過程便可得其自然之良知,而是說不能靠知識(shí)的積累與人為的智慮去獲 得,必須通過悟方可達(dá)此目的。而此悟字最足遭致后人誤解,明末儒者劉 宗周便說龍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懸空期個(gè)悟,終成玩弄光景。”(同 上,《師說》)其實(shí),王畿的本意是說學(xué)要以悟?yàn)殚T徑,而并非是只須悟便 可解決所有問題。應(yīng)該說此種思路是符合陽明的學(xué)術(shù)思路的,陽明論學(xué)也 強(qiáng)調(diào)悟,在如今所保存的幾種天泉證道的資料中,可以說都曾指出了次一 點(diǎn)。拿出入較大的王畿與錢德洪的不同記載相比,便可一目了然。王畿記 陽明之言曰:“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 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 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dāng),即本體便是工夫,簡(jiǎn)易直截,更無剩欠,頓悟之 學(xué)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嘗悟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 物皆從有生,須用為善去惡工夫,隨處對(duì)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于 無,復(fù)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王龍溪先生全集》卷一,《語錄》) 錢德洪則記其師言曰:“我這里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悟入, 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個(gè)未發(fā)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 人己內(nèi)外一齊透了。其次不免有習(xí)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shí)落 為善去惡功夫,熟后渣滓去得盡時(shí),本體亦明盡了。”(《王陽明全集》卷 三,《傳習(xí)錄》下)在此,王畿明確地指出了無論是簡(jiǎn)易直截的頓悟還是 為善去惡的漸修,其最終目的都是要悟得無善無惡之良知本體;錢德洪的 話稍微含糊一些,而所謂“渣滓去得盡時(shí),本體亦明盡了”,也應(yīng)該是漸 修后的透悟。在后來的陽明年譜中,也有“汝中須用德洪功夫,德洪須透 汝中本體”(同上卷三五)的話,可證陽明的確要求漸修之人最終亦須悟 得良知之虛無本體。因而王畿強(qiáng)調(diào)學(xué)要以悟?yàn)殚T徑并未違背陽明之本意。 當(dāng)然,陽明對(duì)王畿只偏于頓悟一途確實(shí)表示過憂慮,說他“只去懸空想個(gè) 本體,一切事為俱不著實(shí),不過養(yǎng)成一個(gè)虛寂,此個(gè)病痛不是小小。”這 是錢德洪的記載,王畿所記無此語,但年譜中亦有此記載,可見是實(shí)有之 言。故而在陽明逝世后王畿便對(duì)其四無說有所糾正,他在《與程方峰》中 說:“天泉證道大意,原是先師立教本旨,隨人根器上下,有悟有修。良 知是徹上徹下真種子,智雖頓悟,行則漸修。”可知他是接受了陽明的勸 告的。但他又有了自己的發(fā)揮創(chuàng)造,這便是顧及兩端而統(tǒng)合之的“圓”之 特征,所以他接著說:“此學(xué)全在悟,悟門不開,無以征學(xué)。然悟不可以 言思期必而得,悟有頓漸,修亦有頓漸。著一漸字,固是放寬;著一頓字, 亦是期必。放寬便近忘,期必又近于助。要之皆任識(shí)神作用,有作有止, 有生有滅,未離生死窠臼,若真信良知,從一念入微承當(dāng),不落揀擇商量, 一念萬年,方是變識(shí)為智,方是師門真血脈路。”(《王龍溪先生全集》卷 十二)他首先承認(rèn)了學(xué)有頓漸二途,此乃其繼承師說處。但他更強(qiáng)調(diào)的是, 學(xué)者須以悟?yàn)殚T徑而斷不能一味執(zhí)著于頓與漸,如果糾纏于漸,那就有放 松自我進(jìn)取的危險(xiǎn),而放松自我進(jìn)取便意味著舍棄心性的修煉,此即為 “忘”;而專執(zhí)于頓,那就有急于求成的急躁之病,而急于求成的急躁便 會(huì)造成揠苗助長(zhǎng)的不良后果。而按王畿的意思,要成功就必須放棄對(duì)頓、 漸的固執(zhí),該頓者即頓,該漸者用漸,最后悟得良知真境界,“變識(shí)為智”, 方可達(dá)到人生的徹悟而學(xué)有所得。如此論學(xué),則顯然是在陽明的基礎(chǔ)上又 有了新的進(jìn)展而更加圓融。 王畿有一首論學(xué)詩曰:“天根寂寂從何起,直須感處觀無始。愧心才 動(dòng)面生丹,哀心乍萌顙溢泚。瑤藏沖開捷有神,莫把真金棄如屣。寂中起 感感歸寂,千圣傳來舊宗旨。路頭差別較些兒,擇術(shù)從教慎函矢。世鮮中 行道益孤,媚俗紛紛亂朱紫。夫君自是儒中英,好向毫厘辨千里。”(同上 卷十八,《再用韻論學(xué)一首》)良知之體本寂,但須于感處觀之,寂中可以 起感而感亦必歸于寂,兩端兼顧,體用雙彰,此方可得大道之中行而不滯 于一偏。可見王畿本人是有自覺的求“圓”意識(shí)的。 |
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
版權(quán)所有 北京國(guó)學(xué)時(shí)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Copyright©2000
國(guó)學(xué)網(wǎng)站,版權(quán)專有;引用轉(zhuǎn)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quán)。
國(guó)學(xué)網(wǎng)站,版權(quán)專有;引用轉(zhuǎn)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q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