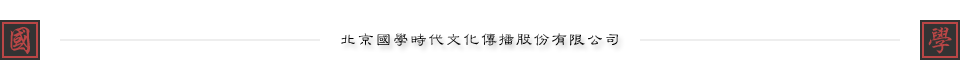文史結(jié)合,史論兼具———從《唐代科舉與文學(xué)》看傅璇琮先生的治學(xué)方法
【摘 要】《唐代科舉與文學(xué)》一書將科舉作為研究之中介,把它與文學(xué)溝通起來,運(yùn)用文史結(jié)合的治學(xué)方法綜合考察唐代文學(xué)與科舉的關(guān)系。其文史結(jié)合的治學(xué)方法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gè)方面:一、作者對(duì)每一問題的論述都以史料為基礎(chǔ),經(jīng)過對(duì)大量原始資料的分析和鑒別之后他才得出結(jié)論。二、注重對(duì)一特定時(shí)代知識(shí)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和心理狀態(tài)做歷史的分析,以展現(xiàn)特定歷史背景下文學(xué)的面貌。三、反過來以詩、文等文學(xué)作品來明確科舉史中存疑的地方。
傅璇琮先生是當(dāng)今古典文學(xué)界非常有影響的學(xué)者之一,也是我深深敬仰的學(xué)界前輩。傅先生的學(xué)問很深,學(xué)術(shù)成果頗豐。近年來他的學(xué)術(shù)研究受到古典文學(xué)界的廣泛關(guān)注,產(chǎn)生了極大影響。羅宗強(qiáng)先生在為傅先生的《唐詩論學(xué)叢稿》(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所做的序中將它界定為“文學(xué)社會(huì)歷史學(xué)研究”,而陳允吉先生為同一本書所作的另一序言中將它稱之為“文學(xué)的歷史文化研究”。無論是“文學(xué)社會(huì)歷史學(xué)研究”,還是“文學(xué)的歷史文化研究”,其中運(yùn)用的一個(gè)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文史結(jié)合。這種方法先生自己說得再明白不過了:“這種方法,就是試圖通過史學(xué)與文學(xué)的相互滲透或溝通,掇拾古人在歷史記載、文學(xué)描寫中的有關(guān)社會(huì)史料,做綜合的考察……”[1]《唐代科舉與文學(xué)》是運(yùn)用這一治學(xué)方法寫出來的代表性著作,這一點(diǎn)已得到學(xué)術(shù)界的一致認(rèn)可。對(duì)于這一點(diǎn)先生自己也是很提倡的,他說:“近二十年來我們唐代文學(xué)研究之所以有如此大的進(jìn)展,是不少學(xué)者注意將文學(xué)研究與史學(xué)研究結(jié)合起來。有史學(xué)研究的扎實(shí)基礎(chǔ),就能使文學(xué)作品的涵義理解得更為深切、豐滿,否則就很容易泛泛而談,雖然詞句很美麗,構(gòu)思很機(jī)巧,但往往會(huì)在基本史實(shí)方面出差錯(cuò),從而降低了整篇文章或整部著作的品位。”[2]
《唐代科舉與文學(xué)》這本書共三十七萬字,1986年由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書共十七章,分別是:材料敘說、唐登科記考索、總論唐代取士各科、鄉(xiāng)貢、舉子到京后活動(dòng)概說、明經(jīng)、制舉、進(jìn)士考試與及第、進(jìn)士出身與地區(qū)、知貢舉、進(jìn)士行卷與納卷、進(jìn)士放榜與宴集、舉子情狀與科場風(fēng)習(xí)、唐人論進(jìn)士試的弊病及改革、進(jìn)士試與文學(xué)風(fēng)氣、進(jìn)士試與社會(huì)風(fēng)氣、學(xué)校與科舉、吏部銓試與科舉。在這些章節(jié)中,作者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充實(shí)他所講述的內(nèi)容。其中進(jìn)士試是作者論述的重點(diǎn),因?yàn)檫M(jìn)士試在唐代科舉中的地位最高,與文學(xué)的關(guān)系最密切,對(duì)舉子生活的影響也是最深遠(yuǎn)的。作者自述:“我的重點(diǎn)是考察唐代士人在登第以前或落第以后的生活情景,至于登第以后如何通過吏部銓選進(jìn)入仕途,則只用最后一章(第十七章《吏部銓試與科舉》)加以概述。”[2]可見作者在將科舉制度作為文化史的一種進(jìn)行研究的時(shí)候是緊緊圍繞文學(xué)這個(gè)中心展開的。作者傅璇琮先生是精通文史的,在這本書中他的文史結(jié)合的治學(xué)方法得到了充分體現(xiàn),我是從以下幾個(gè)方面來理解他的這種治學(xué)方法的。
一、作者對(duì)每一問題的論述都以史料為基礎(chǔ),經(jīng)過對(duì)大量原始資料的分析和鑒別之后他才得出結(jié)論。
文史結(jié)合就意味著在研究的過程中必須以史為基礎(chǔ),在尊重史實(shí)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研究,而不是從想當(dāng)然出發(fā),作看似概括性強(qiáng)而實(shí)為虛擬的推想。傅先生對(duì)史這一方面是很看重的,他在《于平實(shí)中創(chuàng)新———記臺(tái)灣學(xué)者羅聯(lián)添先生的治學(xué)成就》一文中說:“澄其源,就是探尋問題的原始材料究竟如何,應(yīng)當(dāng)對(duì)原始材料做準(zhǔn)確的搜討與把握,而不應(yīng)以后起的或已變化過的材料當(dāng)作原始材料。清其流,就是從最初的起因出發(fā),不帶任何個(gè)人愛好與偏見,把由原始材料生發(fā)的種種解釋、議論、記載,按照事物本身發(fā)展加以清理,惟有這樣,才能對(duì)課題的縱向發(fā)展與橫向聯(lián)系有一個(gè)歷史的全面的概括,而由此得出的結(jié)論,才會(huì)有充實(shí)的材料基礎(chǔ)。”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傅先生做學(xué)問的嚴(yán)謹(jǐn)態(tài)度。在《唐代科舉與文學(xué)》一書中,傅先生提供了大量的原始材料用以佐證他的觀點(diǎn),這些史料的來源面非常廣泛,不囿于一兩本書。本書使用的主要史料除了清代徐松的《登科記考》外,還包括《新唐書》、《唐摭言》、《蔡寬夫詩話》、《封氏聞見記》、《文苑英華》、《玉海》、《文獻(xiàn)通考》等幾十種之多,這些史料都是第一手材料。作者在論述問題時(shí)非常重視對(duì)這些史料的考訂,真正做到了以史實(shí)為基礎(chǔ),用事實(shí)說話。如第六章講到制舉的地位時(shí),為了證明制舉在唐人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先生除了引用《李娃傳》中的一段話和清人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的一段話,在這節(jié)的末尾又舉出了《通鑒》卷二三七、陳子昂《唐水衡監(jiān)丞李府君墓志銘》、陳子昂《周故內(nèi)供奉學(xué)士懷州河內(nèi)縣尉陳君碩人墓志銘》、張說《河州刺史冉府君神道碑和皇甫冉送錢塘路少府赴制舉》多個(gè)例子證明。又如第五章第二節(jié)講到明經(jīng)科是否也起源于隋的問題時(shí)首先列出《通鑒》中的一則材料,根據(jù)胡三省注明經(jīng)科起于隋,《舊唐書·孔穎達(dá)傳》中的一則材料也表明明經(jīng)科起于隋。但作者指出“僅憑以上所舉兩《唐書》和《通鑒》的材料,還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3](P113)根據(jù)《唐摭言》卷一和卷十五的明確表述作者斷定作為科舉制度的明經(jīng)科同進(jìn)士科一樣在唐代起于高祖武德五年,隋朝的明經(jīng)科屬于科舉制度還是屬于察舉制度還不甚清楚。在這里,如果作者輕信兩《唐書》和《通鑒》的材料不僅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jié)論,還會(huì)在基本史實(shí)方面出錯(cuò),從而影響整本書的價(jià)值。詳盡地占有資料,并對(duì)資料作細(xì)致地分析和整理,有這樣扎實(shí)的史料基礎(chǔ)做保證得出來的結(jié)論自然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由此我們也可見出老一輩學(xué)者在做學(xué)問過程中腳踏實(shí)地、嚴(yán)肅認(rèn)真的態(tài)度。
有扎實(shí)的史料考證,這并不意味著《唐代科舉與文學(xué)》是一本枯燥的考據(jù)之書。它決不是索然無味的史料的堆積,它是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礎(chǔ)上得出具有學(xué)術(shù)價(jià)值的觀點(diǎn)。純粹的史料考訂是稱不上文史結(jié)合的。這本書只是將科舉作為研究的中介和橋梁,它的最終目的還是對(duì)關(guān)涉科舉的文學(xué)的研究。作者通過考證唐初進(jìn)士科的考試內(nèi)容得出“以詩賦取士”促進(jìn)了唐詩的繁榮這一觀點(diǎn)不合理的結(jié)論。他通過《通典》和《文苑英華》的材料證明在唐初一個(gè)相當(dāng)長的時(shí)期內(nèi),進(jìn)士考試是與詩賦無關(guān)的,到了高宗后期,武則天實(shí)際掌握政權(quán)時(shí)進(jìn)士試才由試策文一場變?yōu)樵囂?jīng)、雜文、策文三場。到了天寶年間,雜文才專用于詩賦。而在這時(shí),唐詩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了一個(gè)相當(dāng)高的階段了,不僅走過了初唐,也已步入了盛唐的階段,而杰出的詩人如“初唐四杰”、陳子昂、李白、杜甫、王維等已相繼登上了詩壇,可見唐詩的繁榮與試詩賦并無直接關(guān)系。從史料出發(fā),經(jīng)過詳細(xì)考訂得出一個(gè)有意義的結(jié)論,這表明作者文史結(jié)合的治學(xué)方法不僅落到了實(shí)處,而且體現(xiàn)了其優(yōu)越的地方。
二、注重對(duì)一特定時(shí)代知識(shí)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和心理狀態(tài)做歷史的分析,以展現(xiàn)特定歷史背景下文學(xué)的面貌。
傅先生在《唐代科舉與文學(xué)》中體現(xiàn)的文史結(jié)合不僅在于其扎實(shí)的史料和考證基礎(chǔ),也在于其在寫作過程中歷史的眼光和歷史的分析手法。他對(duì)法國藝術(shù)史家丹納在《藝術(shù)哲學(xué)》中提出的重視種族、環(huán)境和社會(huì)習(xí)俗對(duì)于文學(xué)藝術(shù)有重大影響的觀點(diǎn)十分贊賞,同時(shí)他也經(jīng)常提到丹麥文學(xué)史家勃蘭兌斯《十九世紀(jì)文學(xué)主潮》中的名言:“文學(xué)史,就其深刻的意義來說,是一種心理學(xué),是研究人的靈魂,是靈魂的歷史。”這些觀點(diǎn)對(duì)先生影響很大,是他在寫作《唐代科舉與文學(xué)》一書時(shí)能從歷史的角度出發(fā),用歷史的眼光進(jìn)行分析,展現(xiàn)特定的時(shí)代背景和社會(huì)習(xí)俗對(duì)文學(xué)的影響。他還特別關(guān)注唐代舉子們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和心理狀態(tài),對(duì)這一群體生活的歷史文化背景及他們的命運(yùn)他都有詳細(xì)的論述。
傅先生認(rèn)為科舉制度“牽連著社會(huì)上各個(gè)階層知識(shí)分子的命運(yùn)。研究科舉在唐朝的發(fā)展,事實(shí)上就研究了當(dāng)時(shí)大部分知識(shí)分子的生活道路。”[1]其實(sh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科舉在唐代的發(fā)展史也就是唐代舉子們的生活史。基于這個(gè)原因,傅先生注重對(duì)唐代舉子們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和心理狀態(tài)作歷史的分析,將一部舉子們的生活風(fēng)俗畫展現(xiàn)在人們面前。本書從第三章鄉(xiāng)貢開始詳細(xì)地?cái)⑹雠e子們參加考試的整個(gè)過程,從被選拔上京考試、考前一些活動(dòng)直至發(fā)榜之后的宴集。在這個(gè)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那個(gè)時(shí)代知識(shí)分子們在科舉道路上的艱難跋涉。第四章第三節(jié)講元日引見,即舉子們在元旦那一天接受皇帝接見,因?yàn)樘迫藳]有文字記載當(dāng)時(shí)的具體情況,不得其詳。為了讓讀者身臨其境地體會(huì)當(dāng)時(shí)那種情狀,傅先生引用了北宋中葉沈括的一段記敘,寫得很風(fēng)趣,可以作為參考:
舊制,天下貢舉人到闕,悉皆入對(duì),數(shù)不下三千人,謂之“群見”。遠(yuǎn)方士皆未知朝廷儀范,班列紛錯(cuò),有司不能繩勒。見之日,先設(shè)禁圍于著位之前,舉人皆拜于禁圍之外,蓋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座者。有司患之。近歲遂止令解頭入見,然尚不減數(shù)百人。嘉祐中予忝在解頭,別為一班,最在前列,目見班中唯從前一兩行,稍應(yīng)拜起之節(jié),自余亦終不成班綴而罷,每為閣門之累。常言殿廷中班列不可整齊者,唯有三色,謂舉人、蕃人、駱駝。(《夢溪筆談》卷九)
作者在這段之后說:“沈括把舉人與駱駝并提,詼諧帶有挖苦,把一些從遠(yuǎn)方來的讀書人不識(shí)禮儀、搶先恐后的紛亂情狀,描寫得極為傳神。”作者就是這樣通過極為有限的材料努力展示那個(gè)時(shí)代舉子們辛酸與悲苦的境遇。其中寫到一個(gè)老秀才一直考到老而未中,有一年除夕夜忽發(fā)奇想,想入宮窺看進(jìn)儺的情況。他被人帶進(jìn)去卻被當(dāng)作一般樂人看待,跌跌撞撞,低頭什么也不敢看。這樣折騰一夜,第二天早上回到住處,連病了六十天,錯(cuò)過了這一年的考試。這樣一個(gè)失意老秀才的悲慘境遇放入《儒林外史》中也毫不遜色。通過作者給我們提供的這些材料,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那個(gè)時(shí)代的知識(shí)分子所受到的包括科舉制在內(nèi)的各種物質(zhì)和精神的壓力是何等沉重。有了這樣的體會(huì),我們再來讀韓愈《與李翱書》中那一段傳誦的名句會(huì)感到字字包含著血淚:
仆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于人以度時(shí)月。當(dāng)時(shí)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dāng)痛之時(shí),不知何能自處也。(《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三)
傅先生在提供豐富材料展示舉子生活道路和心理狀態(tài)的同時(shí),他往往也會(huì)用同情的筆調(diào)抒寫自己的感受,這種感受是將自己融入到那些舉子當(dāng)中,站在那個(gè)時(shí)代立場上去體會(huì)的結(jié)果,看來古往今來的讀書人對(duì)讀書考功名所經(jīng)歷的酸甜苦辣的感受是相通的。同情只是一方面,更多的則是對(duì)這種狀況作歷史地分析。同樣是第十二章,針對(duì)科場中的腐敗風(fēng)習(xí),傅先生冷靜地指出;“一般地說,作為封建社會(huì)選拔官吏制度的科舉制,作為地主階級(jí)國家的一項(xiàng)政治設(shè)施,無論它怎樣嚴(yán)格防范,漏洞是不可能堵塞的,因?yàn)樗旧硎且环N私有制的產(chǎn)物,它是適應(yīng)地主階級(jí)的政治需要產(chǎn)生的,絕不可能杜絕走私舞弊等腐敗風(fēng)氣。明清時(shí)期,尤其是清代,科場禁制十分嚴(yán)密,但科場案仍不時(shí)有所揭發(fā),更不用說數(shù)量大得多的未被揭發(fā)的種種走私行為了。特殊地說,在唐代,科舉制度還處于初級(jí)階段,它仍不免帶有前一歷史時(shí)期薦舉制和九品中正制的某些痕跡……在這樣總的社會(huì)情勢下,科舉取士也呈現(xiàn)出種種腐敗的惡劣的風(fēng)氣,那是必然的。”[3](P357-358)這段分析體現(xiàn)出作者歷史的眼光,他設(shè)身處地站在那個(gè)時(shí)代考慮問題,并不苛求古人,我想這樣才是對(duì)那個(gè)時(shí)代歷史面貌的真實(shí)反映。
三、反過來以詩、文等文學(xué)作品來明確科舉史中存疑的地方。
“以文證史”也是文史結(jié)合的一種表現(xiàn)方式,傅先生的文史結(jié)合在這方面也有所體現(xiàn)。因?yàn)槭妨系那啡保詫?duì)于唐代科舉的不少細(xì)節(jié)問題至今不太清楚或缺少定論,傅先生在《唐代科舉與文學(xué)》中經(jīng)常運(yùn)用信手拈來的詩句補(bǔ)充史料的不足。如第十一章進(jìn)士放榜與宴集第一節(jié)講進(jìn)士放榜時(shí)的情況時(shí)引用了韋莊《放榜日作》、李旭《及第后呈朝中知己》中的詩句,張鷟《朝野僉載》中的記載和晚唐人康駢在《劇談錄》中記載的一則小故事,通過這些詩和文的記載我們對(duì)進(jìn)士放榜過程中的種種細(xì)節(jié)和情狀就了解得非常清楚了。另外對(duì)于放榜的時(shí)間,根據(jù)歷史的記載通常是在二月,但具體在二月哪一天不太清楚,傅先生從白居易和柳宗元的文章中推知出了具體哪一天放榜。白居易有一篇《省試性習(xí)相遠(yuǎn)近賦》(《白居易集》卷三十八)題下自注說:“貞元十六年二月十四日及第,第四人。”這篇賦是在禮部試雜文時(shí)所作,題下小注是白居易在放榜以后追加的。從這里可以知道唐德宗貞元十六年進(jìn)士放榜的日子是二月十四日。柳宗元有《送苑論登第后歸覲詩序》(《柳宗元集》卷二十二)說:“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于南宮,余與兄又聯(lián)登焉。”據(jù)徐松《登科記考》卷十三載,柳宗元與苑論同于貞元九年登進(jìn)士第;又據(jù)陳垣《二十史朔閏表》,貞元九年二月丙子為二月二十七日,由此知這一年放榜時(shí)間為二月二十七日。對(duì)于放榜的具體時(shí)間史料中似未記載,傅先生也是從時(shí)人的詩句中推出來的。黃滔有“五更桂苑聽榜后”(《二月二日宴中貽同年先輩渭》)、“仙榜標(biāo)名出曙霞”(《放榜日》)(《唐黃御史公集》卷三);劉滄有“禁漏初定蘭省開,列仙名目上清來。飛鳴曉日鶯聲遠(yuǎn),變化春風(fēng)鶴影回。”(《看榜日》、《全唐詩》卷五八六)從以上這些詩句可以看出放榜的時(shí)間是在一天之中的清晨。通過對(duì)當(dāng)時(shí)人詩、文等文學(xué)作品的考察,傅先生明確了關(guān)于放榜的一系列細(xì)節(jié)問題,這些問題在史料中是少有記載的,而他們對(duì)于全章乃至全書來說又是不可或缺的。這樣“以文證史”不失為一種很好的考證方法,可以為我們所借鑒。
傅先生以科舉為中介運(yùn)用文史結(jié)合的治學(xué)方法寫成《唐代科舉與文學(xué)》,這一寫作思路在八十年代中期為學(xué)術(shù)開辟了一塊新的可耕地。在這塊土地上,有一些學(xué)者已仿照他的寫作思路、學(xué)習(xí)他的治學(xué)方法作類似的研究,王勛成《唐代銓選與文學(xué)》(中華書局2001年4月版)便是很好的一例。這種治學(xué)方法為唐代文學(xué)乃至整個(gè)古典文學(xué)的研究注入了生機(jī)和活力,我們后學(xué)者還可用這一好工具在自己的研究領(lǐng)域挖掘出更多的東西。
參考文獻(xiàn)
[1]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xué)》序[A].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3.
[2]傅璇琮.《唐代銓選與文學(xué)》序[J].蘭州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1,(3).
[3]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xué)[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