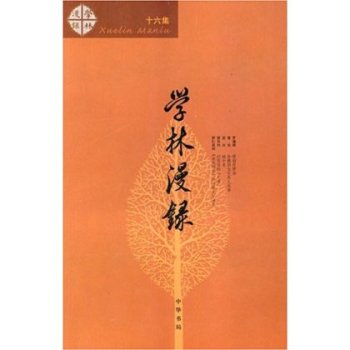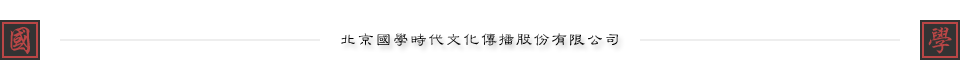傅璇琮:《學(xué)林漫錄》憶舊及其他
我于1951年秋入清華大學(xué)中文系求學(xué),至1952年8月,隨我國(guó)高等學(xué)校院系大調(diào)整而就讀于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三年后畢業(yè)留校,擔(dān)任浦江清先生主講的“宋元明清文學(xué)史”課的助教。本以為就此可以在大學(xué)教學(xué)和科研的坦途上前進(jìn)了,不料在1958年年初,因所謂的“同人刊物”問(wèn)題,與樂(lè)黛云、褚斌杰、裴斐和金開(kāi)誠(chéng)等人一起被誣為“右派集團(tuán)”而身心俱受打擊。
1958年3月,我從北京大學(xué)被貶逐至商務(wù)印書(shū)館。我在北大是教書(shū),只不過(guò)三四年,而且那時(shí)只是個(gè)助教,跑腿兒的機(jī)會(huì)多,真正上堂講課不過(guò)少數(shù)幾次;到出版社是編書(shū),倒是每天與書(shū)打交道了(當(dāng)然,“文化大革命”中有幾年除外),編書(shū)生涯占去了一生中的大半輩子。但現(xiàn)在稍稍作一些回顧,編出的書(shū)真能愜意的,卻也似乎不多。能說(shuō)得過(guò)去的,我覺(jué)得只有《學(xué)林漫錄》叢刊那一種。
到“商務(wù)”那會(huì)兒,也不過(guò)是二十五六歲的青年,但自我感覺(jué)似乎已入“中年”。那時(shí)“商務(wù)”在北總布胡同10號(hào),由幾個(gè)四合院組成,都是平房。
我所在的古籍編輯室,正好是在北屋西頭,面對(duì)的是一個(gè)頗為典雅幽靜的小院子。室主任吳澤炎先生打算在由云龍舊編的基礎(chǔ)上重編《越縵堂讀書(shū)記》,他可能覺(jué)得需要一個(gè)幫手,也或許看到我剛從大學(xué)出來(lái),得收收心,就叫我?guī)退鲞@件事。
步驟是將由云龍的舊編斷句改成新式標(biāo)點(diǎn),并再?gòu)睦钤娇z的日記中補(bǔ)輯舊編所遺漏的部分。李慈銘也可以算是我的鄉(xiāng)先輩,大學(xué)念書(shū)時(shí)讀《孽海花》,對(duì)書(shū)中所寫(xiě)的他那種故作清高的名士派頭感到可笑,但對(duì)他的認(rèn)識(shí)也僅此而已,現(xiàn)在是把讀他的日記當(dāng)作一件正經(jīng)工作來(lái)做了,對(duì)這位近代中國(guó)士大夫中頗具代表性的人物及其坎坷遭遇了解稍多,竟不免產(chǎn)生某種同情。我雖然頭上已戴了“帽子”,但那時(shí)對(duì)腦子里的“東西”卻似乎還拘查得不嚴(yán)。
我是住集體宿舍的,住所就在辦公室后面一排較矮的平房里,起居十分方便。一下班,許多有家的人都走了,我就搬出一張?zhí)僖危诶认拢鎸?duì)院中滿栽的牡丹、月季之類(lèi),就著斜陽(yáng)余暉,手執(zhí)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線裝本《越縵堂日記》,一面瀏覽其在京中的行蹤,一面細(xì)閱其所讀的包括經(jīng)、史、子、集的各類(lèi)雜書(shū),并在有關(guān)處夾入紙條,預(yù)備第二天上班時(shí)抄錄,真有陶淵明“時(shí)還讀我書(shū)”的韻味,差一點(diǎn)兒忘記了自己的“罪人”身份。
但好景不長(zhǎng),1958年7月,由于幾個(gè)老牌出版社“專(zhuān)業(yè)分工”的確定,我又被調(diào)轉(zhuǎn)至中華書(shū)局,隨即轉(zhuǎn)入紛繁的編書(shū)生涯,“商務(wù)”那段短暫而悠閑的生活結(jié)束了,從此,“此情可待成追憶”(李商隱《錦瑟》語(yǔ))了。
當(dāng)時(shí)的中華書(shū)局總編輯金燦然告誡我:“你就在工作中好好改造吧,安心看稿。”他懂得愛(ài)惜專(zhuān)業(yè)人才,并不讓我去“下放勞動(dòng)”,而是把我圈在作者的書(shū)稿中,專(zhuān)致于編輯業(yè)務(wù)。我為審讀有關(guān)書(shū)稿,就上自《詩(shī)經(jīng)》下至《人境廬集外詩(shī)》地翻閱了不少書(shū)。
按照我當(dāng)時(shí)政治處境,是不能寫(xiě)文章往外發(fā)表的,于是我白天審讀、加工稿件,晚上看我要看的書(shū)。當(dāng)時(shí)我處理陳友琴先生的《白居易詩(shī)評(píng)述匯編》,我提議由中華書(shū)局搞一套“中國(guó)古典作家研究資料匯編”,領(lǐng)導(dǎo)同意這一方案,于是把陳先生的這部書(shū)改名為《中國(guó)古典作家研究資料匯編·白居易卷》……我自己就搞《黃庭堅(jiān)與江西詩(shī)派卷》和《楊萬(wàn)里范成大卷》。
我平時(shí)從中華書(shū)局圖書(shū)館借書(shū),夜間翻閱。每逢星期天,則到文津街的北京圖書(shū)館看一天書(shū),中午把早晨所帶的饅頭伴著圖書(shū)館供應(yīng)的開(kāi)水當(dāng)一頓午飯。我的近二十萬(wàn)字的《楊萬(wàn)里范成大研究資料匯編》和七十余萬(wàn)字的《黃庭堅(jiān)與江西詩(shī)派研究資料匯編》,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編出來(lái)的,這也就是我真正做研究工作的起點(diǎn)。我沒(méi)有荒廢時(shí)間。
我那時(shí)就想嘗試一下,在出版部門(mén)長(zhǎng)期當(dāng)編輯,雖為他人審稿、編書(shū),當(dāng)也能成為一個(gè)研究者。我們要為編輯爭(zhēng)氣,樹(shù)立信心:出版社是能出人才的,編輯是能成為專(zhuān)家學(xué)者的。
《楊萬(wàn)里范成大卷》于1964年出版,《黃庭堅(jiān)與江西詩(shī)派卷》亦于1978年出版。關(guān)于山谷研究資料一卷,我曾寄送錢(qián)鍾書(shū)先生,以求指正,且當(dāng)時(shí)亦未識(shí)得荊州。不久即收到錢(qián)先生賜函,得悉錢(qián)先生已閱過(guò)《楊萬(wàn)里范成大卷》,有獎(jiǎng)褒后學(xué)之厚意,更使我堅(jiān)定走編輯學(xué)者化的道路。錢(qián)先生函摘錄如下:
璇琮先生著席:
十?dāng)?shù)年前得見(jiàn)尊纂石湖資料,博綜精審,即嘆可懸諸國(guó)門(mén),為茲事楷模……心儀已久,頃奉惠頒新著,望而知為網(wǎng)羅無(wú)遺之巨編,沾丐何極。山谷句云:能與貧人共年谷。斷章以謝隆情厚賜,亦本地風(fēng)光也。先此布懷,書(shū)不盡意,即祝起居安隱,文章富有。
錢(qián)鍾書(shū)上,二十六日。
李文饒言好驢馬不入行,研究所乃驢馬行耳。一笑。
應(yīng)當(dāng)說(shuō),中華書(shū)局三十年的工作,打下了我做學(xué)問(wèn)的底子。我始終對(duì)這個(gè)環(huán)境是有感情的。我在《唐代詩(shī)人叢考》(中華版)2003年重印時(shí)的“重印題記”中說(shuō)過(guò):我在編輯工作中學(xué)到了那時(shí)大學(xué)環(huán)境中學(xué)不到的許多實(shí)在學(xué)問(wèn),這也得力于中華書(shū)局在學(xué)術(shù)界的特殊位置。但后來(lái)卻又受到一種莫名其妙的壓抑、欺凌,以及因所謂世態(tài)炎涼而致的落井下石的遭遇。但我這個(gè)人畢竟是個(gè)書(shū)生,從上世紀(jì)50年代起,不管環(huán)境如何,總是抓時(shí)間讀書(shū)作文。
不過(guò),頭幾年的事務(wù)也確實(shí)叢雜得夠嗆。
剛到中華書(shū)局文學(xué)編輯室,即碰到新編唐詩(shī)三百首之事。在1958年的大浪潮中,對(duì)古人一切都要推倒重來(lái),說(shuō)是清代乾隆年間蘅塘退士的《唐詩(shī)三百首》“美化封建社會(huì)”,對(duì)今天的讀者毒素很大,我們要新編一本來(lái)加以“消毒”。新編當(dāng)然無(wú)可厚非,問(wèn)題是依據(jù)什么“標(biāo)準(zhǔn)”。既然舊編“美化封建”,我們現(xiàn)在就要反舊編之道而行之,揭露封建社會(huì)的黑暗面。于是以民間作品為主,把相傳為黃巢的“反詩(shī)”以及民歌民謠優(yōu)先選入,再收白居易、杜荀鶴等所謂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
編輯室內(nèi)屢次為某些作品入選與否爭(zhēng)來(lái)爭(zhēng)去,編輯室一位副主任,可稱(chēng)“三八式”干部,后來(lái)總結(jié)這次新編的工作,認(rèn)為自始至終貫串“兩條路線”的斗爭(zhēng),無(wú)疑是把我和其他幾位列入錯(cuò)誤路線中去的。她解放前曾在鄧拓手下做過(guò)事,有老交情,于是請(qǐng)鄧拓當(dāng)顧問(wèn),這本“新編”的前言即出于鄧拓之手。當(dāng)時(shí)大家都洋洋自得,認(rèn)為牌子硬。
殊不料“福兮禍所伏”,1966年上半年批“三家村”時(shí),把《新編唐詩(shī)三百首》也揭發(fā)出來(lái)了,說(shuō)是鄧拓借選詩(shī),把唐詩(shī)中描寫(xiě)黑暗的作品大量選入,是借此攻擊“大躍進(jìn)”、“總路線”,把一個(gè)好端端的新中國(guó)搞得暗無(wú)天日、一塌糊涂。
那時(shí)我還在河南安陽(yáng)農(nóng)村搞“四清”,春夜靜寂時(shí),讀到《人民日?qǐng)?bào)》上的這一揭發(fā)批判文章,真是驚得目瞪口呆。因?yàn)槲沂菂⑴c者,明明白白知道詩(shī)是編輯室內(nèi)的人選的,只不過(guò)選成后鄧拓看看,怎么忽而變成是鄧拓選的了,而且是鄧拓借此而作為“反黨反社會(huì)主義的工具”了!安陽(yáng)是殷墟的舊地,甲骨文是我們文明的老祖宗,我倚伏于中原大地上一個(gè)農(nóng)家的昏微燈光下,面對(duì)著這篇“檄文”,真感慨于我們古老的歷史傳統(tǒng)中一種可怕陰森的東西。
《新編唐詩(shī)三百首》工作于1958年10月間結(jié)束,隨即轉(zhuǎn)入雜務(wù)。記得我剛進(jìn)中華書(shū)局時(shí),一位編輯室主任曾給我一部明季抗清的文臣寫(xiě)的文稿《邢襄奏稿》和《樞垣初刻》,叫我寫(xiě)一篇“出版說(shuō)明”;后來(lái)還經(jīng)手過(guò)顧頡剛先生標(biāo)點(diǎn)的清人姚際恒的《詩(shī)經(jīng)通論》;第三部是《顧亭林詩(shī)文集》,除了通閱、標(biāo)點(diǎn)外,還要各寫(xiě)數(shù)千字的有評(píng)析的說(shuō)明文字。1958年至1959年間文教戰(zhàn)線“拔白旗、插紅旗”,北大中文系師生編了一部陶淵明研究資料匯編,編輯室領(lǐng)導(dǎo)又命我做該書(shū)的責(zé)任編輯。而自60年代初期起,我又參加“二十四史”的校點(diǎn)。這樣的一種上下千余年的工作,對(duì)于像我這樣不到三十歲的人來(lái)說(shuō),也可以說(shuō)是一種“鍛煉”,但它們對(duì)于我也是一種事業(yè)上的興趣,并不只是作為一種“任務(wù)”,我在理智上覺(jué)得應(yīng)當(dāng)把它做好。
而對(duì)于《學(xué)林漫錄》,則完全是出于一種趣味上的愛(ài)好。1979年至1980年間,我任中華書(shū)局古代史編輯室副主任。由于工作關(guān)系,我在古典文學(xué)界之外,又結(jié)識(shí)了歷史學(xué)界不少老年和中年學(xué)者,交友面比過(guò)去稍廣了。我感到史學(xué)界的研究者,專(zhuān)業(yè)性似乎比古典文學(xué)界為強(qiáng),對(duì)學(xué)術(shù)課題鉆研較深,但他們與古典文學(xué)界中一些朋友一樣,大多希望在專(zhuān)業(yè)范圍之外,瀏覽一些雖然也是學(xué)術(shù)問(wèn)題卻比較輕松的漫談式的文章。這時(shí),我正好從朋友處看到香港出版的《藝林叢錄》,受到啟發(fā),覺(jué)得不妨也編這樣一種不定期的學(xué)術(shù)小品集。這正是《學(xué)林漫錄》初集“編者的話”所說(shuō)的緣起:
不少文史研究者或愛(ài)好者,愿意在自己的專(zhuān)業(yè)領(lǐng)域內(nèi),就平素所感興趣的問(wèn)題,以隨意漫談的形式,談一些意見(jiàn),抒發(fā)一些感想。而不少讀者,也希望除了專(zhuān)門(mén)論著之外,還可讀到學(xué)術(shù)性、知識(shí)性、趣味性相結(jié)合的作品,小而言之,可資談助,大而言之,也可以擴(kuò)大知識(shí)面,開(kāi)闊人們的眼界,啟發(fā)人們的思想,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學(xué)林漫錄》的出版,正是為了適應(yīng)這樣的要求。
至于編選的宗旨,仍用“編者的話”說(shuō)便是:
《學(xué)林漫錄》的編輯,擬著重于“學(xué)”和“漫”。所謂“學(xué)”,就是說(shuō),要有一定的學(xué)術(shù)性,要有一得之見(jiàn),言之有物,不是人云亦云,泛泛而談,如顧炎武所說(shuō)的“廢銅”。所謂“漫”,就是上面說(shuō)過(guò)的不拘一格的風(fēng)格與筆調(diào)。杜甫在他定居于成都時(shí),寫(xiě)了一首《江上值水如海勢(shì)聊短述》的七律,有這樣兩句:“老去詩(shī)篇渾漫與,春來(lái)花鳥(niǎo)莫深愁。”是很有意義的。杜甫在他后期,詩(shī)律是愈來(lái)愈細(xì)了,但自己卻說(shuō)是“漫與”,似乎是說(shuō)詩(shī)寫(xiě)得不怎么經(jīng)心了。這是不是謙詞呢?不是。老杜經(jīng)歷了大半生的戎馬戰(zhàn)亂,在離亂的生活中積累了豐富的實(shí)踐知識(shí),稍有閑暇,又讀了不少書(shū),只有在這樣的深厚的基礎(chǔ)上,才能寫(xiě)出“渾漫與”三字,就是說(shuō),看來(lái)不經(jīng)心,其實(shí)正是同一篇詩(shī)中所說(shuō)的“語(yǔ)不驚人死不休”的。拿杜甫這首詩(shī)中的詩(shī)句,來(lái)為我們這本書(shū)的“漫”字作注腳,恐怕是合適的。
其時(shí),黃裳先生是刊物的作者與讀者之一,他曾來(lái)信鼓勵(lì)說(shuō):
刊物印刷裝幀皆佳,雖出版少遲,亦可滿意也。尊撰“大政方針”極是,近來(lái)“正經(jīng)”學(xué)術(shù)刊物甚多,然質(zhì)量殊不足與招牌相符。原因可能是人材寥落,后繼者少。魯迅有言,不妨大家降一級(jí)試試看,即試寫(xiě)此種小文,不端架子,反能少有新意,亦未可知,不知以為如何。
《學(xué)林漫錄》第一集出版于1980年6月。這一集是我一個(gè)人編的,籌備了大約半年,向一些文史界相識(shí)師友組稿。先是向我素所敬仰的啟功先生索文,他欣然先寫(xiě)兩篇,一是《記齊白石先生軼事》,一是《堅(jiān)凈居題跋》。啟功先生的這兩篇可以說(shuō)是代表《學(xué)林漫錄》的兩大部分內(nèi)容,就是記述近代有建樹(shù)的學(xué)者、作家、藝術(shù)家事跡的文章,以及包括各種內(nèi)容的學(xué)術(shù)小品。這在當(dāng)時(shí),對(duì)不少讀者來(lái)說(shuō),都有一種新鮮感,因此,頗受文史界以及其他行業(yè)中人的歡迎。正如第三集的“編者的話”所說(shuō):
讀者歡迎已出的初集和二集,大約就在它的別具一格吧。所謂別具一格,從內(nèi)容上說(shuō),就是所收文章的面較寬。舉凡近當(dāng)代一些學(xué)者、作家、藝術(shù)家事跡的記述,詩(shī)文書(shū)畫(huà)的考析和鑒賞,古今著作的推薦和評(píng)論,以及讀書(shū)隨筆、序跋札記,只要有一得之見(jiàn),言之有物,均可登載。另外,從文章的風(fēng)格上,我們主張不擺架子,不作姿態(tài),希望如友朋之間,促膝交談,海闊天空,不受拘束。
初集問(wèn)世以后,我因其他事忙,就約了古代史編輯室的張忱石和文學(xué)史編輯室的許逸民兩位合編。他們當(dāng)時(shí)還不太忙,三人共同商量,事情就好辦得多。《學(xué)林漫錄》刊登學(xué)者、作家、藝術(shù)家的事跡,在當(dāng)時(shí)為其他刊物所少見(jiàn),而約請(qǐng)的寫(xiě)作者一般都是這些學(xué)者、作家、藝術(shù)家們的朋友、學(xué)生或親屬,親炙日久,了解自深,行文又自然、真摯,讀來(lái)使人備感親切。這是《學(xué)林漫錄》的一大特色。前后所記述的有齊白石、陳寅恪、張?jiān)獫?jì)、朱自清、陳垣、黃侃、鄧之誠(chéng)等四十幾位人物。
《學(xué)林漫錄》的文章一般只不過(guò)兩三千字,是希望不要給讀者以過(guò)重的閱讀負(fù)擔(dān)。有的還僅數(shù)百字,如俞平伯先生的《德譯本〈浮生六記〉序》(第八集)和錢(qián)仲聯(lián)先生的《重修破山寺碑記》(第十二集)。前者是吳小如先生約來(lái)的,后者是許逸民同志和我有一次與錢(qián)先生一起開(kāi)會(huì),錢(qián)先生隨便談起時(shí)向他約的。兩篇都用文言寫(xiě):俞先生的序?yàn)t灑清脫,一如晚明風(fēng)格;錢(qián)先生的記則奧義麗辭,直追六朝譯經(jīng)。
但《學(xué)林漫錄》所收也有長(zhǎng)文章,一是時(shí)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總編輯的錢(qián)伯城。一次我到上海去,他說(shuō)他寫(xiě)了老畫(huà)家顏文梁先生年譜,幾萬(wàn)字,當(dāng)時(shí)哪家刊物都不能登,顏先生雖然無(wú)論人品畫(huà)品都可稱(chēng)為近代中國(guó)油畫(huà)界的佼佼者,但人老了,知道的人不多了,實(shí)在遺憾得很。我遂以不拘一格為由向張、許兩位推薦,在第六集一次性刊出。想要了解20世紀(jì)二三十年代中國(guó)油畫(huà)的發(fā)展,此文是非讀不可的。
另一長(zhǎng)篇是北京大學(xué)吳小如先生的《京劇老生流派綜述》。這是吳先生的舊作,比錢(qián)伯城同志所作的年譜更長(zhǎng),從譚鑫培一直說(shuō)到周信芳,共八篇,總計(jì)超過(guò)十萬(wàn)字。這樣當(dāng)然不可能一集刊完,于是與小如先生商定,每集刊兩篇。本以為這樣的專(zhuān)門(mén)記述不易為眾人所注意,卻不想引起轟動(dòng)效應(yīng),不但像啟功先生那樣的大學(xué)者贊不絕口,據(jù)我的大學(xué)同窗白化文介紹,北大一位化學(xué)系教師,每集必捧讀吳先生的這一長(zhǎng)篇連載,寢食俱廢。更怪的是,據(jù)他說(shuō),有一位肺癌晚期的在我國(guó)工程技術(shù)界頗有建樹(shù)的長(zhǎng)者,于平靜的回光返照中,對(duì)自己的一生是滿意的,別無(wú)眷戀,只惦記著要看看吳先生對(duì)馬連良的評(píng)議最后究竟如何。
我們幾個(gè)人還立了一個(gè)規(guī)矩,那就是從初集起,每一集的“學(xué)林漫錄”四字,都分別約請(qǐng)一些學(xué)者或書(shū)法家書(shū)寫(xiě),這樣集合起來(lái)不啻是當(dāng)代名人書(shū)跡,不但有觀賞價(jià)值,還有文獻(xiàn)價(jià)值。初集由我約了錢(qián)鍾書(shū)先生題簽,以后幾集則是下列諸位先生:?jiǎn)⒐Α㈩櫷垺⑷~圣陶、鄒夢(mèng)禪、黃苗子、許德珩、許姬傳、張伯駒、李一氓、趙樸初、王蘧常、任繼愈等,這也是別具一格之處。封面設(shè)計(jì)也是一貫的素雅沉靜的風(fēng)格。
自從1980年6月出版《學(xué)林漫錄》初集以后,就進(jìn)度和印數(shù)來(lái)說(shuō),可以說(shuō)每況愈下,特別是在1988年出現(xiàn)了大滑坡。我曾就各集作了一個(gè)統(tǒng)計(jì):初集1980年出,印了三萬(wàn)多冊(cè);第二、三、四集是1981年出,第五、六集是1982年出,第七、八集是1983年出,第九集是1984年出,這幾集印數(shù)都在一萬(wàn)數(shù)千冊(cè)。1985年倒也出了兩集(第十集、十一集),印數(shù)已跌進(jìn)一萬(wàn)以?xún)?nèi)了。而1985年以后,1986、1987兩年都是空檔,1988年1月才出了第十二集,印數(shù)只有兩千五百冊(cè)。
這當(dāng)然要虧本,出版部的同志不熱心,經(jīng)營(yíng)管理的同志也提了意見(jiàn)。而相識(shí)的朋友,包括不少作者,是仍然很關(guān)心的,見(jiàn)到必問(wèn)有新的出來(lái)否?有的開(kāi)玩笑地說(shuō):《學(xué)林漫錄》的“漫”應(yīng)該改為“慢”了。
結(jié)果第十三集于1991年5月出版,印一千冊(cè);八年后出版了第十四集,印四千冊(cè)。后來(lái)又把它們集合起來(lái),換了封面重印過(guò)一次。中華書(shū)局?jǐn)M陸續(xù)新編,但恐怕不可能每年都編輯新集了。
在編輯《學(xué)林漫錄》的過(guò)程中,我對(duì)于那些談書(shū)人書(shū)事的文章就十分有興趣,先后主張刊登過(guò)《傻公子的“傻貢獻(xiàn)”——嘉業(yè)堂藏書(shū)樓的過(guò)去和現(xiàn)在》(許寅)和《書(shū)林瑣記》(雷夢(mèng)水)等,但畢竟側(cè)重點(diǎn)不同,所用文章有限。多年前,在編纂《中國(guó)藏書(shū)通史》問(wèn)世以后,曾與北京大學(xué)圖書(shū)館學(xué)系1984屆畢業(yè)、到南京大學(xué)工作后曾經(jīng)有過(guò)多次學(xué)術(shù)合作的徐雁教授談及,在此領(lǐng)域尚有文章可做。他表示即可籌劃一套《書(shū)林清話文庫(kù)》,大可裨補(bǔ)學(xué)壇,沾溉書(shū)林。我以為文庫(kù)的立意頗佳,有關(guān)各書(shū)的選題,如韋力先生的《書(shū)樓尋蹤》、曹培根先生的《書(shū)鄉(xiāng)漫錄》、孟昭晉先生的《書(shū)目與書(shū)評(píng)》、劉尚恒先生的《二余齋說(shuō)書(shū)》、謝灼華先生的《藍(lán)村讀書(shū)錄》、周巖先生的《我與中國(guó)書(shū)店》以及來(lái)新夏先生的《邃谷書(shū)緣》、徐雁先生的《蒼茫書(shū)城》、虎闈先生的《舊書(shū)鬼閑話》、林公武先生的《夜趣齋讀書(shū)錄》、胡應(yīng)麟等的《舊書(shū)業(yè)的郁悶》、范笑我先生的《笑我販書(shū)續(xù)編》,都極有文獻(xiàn)價(jià)值和文化涵義。
按20世紀(jì)初葉德輝曾著有《書(shū)林清話》一書(shū),以筆記體裁記敘古代版刻、藏書(shū)情況,多有專(zhuān)門(mén)知識(shí)性的掌故。但他未說(shuō)及何以名為“清話”。按陶淵明有詩(shī)云:“信宿酬清話,益復(fù)知為親。”(《與殷晉安別》)他與摯友臨別,可以連續(xù)兩夜(信宿)談話,即清雅不拘世俗之交談,故更為親切。又“建安七子”之一劉楨有“清談同日夕,情敘憂勤”(《贈(zèng)五官中郎將》之二);東晉時(shí)名士殷浩因事離開(kāi)京都,宰相王導(dǎo)特約其共敘:“身今日當(dāng)與君共談析理。”于是,“既共清言,遂達(dá)三更”(《世說(shuō)新語(yǔ)·文學(xué)》)。可見(jiàn)清話、清談、清言,都有情深思切、朝夕細(xì)敘之意。我想,讀者披覽這套文庫(kù),也必有此感。我讀韋力先生之《書(shū)樓尋蹤》、周巖先生之《我與中國(guó)書(shū)店》,既有一種滄桑之感,更有對(duì)書(shū)林的緬懷之情。現(xiàn)在在鄧子平先生的傾力支持下,經(jīng)過(guò)兩年多的組稿,基本形成了如今的格局。來(lái)自各地的作者們的書(shū)稿,盡管各自的側(cè)重點(diǎn)有所不同,但他們鐘愛(ài)書(shū)籍文化、探究古今圖書(shū)的學(xué)術(shù)趣味卻是共同的,想讀者必會(huì)有“交酌林下,清言究微”(陶淵明《扇上畫(huà)贊》)之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