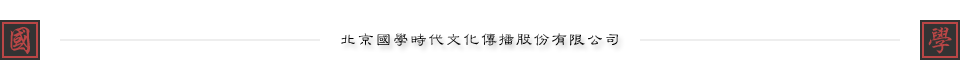歷代著名家教選介(九):張之洞家書
附錄二
《張之洞家書》考辨 龍泉山人
現(xiàn)在刊布的張之洞家書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是1929年北平文華齋刻本《張文襄公全集》中的《家書》(以下簡稱“全集本家書”),內(nèi)容是致叔父、仲兄、子密等人的書札;二是現(xiàn)在比較通行的《張之洞家書》(以下簡稱“通行本家書”),內(nèi)容是40通致、復(fù)雙親書和4通致、復(fù)兒子書。關(guān)于這兩部分內(nèi)容的真?zhèn)螁栴},歷來眾說紛紜。《歷史研究》2000年第2期刊載了秦進(jìn)才先生的《<張之洞家書>辨?zhèn)巍芬晃摹G叵壬鷱奶摌?gòu)人物、違反制度、時間混亂、編造履歷、使用后世語言等方面詳細(xì)分析了“通行本家書”,認(rèn)為它并非出自張之洞之手,乃后人偽造;同時,秦先生還對“通行本家書”的偽造者及其傳播源流進(jìn)行了一番考證與分析。此外,秦先生在1998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張之洞全集》《家書》部分后的按語中認(rèn)為,“全集本家書”也是偽造的。[①]關(guān)于“通行本家書”的真?zhèn)螁栴},秦先生的“后人偽造說”的觀點(diǎn)無可置疑。不過,關(guān)于“通行本家書”的傳播源流及其偽造者,筆者有不同看法。同時,筆者就“全集本家書”中的部分內(nèi)容進(jìn)行考辨,認(rèn)為它們是可信的。
一 、“通行本家書”的傳播源流辨
在考察“通行本家書”的傳播源流時,秦先生認(rèn)為:“首先傳播《張之洞家書》的是上海中央書店,但筆者沒有找到最初的版本。筆者看到的有中央書店1934年9月重印本、1935年10月第6版、1936年5月第7版等。1935年10月版增列叢書名《清朝十大名人家書》,也有時作‘清代名人’。”后面作者又認(rèn)為:“上海中央書店版的《張之洞家書》,奠定了偽造的《張之洞家書》流傳的基礎(chǔ),后經(jīng)多次再版,流布甚廣。”也就是說,上海中央書店是最早刊布《張之洞家書》的。中央書店最早出版家書的確切時間,盡管我們現(xiàn)在還沒有明確的材料,但是從秦先生所舉該書有1934年9月重印本、1935年10月第6版、1936年5月第7版等版本的情況來看,該書在當(dāng)時是比較暢銷的,所以才會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屢屢再版重印,因此,可以斷定,它的初印時間應(yīng)該就在1934年前后。
國家圖書館分館普通古籍館藏中有一部鉛印本《十大名家家書》。在該書的版權(quán)頁上,書名題“十大名家家書”,出版時間題“民國十四年一月初十日付印、民國十四年二月初十日出版”,編輯者是“虞山襟霞閣主”,評校者是“衡陽秋痕樓主”,出版者和印刷者都是“上海共和書局”。不過該書并非全本,只存鄭板橋、林則徐、曾國藩、彭玉麟、胡林翼、左宗棠、張之洞、袁世凱等八家。其中《張之洞家書》的正文共37葉,每葉13行,行31字,卷端題“虞山襟霞閣主編次”,前有著者小史,內(nèi)容包括40通致、復(fù)雙親書和4通致、復(fù)兒子書。無論是從編者,還是從內(nèi)容以及編排情況來看,上海共和書店版《張之洞家書》與中央書店版是相同的。也就是說,早在中央書店之前,就已經(jīng)有共和書店刊布的《張之洞家書》。由于尚未發(fā)現(xiàn)更早的資料,我們可以確認(rèn),《張之洞家書》的最早出版時間應(yīng)該是民國十四年,即1925年;最早出版者是上海共和書局,而不是上海中央書店。
二 、“通行本家書”乃張厚谷偽造辨
1929年,在《張文襄公全集》卷229《家書》的案語中,王樹柟談到自己從張厚谷處獲得三卷家書,并沒有說它們就是張厚谷偽造的。1937年,甘鵬云在《張文襄公全集校勘記·后記》中也只是解釋了不印家書的原因,那就是張仁樂(燕卿)、張仁蠡(范卿)認(rèn)為家書是滬上贗作。甘鵬云也沒有明確指出張厚谷就是家書的偽造者。唯一明確指出張厚谷是家書偽造者的是張之洞的族孫張達(dá)驤。他在與李石孫先生合著的《張之洞事跡述聞》[②]一文中談到,在張之洞去世后,“其后長子張權(quán)托王樹柟(字晉卿)編定遺集。有之洞族孫張厚谷(字修甫)往見樹柟。樹柟談及全集中尚少家書一門,似憾欠缺。厚谷即回家連夜偽造了家書一本送與樹柟。初刻印行后為張權(quán)發(fā)覺撤除,故印本無家書。然刻板書坊抄有‘家書’副本,印為單行本以牟利,文字淺陋,謬誤百出,實非之洞手筆。此事達(dá)驤亦知之,質(zhì)問厚谷,但已無從收回了”。由于張達(dá)驤先生是張之洞族孫,按理出自他之手的材料應(yīng)該比較可信。但是,張先生這段話的可信度卻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秦先生已經(jīng)對張先生的“然刻板書坊抄有‘家書’副本,印為單行本以牟利”這句話提出了疑問。經(jīng)過考辨,筆者認(rèn)為張先生“厚谷即回家連夜偽造了家書一本送與樹柟”的觀點(diǎn)值得懷疑。
從秦先生對通行本家書幾個方面的分析來看,我們可以確定,偽造者是一個對清代科舉制度一無所知、對張之洞及其家族知之甚少的人物。要不然,在偽造過程中就不會犯諸多常識性錯誤。盡管秦先生在文章中提出“至此,偽造張之洞家書者為張厚谷,當(dāng)可無疑”,但同時也認(rèn)為此事還存在三點(diǎn)疑問。結(jié)合有關(guān)文獻(xiàn),筆者覺得張厚谷偽造通行本家書的可能性不大。
首先,我們將通行本家書與全集本家書進(jìn)行比較,很容易就會發(fā)現(xiàn)三點(diǎn)抵牾之處:
第一點(diǎn),通行本3月22日致雙親書中張之洞報告自己的中式情況是“得中進(jìn)士第四名,現(xiàn)已屆殿試期矣”,而全集本第1通《致叔父》中則是“會試中式一百四十名貢士,覆試一等第一名,殿試一甲第三名進(jìn)士,朝考一等第二名”,兩者名次不相符。
第二點(diǎn),通行本第三通致雙親書是報告自己中式情況,而全集本第15通《致仲兄》中稱:“昨日探知先大夫請恤事,已于三月二十日奉旨:‘著交部照軍營立功后病故例議恤。欽此。’頃托人在兵部探詢恤典詳悉如何,隨后布聞。榜發(fā)后,弟幸獲中式,適出范鶴生師之門。”中式時前者的雙親仍健在,而后者的父親已故去。
第三點(diǎn),通行本12月19日致雙親書中稱“兒則既無兄弟,又喪妻室,僅一呱呱在抱之麟兒,又煩大人挈領(lǐng)”,全集本第3通《致兄文竹》中既提到“六弟”,也提到“子青五兄”,兩者在有無兄弟上也不相同。
按照張先生和秦先生的觀點(diǎn),通行本與全集本都是張厚谷一人偽造的。這就讓人費(fèi)解了:為什么同出張厚谷之手的家書會出現(xiàn)如此自相矛盾的地方?更何況是“連夜偽造”?合理的解釋是通行本與全集本出自兩個不同的人之手,而不是出自同一個人之手。
其次,在秦先生之前,劉路生先生發(fā)表了《<袁世凱家書>考偽》一文[③]、劉學(xué)照先生發(fā)表了《李鴻章家書辨?zhèn)巍芬晃腫④]。劉路生先生考辨的《袁世凱家書》“收錄袁世凱的書信63函(內(nèi)報告,宣言各一件),其中致親戚者49函,其余11函,分致有關(guān)人士……襟霞閣主編次,1925年上海共和書局、1935年中央書局先后出版”,其內(nèi)容與國圖所藏《十大名家家書》的《袁世凱家書》完全相同。劉學(xué)照先生考辨的《李鴻章家書》最早的版本僅提到是1936年廣益書局排印本,而且恰好國圖的《十大名家家書》缺少《李鴻章家書》,因此還不能斷定它與《張之洞家書》、《袁世凱家書》的關(guān)系[⑤]。不過如果我們比較這三種書的作偽痕跡、作偽手段,可以得出很多相同的特點(diǎn)出來:第一,作偽者對張之洞、李鴻章、袁世凱的身世和家族成員情況不甚清楚,所以在才會出現(xiàn)各種張冠李戴、無中生有的現(xiàn)象;第二,作偽者對晚清的制度不甚了解;第三,作偽者在不自覺地使用了當(dāng)時的語言。由于《張之洞家書》與《李鴻章家書》都是由上海共和書店于民國十四年首次出版,因此,兩者的偽造者應(yīng)該是同一個人或同一個時代的人。
再次,我們通過了解張厚谷的生平情況可以判斷通行本家書并非他偽造。國家圖書館分館地方志與家譜文獻(xiàn)中心收藏有一部民國26年(1937)鉛印本《南皮張氏四門第十八支家譜》(以下簡稱《家譜》),其中有張厚谷的小傳:
“原名龍瑞,字修府,亦字只齋,歲貢生,考取三江師范學(xué)堂輿地專門教習(xí),前清江蘇淮安府知府,民國二年特派視察貴州軍政大員、彰武鎮(zhèn)威大將軍行署秘書長,東三省巡閱使署秘書長兼政務(wù)處處長,漢粵川鐵路參贊代行督辦事,東三省電政監(jiān)督,江蘇無錫縣知事,冀察政務(wù)委員會政務(wù)處第一組組長兼冀察地方參議會籌備主任。著有《南皮張氏碧葭精舍印存》八卷,又《碧葭精舍印譜己巳集》一卷。光緒庚辰年五月十四日辰時生。”[⑥]
光緒庚辰年是1880年。到廢除科舉考試的光緒三十二年(1906),張厚谷已經(jīng)二十七歲了。按照他的家庭背景以及當(dāng)時的情景來看,此前張厚谷應(yīng)該參與過舉業(yè),熟悉當(dāng)時的科舉考試制度。小傳中的“歲貢生”可為佐證。如果通行本是張厚谷偽造的話,里面不應(yīng)該在科舉制度方面犯諸多常識性的錯誤。還有一點(diǎn),也正是秦先生的疑惑,作為張之洞族孫的張厚谷應(yīng)當(dāng)比較了解張之洞的生平履歷,至少不應(yīng)該偽造出“兒則既無兄弟”的話語出來。從這兩點(diǎn)來看,我覺得張厚谷偽造通行本家書的可能性不大。
最后,從家書的流傳源流來分析,我們也可以發(fā)現(xiàn)家書并非張厚谷偽造的蛛絲馬跡。正如上述第一部分所言,通行本家書早在民國十四年就已經(jīng)在上海出版了,而《張文襄公全集》是在民國十七年才開始刊刻的,中間相差3年。盡管現(xiàn)在我們無法知道張厚谷給王樹柟三卷家書的確切時間,但是,張先生所言“樹柟談及全集中尚少家書一門,似憾欠缺”的話語,似乎表明當(dāng)時全集的編輯工作基本完成,等待付之梨棗。我們據(jù)此可以推測這個時間應(yīng)該更接近民國十七年,早于民國十四年的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說,張厚谷給王樹柟三卷家書的時候,通行本極有可能已經(jīng)在上海出版發(fā)行了。
結(jié)合上述四方面的分析,筆者認(rèn)為通行本家書系張厚谷偽造的可能性不大,極有可能如陳恭祿先生所言,是騙取稿費(fèi)的文人或貪圖利潤的書賈所為。
武昌蛇山首義公園內(nèi)抱冰堂(張之洞晚號抱冰)。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湖廣總督張之洞調(diào)任軍機(jī)大臣離鄂,其在鄂門生、僚屬建此堂以存紀(jì)念。1953年曾進(jìn)行修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