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文化》第30期(2009年秋季號)
主 辦: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中國文化》編輯部
周 期:半年刊
出版時間:2009年秋季號
學(xué)人寄語
舊時在臺灣創(chuàng)辦佛光大學(xué)時,邀雷驤、黃春明為圖書館作了兩組藏書票,他們鼓勵我也做一組,遂塗鴉為之。其中有一款,繪一小人閑坐,題詩於上,曰:“久矣讀書忘歲年,優(yōu)遊經(jīng)籍樂其天,庭前唯見花發(fā)落,珍重人間自在緣。”記得當(dāng)日題這詩時,幾乎落筆即是,比曹子建七步成詩還要迅捷。非我才華更高,實(shí)因這是我一貫的態(tài)度、長期的想法,幫不假思索,沖口而出。
此詩其實(shí)亦卑之無甚高論,講的無非是一種讀書人的狀態(tài)。只不過,這種狀態(tài),在今日,或要被歸類為“傳統(tǒng)的”。事實(shí)上也就是老古董,不合時宜的。
合乎時宜的學(xué)者,現(xiàn)在不能讀書忘歲年,因?yàn)槊磕甓加行抡n題、新專案要申報(bào)、要立項(xiàng)、要送審、要接受年檢、要填交總結(jié)成果。他也不能優(yōu)遊經(jīng)籍,自得其樂,因?yàn)樽x書是為了找研究課題,要覓冷門、找熱點(diǎn),拾遺補(bǔ)缺,尋虛搗隙,撰寫論文,刊載於某某核心刊物,或爭取列入SSCI、AHCI。何況,現(xiàn)在基本上也不讀經(jīng)籍,只看論文、期刊資料,或乾脆上網(wǎng)下載了。新時代之學(xué)人既已如此,何能自在?若不幸暴得大名,上電視、開講壇,或四下走穴,更是忙得不可開交,讀書自樂、體會天地自然之生意,恐遂愈發(fā)不可得了。
也就是說,老式的“讀書人”,跟現(xiàn)代的“學(xué)人”,乃是兩類不同的人。前者讀書養(yǎng)心,可以自樂其天,愛看什麼書、怎麼看、如何受用,都是自己的事。現(xiàn)代學(xué)人則譬如工廠職工,讀書乃其工作,工作還得有產(chǎn)出成果。論文、研究報(bào)告、技術(shù)專利、學(xué)生培養(yǎng)等即是他的產(chǎn)出,不由他決定。生產(chǎn)什麼、什麼標(biāo)準(zhǔn)、多少產(chǎn)量,均由機(jī)構(gòu)決定之,他只需配合。若不能或不願配合,就得捲舖蓋走人,喪失了學(xué)人的資格。
在現(xiàn)代這樣的學(xué)術(shù)生產(chǎn)體系中,唉歎古風(fēng)不存,是沒意義的;緬念舊日讀書人之樂,亦只是詩興勃發(fā)時這一點(diǎn)感慨。若想螳臂擋車,逆拒潮流,恐怕也很快就會慘遭滅頂;如欲號召義師,弔民伐罪,大約也很難真正糾集同志。
但,情況雖然如此不利,我們還是可以給自己一點(diǎn)空間。除了寫那些交差的、應(yīng)景的、公式化生產(chǎn)的論文之外,給自己一點(diǎn)時間,不帶任何目的地讀點(diǎn)“閒書”,或自作一二筆記、或與一二素心學(xué)友函劄談心論學(xué),或遊藝詩文琴曲,或自作名山之業(yè),不逐俗世聲華,都不是太困難的事。至不濟(jì),亦可優(yōu)遊經(jīng)籍,暫時擺脫知識工人的身分,得到單純讀書人的快樂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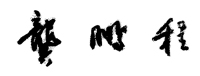
龔鵬程
2009年10月
編 後
現(xiàn)在大家看到的是《中國文化》2009年秋季號。長期護(hù)惜本刊的季羨林先生、任繼愈先生和柳存仁先生,接連在今年的夏秋之間離開我們。還有與本刊文字往來密切的卞孝萱先生、舒蕪先生,也在不久前辭世。這使得今年的學(xué)術(shù)秋天倍添寂寥,故特於“學(xué)林人物志”專欄聊寄辦香。
季、柳兩先生是本刊的學(xué)術(shù)顧問,他們有多篇文字在《中國文化》刊載。季先生的文章,包括第一期的《新博本吐火羅文A(焉耆文)<彌勒會見記劇本>第十五和十六張譯釋》、第二期的《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筆談》、第四期的《新疆古代民族語言中語尾-am>U的現(xiàn)象》、第九期的《關(guān)於“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第十五十六期合刊的《牛棚生活》,共五篇。柳先生的文章計(jì)有第十期的《馬來西亞和漢學(xué)》、第十一期的《道教與中國醫(yī)藥》、第十三期的《藏文本羅摩衍那本事私箋》和《古代的幽默》、第十九二十期合刊的《關(guān)於圖理琛的<異域錄>》和第二十九期的《金庸小說裏的摩尼教》,共六篇。季之專學(xué)獨(dú)擅在梵文和吐火羅文的研究與翻譯,柳之專精為道教和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兩人所賜文均為其專學(xué)領(lǐng)域的典範(fàn)之作。
《中國文化》創(chuàng)刊之初,季羨林先生嘗說“好像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讓人不相信那個特殊的歷史時刻還會有這樣一本刊物問世。後來因資金不足而無法按時出刊,亦為季先生所關(guān)切,一次竟派弟子專程詢問究竟,得知尚可維持方放下心來。柳先生也曾為此系念於懷,2006年一月二十曰的信裏寫道:“承示及《中國文化》因乏固定基金支持,故往往脫期。此意弟亦有時有此同感。然回顧此刊物之初露頭角,實(shí)在二十年前改革開放之草創(chuàng)時代。其時大學(xué)哲學(xué)系初開班,請遠(yuǎn)方學(xué)人如杜君維明來講儒家思想,又創(chuàng)辦文化書院,聲勢浩大,功在社會,實(shí)不可沒。且刊物迄今仍在京港及臺灣三地發(fā)行,此於促進(jìn)兩岸知識界之認(rèn)識,厥功尤偉,似不可輕言停頓。”季、柳等老輩碩學(xué)的鼓勵與期許,實(shí)為我們困知勉行的力量源泉。如今刊物得造物眷顧,交郵局發(fā)行,不再脫期,然老輩獎掖學(xué)術(shù)的拳拳之殷,我們豈敢或忘。
此期刊載柳存仁先生的《研究中國傳統(tǒng)學(xué)問的途徑和方法》一文,就是為表達(dá)我們的緬懷之意。柳先生此文系1996年十月在香港浸會大學(xué)“潘重規(guī)先生學(xué)術(shù)講座”所作的一次演講。潘字石禪,是太炎先生大弟子黃侃的高弟兼東坦,以治敦煌學(xué)和紅學(xué)名世,長期執(zhí)教臺灣文化大學(xué),與柳先生交誼甚篤。所以柳先生講論的內(nèi)容,主要以季剛先生鐘愛的八種典籍為主,這八部書是《詩經(jīng)》、《周禮》、《左傳》、《史記》、《漢書》、《說文》、《廣韻》、《文選》,季剛先生當(dāng)年曾有“八部之外皆狗屁”之說。柳先生所講當(dāng)然不止這八部典籍,《語》、《孟》、《荀》、《韓》、《老子》、《莊子》、《墨子》、《管子》、韓愈等均有涉獵。特點(diǎn)是“由至淺望至深”。他說這是治中國學(xué)問所必需的一些“很基本的東西”,如果連“這些簡單的敲門磚都不具備,那也就不能研究傳統(tǒng)的學(xué)問了”。
本期內(nèi)容宏富,名篇佳構(gòu)非止一端,讀者率性採擇可耳。此外不覺得另有話好說了。
2009年10月6日己丑中秋後三日編後謹(jǐn)記
文章分頁: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