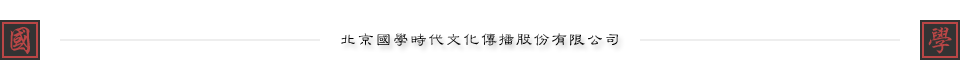六藝之為道 一心之為德——馬一浮學(xué)術(shù)思想片論
二十世紀(jì)上半葉,正值戰(zhàn)亂頻仍,國(guó)是蹇難,而致力于“本國(guó)學(xué)術(shù)之獨(dú)立”的一代中國(guó)學(xué)人卻創(chuàng)造了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思想史上的輝煌實(shí)績(jī)。國(guó)學(xué)大師們留下的著作,其恢弘的精神氣象和博大精深的學(xué)術(shù)建構(gòu),堪為后學(xué)楷模。
馬一浮(1883—1967)是其中的一個(gè)代表。他以張橫渠“四句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xué),為萬世開太平)為治學(xué)宗旨,秉承宋明心性之學(xué),融通儒、道、釋,主張各種立于文字的宗教或?qū)W問雖有千差萬別,但在心性本源上卻是殊途同歸。馬一浮的主要學(xué)術(shù)著述有《泰和會(huì)語(yǔ)》、《宜山會(huì)語(yǔ)》,兩者皆為1938年抗戰(zhàn)避難途中為浙江大學(xué)師生講學(xué)稿。而最詳盡地表述其學(xué)術(shù)思想的,則是1939年9月至1941年5月在樂山烏尤寺創(chuàng)設(shè)“復(fù)性書院”并任主講,結(jié)集刊行的《復(fù)性書院講錄》六卷,以及當(dāng)時(shí)答復(fù)院內(nèi)外問學(xué)者書信結(jié)集成的《爾雅臺(tái)答問》、《爾雅臺(tái)答問續(xù)編》。馬一浮的學(xué)術(shù)思想,可用他在《泰和會(huì)語(yǔ)》中“六藝之為道,一心之為德”這句話提挈,以下試做闡明。
一、六藝該攝一切學(xué)術(shù)
何為“六藝”?一般認(rèn)為是指禮、樂、射、御、書、數(shù)這六種古代儒家的技藝教育。馬一浮則依據(jù)《漢書·藝文志》,以“六藝”特指“六經(jīng)”,也就是孔子刪修并成為儒家經(jīng)典的《詩(shī)經(jīng)》、《尚書》、《禮》、《樂》、《易經(jīng)》、《春秋》,“經(jīng)者常也,以道言,謂之經(jīng);藝尤樹藝,以教言,謂之藝。” 也就是說,六經(jīng)總括天地萬物的根本原則,以之教導(dǎo)人就稱六藝。
六藝之教的宗旨,馬一浮引《禮記·經(jīng)解》中孔子的一段話:“入其國(guó),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shī)》教也;疏通知遠(yuǎn),《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以及《莊子·天下篇》:“《詩(shī)》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yáng),《春秋》以道名分。”孔子是從受教的人來說,莊子則是就所教的內(nèi)容而言。“通”為六藝的基本特點(diǎn),一條根本的原理統(tǒng)貫六藝全部始終,故不能分開來當(dāng)作幾門學(xué)科看待,“六藝之教,通天地,亙古今,而莫能外也。六藝之人,無圣凡,無賢否,而莫能出也。散為萬事,合為—理。此判教之大略也。”
基于以上對(duì)六藝學(xué)術(shù)地位的判定,馬一浮認(rèn)為六藝乃一切學(xué)術(shù)的本原,統(tǒng)攝古今中外一切學(xué)問:
(一)六藝統(tǒng)諸子及經(jīng)、史、子、集四部。國(guó)學(xué)即是六藝之學(xué),六藝統(tǒng)儒、墨、名、法、道諸子各家。馬一浮不認(rèn)同諸子百家出于王官之學(xué)的說法,他認(rèn)為,由于學(xué)習(xí)六藝者各有所偏重,往熟悉的方面一路發(fā)展,于是都僅得六藝之一二,不及其余,因此形成各有得失的諸子百家。《十三經(jīng)》里包括宗經(jīng)論、釋經(jīng)論兩部分,皆統(tǒng)于經(jīng),各類史學(xué)巨制皆統(tǒng)于《尚書》、《禮》、《春秋》。而集部文章體制、流別雖繁,也皆統(tǒng)于《詩(shī)經(jīng)》、《尚書》,一切文學(xué)盡是詩(shī)教、書教的遺傳。
(二)六藝統(tǒng)西方學(xué)術(shù)文化。例如,一切研究自然現(xiàn)象(“天道”)的自然科學(xué),特點(diǎn)都是“制器尚象”,可統(tǒng)于《易》;凡是研究人類社會(huì)盛衰興廢、分合存亡(“人事”)的社會(huì)科學(xué),可統(tǒng)于《春秋》。甚至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也可統(tǒng)于《禮》,不同的哲學(xué)思想流派,其本體論近于《易》,認(rèn)識(shí)論近于《樂》,經(jīng)驗(yàn)論近于《禮》。不同的思想學(xué)術(shù),對(duì)自然、社會(huì)的思考有所側(cè)重,也有同有異,有得有失。
因此,馬一浮斷言:
因有得失,故有同異。同者得之,異者失之。《易》曰:“天下同歸而殊涂,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睽而知其類,異而知其通,夫何隔礙之有。克實(shí)言之,全部人類之心靈,其所表現(xiàn)者,不能離乎六藝也;全部人類之生活,其所演變者,不能外乎六藝也。
現(xiàn)在看來,馬一浮“ 六藝該攝一切學(xué)術(shù)”的觀點(diǎn)過于絕對(duì),失之迂闊,卻反映了他典型的儒家文化本位思想,這與他同時(shí)代的梁漱溟有相似之處。不同的是,梁漱溟從文化的發(fā)展階段立論,主張“世界文化三期重現(xiàn)說”。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xué)》中,梁漱溟認(rèn)為“意欲”的方向決定了生活的樣法,從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路徑,“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中國(guó)文化是以自為、調(diào)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為其根本精神的”。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的第一期,中國(guó)文化是第二期,而印度文化是第三期,世界文化的未來就是中國(guó)文化的復(fù)興。馬一浮則認(rèn)為,“六藝”既代表了中國(guó)文化的特殊性,又體現(xiàn)了人類思想文化的最高價(jià)值,涵蓋了真善美以及自由、平等、解放等基本理念,因而必然是普遍的、前進(jìn)的、日新的:
學(xué)者當(dāng)知,六藝之教,固是中國(guó)至高特殊之文化。唯其可以推行于全人類放之四海而皆準(zhǔn),所以至高。唯其為現(xiàn)在人類中尚有多數(shù)未能了解,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特殊。故今日欲弘六藝之道,并不是狹義的保存國(guó)粹,單獨(dú)的發(fā)揮自己民族精神而止,是要使此種文化普遍的及于全人類,革新全人類習(xí)氣上之流失,而復(fù)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方是成己成物,盡己之性,盡人之性。……吾敢斷言:天地一日不毀,人心一日不滅,則六藝之道炳然常存。世界人類一切文化最后之歸宿,必歸于六藝。
中國(guó)文化的自覺與自信何其充沛!有這等氣象的,僅熊十力、梁漱溟數(shù)人而已。
二、六藝統(tǒng)攝于一心
馬一浮斷言六藝是人類文化的最后歸宿,既是他儒家文化本位觀的情緒宣泄,更是基于對(duì)儒家心性哲學(xué)體認(rèn)至深,并以“六藝統(tǒng)攝于一心”觀點(diǎn)為中心的學(xué)理建構(gòu)。
“心”是中國(guó)哲學(xué)獨(dú)特的范疇之一,不是生理之心,而是道德的形上本體。孔子未說“心”,只講“仁”,孟子則以道德的本心攝孔子的“仁”,仁的全部意蘊(yùn)皆收于“心”中。《孟子·盡心上》:“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本心即性,則心可與天合而為一。人心自然具有知、能二作用,“人之所不學(xué)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馬一浮的注解是:“知是本于理性所現(xiàn)起之觀照,自覺自證境界,亦名為見地。能是隨其才質(zhì),發(fā)見于事為之著者,屬行邊事,亦名為行。故知能,即是知行之異名。行是就其施于事者而言,能是據(jù)其根于才質(zhì)而言。” 知能即是知行,也就是人先天具有的道德本能。現(xiàn)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牟宗三也強(qiáng)調(diào),“心”不是經(jīng)驗(yàn)層的,而是“虛明照鑒”之性體。
馬一浮解“心”綜合了程朱理學(xué)和陸王心學(xué)。他指明《尚書·洪范》要旨為“明天地人物本是一性”,“性”是天地人物共具之“理”,即自然的普遍法則。天地是“萬物之總名”,人是“天地之合德”,“人者,天地之心也”(《禮記·禮運(yùn)》),“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yīng)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人之性即天地之性,一人之氣即天地之氣,此即說明人與天地萬物本為一體,本無睽隔。
馬一浮統(tǒng)貫條陳,把宋明理學(xué)的“心”、“性”、“理”、“天”、“命”這些范疇一一打通,
天也,命也;心也,性也,皆一理也。就其普遍言之,謂之天。就其稟賦言之,謂之命。就其體用之全言之,謂之心。就其純乎理者言之,謂之性。就其自然而有分理言之,謂之理。就其發(fā)用言之,謂之事。就其變化流形言之,謂之物。故格物即是窮理,窮理即是知性,知性即是盡心,盡心即是致知,知天即是至命。
在他看來,朱子理學(xué)和陽(yáng)明心學(xué)并無窒礙。朱子講格物致知,而知具于心,則理不在心外;陽(yáng)明認(rèn)為知善惡是良知,為善去惡就是格物。心外無物,事外無理,“一心貫萬事,即一心具眾理。即事即理,即理即心。心外無理,亦即心外無事。理事雙融,一心所攝”。
六藝是人心性德中本來具有的義理,是此性德中自然流出的,“六藝之道,即吾人自性本具之理,亦即倫常日用所當(dāng)行之事也。亙古至今,盡未來際,盡虛空界,無須臾而可離,無一事而不遍者也”,“在心為德,行之為道,內(nèi)外一也。德是自性所具之實(shí)理,道即人倫日用所當(dāng)行。德是人人本有之良知,道即人人共由之大路。”六藝之道與一心之德是內(nèi)外統(tǒng)一,由此證明。
從中國(guó)文化固有的思想傳統(tǒng)看,天理人心二者并無分隔。天無私覆,地?zé)o私載,厚德載物乃是天地之心,人心則以惻隱為本,“故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心之全德曰仁”。如果一點(diǎn)沒有惻隱之心,就是麻木不仁,“惻隱,是此心天理發(fā)動(dòng)處。若無惻隱,向下辭讓、羞惡、是非,俱無從發(fā)出來,便是麻木不仁”。于是由“心”再回復(fù)到孔子的“仁”。人心性德全體就是“仁”,具體展開來為仁、智、義、中、和、圣六德,“皆是吾人自心本具的”。六藝之教雖然在啟發(fā)六德上各有側(cè)重,但根本的落腳點(diǎn)是教人識(shí)仁、求仁、好仁、惡不仁。“溫柔敦厚,疏通知遠(yuǎn),廣博易良,恭儉莊敬,潔靜精微,屬辭比事”是六藝之教的“六相”,“六相攝歸一德,故六藝攝歸一心”。
馬一浮闡明了“六藝統(tǒng)攝于一心”的觀點(diǎn),并對(duì)六藝之教推崇備至:
六藝之道,條理粲然。圣人之知行在是,天下之事理盡是。萬物之聚散,一心之體用,悉具于是。吾人欲究事物當(dāng)然之極則,盡自心義理之大全,舍是末由也。圣人用是以為教,吾人依是以為學(xué)。
正是受這種認(rèn)識(shí)支持,他在抗戰(zhàn)時(shí)期非常艱苦的條件下,毅然決然到樂山創(chuàng)辦“復(fù)性書院”。
三、“仁”的闡明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此“理”是天理,天理在人心即是“仁”,所以,“仁”是性德之全。馬一浮對(duì)“仁”的闡釋用力頗多,辨析愈明:
仁者,心之全德。人心須是無一毫私系時(shí),斯能感而遂通,無不得其正。即此便是天理之發(fā)現(xiàn)流行,無乎不在全體是仁。若一有私系,則所感者狹而失其正。觸處滯礙,與天地萬物皆成睽隔,而流為不仁矣。
從“仁”的日常語(yǔ)義中發(fā)揮,由變易中見不易,抉出根本,這是馬一浮的高明處。首先,“仁”的本義是通,中醫(yī)講麻木不仁即指血?dú)獠煌ǎ蛔R(shí)痛癢,毫無感覺。其次,“仁”的基礎(chǔ)是心的“能感”。如何才能人與我通,物與我通呢?須求之于心理感覺,也就是惻隱、同情的情感。有了同情惻隱心,便能夠與他人休戚相通,與天地相通。“仁”可歸之于情感主義倫理。再次,“仁”與“私”相對(duì),“仁者,廓然而大公”,是無“私”且有惻隱之心,“私”就是計(jì)較利害之心,即名利心。“公”與“私”是“仁”與“不仁”的區(qū)分,也是君子小人之別。概言之,
仁者,物我無間故通,不仁者,私吝蔽塞故睽。……今言至德要道,則唯通而不睽,難得而無失也。故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即此現(xiàn)前一念愛敬,不敢惡慢之心,全體是仁。事親之道,即事君之道,即事天之道,即治人之道,即立身之道,亦即天地日月四時(shí)鬼神之道。唯其無所不通,故曰要道。純?nèi)惶炖恚试恢恋隆R挥惺е愠深ジ簦斓厝f物,皆漠然與己不相關(guān)涉。更無感通,而但有尤怨,此則不仁之至,私吝為之也。
在“復(fù)性書院”講授《論語(yǔ)大義》時(shí),為了層層遞進(jìn)說明“仁”的內(nèi)涵,馬一浮運(yùn)用了佛教“四悉檀”說法的方式。“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這是“仁”的最普遍涵義。根據(jù)各人不同的天資(佛教講的“根器”)而隨順講解,也讓聞?wù)邭g喜適悅,是世界悉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dá)而達(dá)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是“仁”的第二層涵義。這里專門就特定對(duì)象講解,因材施教,如同佛教“隨機(jī)宜之大小,宿種之淺深,說各人所應(yīng)之法”的為人悉檀。“仁者其言也韌”,“仁者先難而后獲”,是“仁”的對(duì)治義,針對(duì)各人錯(cuò)失而言,就像對(duì)癥下藥,除遣病痛,對(duì)治悉檀也。“一日克己復(fù)禮,天下歸仁焉”,是“仁”的根本涵義,直抉本源,稱理而說,即第一義悉檀。
“克己復(fù)禮”是“仁”的根本涵義,這是宋明理學(xué)“本體即工夫”精神的發(fā)揮。馬一浮一再?gòu)?qiáng)調(diào),六藝之道不是空言,應(yīng)該從一己的言行實(shí)踐起。克己是修身的功夫,修身的關(guān)鍵是主敬,即“修身以敬”,具體而言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dòng)”。禮者理也,也就是人之所行當(dāng)然之則。《詩(shī)經(jīng)·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意思指普天下的人,都遵從自然的天理規(guī)則,正是內(nèi)在的仁德自然流露。“仁”就是性德所具完善之禮,也就是天理,理行于宇宙萬物中,人稟承此理作為視聽言動(dòng)一切行為的最高準(zhǔn)則。
仁是本質(zhì),禮是形式,兩者內(nèi)外同一,須臾不離。“性不可見,見之于仁。仁不可見,見之于禮。禮之所在,仁即在焉。仁之所在,性即顯焉。其事至近,不出視聽言動(dòng)四者,日用不離。茍無非禮,當(dāng)體即仁。故曰仁遠(yuǎn)乎哉?視聽言動(dòng)皆氣也。禮即理之行于氣中者也。仁則純?nèi)惶炖硪玻氖陆远Y,則全氣是理,全情是性矣。”視聽言貌思是人們五種日常活動(dòng),《尚書·洪范》稱為“五事”。由于心之官主思,四事皆統(tǒng)于心,故思貫四事,一般言視聽言動(dòng)而不言思。圣人所以成就德業(yè),學(xué)者所以盡其知能,都是在日常言行中盡其本心之善。日用之間,大道存焉,所以孔子說:“仁遠(yuǎn)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視聽言動(dòng)功夫出發(fā)點(diǎn)和落腳點(diǎn)是“敬”,這是仁德修養(yǎng)的基本功,如程伊川所說的“涵養(yǎng)須用敬”。敬就是“主一無適”,一心謹(jǐn)持義理而不走作,精神攝聚,氣自收斂,形神自然寬舒流暢。敬則自然虛靜,自然和樂,從而人我一體,物我無間,除遣了“私”字;敬則不敢簡(jiǎn)慢,不敢放肆,除遣了“矜”字,
—有不敬,則日用之間動(dòng)靜云為皆妄也。居處不恭,執(zhí)事不敬,與人不忠,則本心汨沒,萬事墮壞,安在其能致思窮理邪?故敬以攝心,則收斂向內(nèi),而攀緣馳騖之患可漸祛矣。敬以攝身,則百體從命,而威儀動(dòng)作之度可無失矣。敬,則此心常存,義理昭著。不敬,則此心放失,私欲萌生。……故唯敬可以勝私,唯敬可以息妄。私欲盡則天理純?nèi)M南ⅲ瑒t真心顯現(xiàn)。尊德性而道問學(xué),必先以涵養(yǎng)為始基。及其成德,亦只是一敬,別無他道。故曰:“敬也者,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敬”的功夫看似簡(jiǎn)單,實(shí)行卻不容易。名利誘惑面前,人人難免浮躁,皆欲以矜名嘩眾。所以,“去矜”是“主敬”最難處。這里的“矜”完全是貶義,即自恃有德有才的意思,與之相似的是“伐”,即對(duì)人夸耀自己的功勞。《論語(yǔ)》、《易·系辭》以及《老子》都以“矜”、“伐”并舉,馬一浮認(rèn)為二者其實(shí)都是“勝心”或“私吝心”的表現(xiàn),并用佛學(xué)理論仔細(xì)推勘“矜”產(chǎn)生的原因和除遣之法。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shí)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地不居化生萬物之功,圣人不矜保民之德,所以一有私吝心,驕矜便生,自然失去本心之善,天地之理。
(作者單位:四川樂山師范學(xué)院政法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