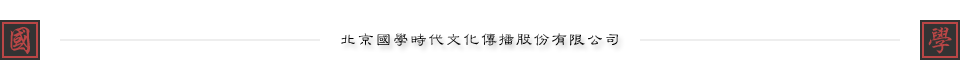吳應箕與桐城派關系考論
內容提要:吳應箕不僅是上江社團的領袖,也是復社領袖,與桐城派的先輩有廣泛的交往。作為選文名家,他對當時的桐城諸子的影響是可以想見的,再進一步看,他的文學思想也通過桐城諸子和自身的傳播惠及戴名世、方苞所開創的桐城派。因為桐城派在學術祈向、對待古今文的態度和理論體系三個方面以驚人的相似性表現出對吳應箕思想的繼承。
關鍵詞:吳應箕;桐城派;戴名世;方苞;影響
作者簡介:章建文,男,1967年生,安徽池州人,池州學院中文系副教授。專業方向:中國古代文學。
吳應箕(1594—1645),始字風之,后更字次尾,號樓山,南直隸貴池興孝鄉(今安徽石臺縣)人,明末著名社會活動家、文學家、復社領袖和抗清英雄。《明史》載:“善今古文”,又操持選政,其言論風旨為時人所重,影響深遠。
桐城派以文名世,是時代孕育的結果,也是地域文化土壤上開出的奇葩。從地域文化的角度考察,晚明時桐城已成為上江文化重鎮,然而桐城以經學名世,在上江地區,艾南英、吳應箕以文名世,而艾南英被復社諸子所排斥,可是吳應箕不僅是上江社團的領袖,也是復社領袖,與桐城諸子有廣泛的交往,其影響也就不可小覷。以此而推,他與清代戴名世、方苞所開拓的桐城文派有沒有關系自然引起我們的思考。為了較為清晰地揭示吳應箕對桐城派的影響,我們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展開論述。
一、吳應箕與桐城派先輩們的交游
吳應箕與桐城諸子的交往是廣泛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639年的一次聚會。“崇禎己卯正月,予應科舉試于郡城,時安慶就試者咸在,而桐城有知名士數人,皆夙昔日游好也”(《樓山堂集》卷十六《池陽郡邸分韻序》)[1],吳應箕請方以智代為征客,舉行了一個小型聚會,詩酒唱和,參加者有十五人,即趙又漢、周農夫(一作“父”)、方爾止、吳子遠(方以智之舅)、方密之、鄧簡之、吳鑑在、左子直、錢幼光、左子厚、張濬之、劉臣向[2](469-472)、羅季先、劉德輿、劉儀之。集詩二十三首,吳應箕為之作序,提出了“志以言白,聚以志起,時以聚得,而素以時征”,強調“志”的重要性,表達了“雅頌久不作,周道今已東。我生困行墨,憂思日忡忡。”希望諸子們“毋為今日聚,而忘起沛豐”(《樓山堂集》卷二十二《池陽郡齋集桐城諸子分韻一東》)。接著在這一年春,由吳應箕起草的《留都防亂公揭》,經過了半年多爭論之后,終于公之于世,署名于上的有:桐城方文、周岐(字農父)、左國林(字子直)、左國材(字子厚)。因這一年他與桐城諸子的交往較集中,我們以此作為考察基點,就顯得較為方便。下面我們就將其中的幾個主要人物予以介紹。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號曼公,明季四公子之一。1633年,就試于南京時結識吳應箕,并主盟吳應箕與劉城開創的國門廣業社。1634年,桐城民變,方以智移居南京。同為復社巨子,在復社活動中接觸頗多。吳氏集中《方密之以智畫天柱峰圖相贈作此還答》(《樓山堂集》卷二十三)、《將去吳門方密之贈詩書扇答此》(《樓山堂集》卷二十五)。
方孔炤(1591—1655),字潛夫,號仁植,即方以智之父。崇禎十一年(1638年)被任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吳應箕為之寫下《與方仁植中丞書》((《樓山堂集》卷十四),吳氏集中還有《贈尚寶方潛夫孔炤》(《樓山堂集》卷二十五)一首七言律。
方文(1612—1669),字爾止,初名孔文,方以智從叔,青少年時與方以智同學友伴達14年之久。方文以詩名世,其詩“樸老真至”。吳氏集中有《送方爾止文赴安廬蔡憲副之招》(《樓山堂集》卷二十四)、《將往無錫答方爾止詩言別》(《樓山堂集》卷二十五)二首。
孫臨(1610—1646),字克咸,后改字武公,明諸生,方以智妹夫,《明史》二七七卷有傳。孫臨工詞賦,著作盈尺,喜談兵,后棄儒從戎。與吳應箕交往密切。吳氏集中有:《贈孫克咸臨》(《樓山堂集》卷二十五)、《贈孫克咸并序》(《樓山堂集》卷二十六)。
錢澄之(1612—1693),初名秉鐙,字飲光,又字幼光,自號田間。先為阮大鋮陰主之中江社成員,1633年冬,方以智從南京回鄉,為其帶來了新的訊息:“三吳舉復社,辨別氣類,與朝局相表里。若某之流,皆在所擯。……吾輩盍早自異諸?”[2](469)于是脫離中江社。著有《田間易學》、《田間詩學》、《莊屈合詁》、《藏山閣詩存》、《藏山閣文存》、《田間文集》等。他不僅是桐城詩派的創始人,也因其古文的創作實績和生活的時間跨度大,影響了幾代桐城士子,也是桐城由專注于經學研究開始轉向熱衷于古文創作的關鍵人物。劉聲木《萇楚齋三筆》卷八說錢澄之:“論詩文精妙,實開桐城諸老之先河,至當而不可易,洵后世學人之龜鑒。”,張舜徽先生在《清代文集別錄·潛虛先生文集》中也說:“桐城經學文章之緒,開自錢澄之。”
潘江,字蜀藻,號木厓。小錢澄之七歲。少即天才雋妙,博覽群書,10歲試文郡邑,群士推為神童。錢澄之說:“及其以詩文交于予也,年正壯盛,方以全力攻制舉之文,而講求用世之學,詩外其余事耳。”然而潘江“以詩文稱于世者30余年”[2](268),著有《木厓集》、《木厓續集》,輯有明代以來的桐城籍詩人之詩的巨著《龍眠風雅》和《龍眠風雅續集》,真正實現了桐城由重經向重文的轉變。在吳氏集中有《潘蜀藻序》,文中語氣透露出前輩對后學的指導鼓勵之意。
與吳應箕交往的桐城名士還有很多,我們只能選擇了一些與戴名世、方苞有聯系的名士作一點介紹,并企圖借此來展開論述。
前四位是方氏家族中人及其姻親,是方苞的長輩。雖然方苞出生于南京,但明末桐城之變后,方氏家族多遷于南京,吳應箕的《留都見聞錄·時事》就有記載:“桐城自甲戌乙亥后,巨室盡家于南。何相國以元老客居而門庭安靜,都人咸誦之。其余,方仁植中丞、方坦庵太史、孫魯山給諫皆為時名人,而悉家于此又數姓之兄弟子侄,文采風流炤耀京邑,他方流寓者所不敢望。”[3]吳應箕長期寓居南京,與他們的交往也較多,再說方苞的祖父方幟與方以智、方文、孫臨年齡相仿,相互的影響是必然的。而方幟學行給方苞的印象是深刻的,他在《大父馬溪府墓志銘》中說:“少時以家貧迫生計,未得時依大父,及冠后,從錢飲光、杜于皇、蒼略諸先輩游,始知大父文學為同時江介諸公所重。”[4](189)敬仰之情溢于言表。方苞的父親方仲舒也與錢澄之、方文也有往來,常相唱和。[5](58)
錢澄之對方苞的影響是直接的。方苞在《田間先生墓表》中說:“苞未冠,先君子攜持應試于皖,反,過樅陽,宿家仆草舍中。晨光始通,先生扶杖叩門而入。先君子驚。問曰:‘聞君二子皆吾輩人,欲一觀所祈向,恐交臂而失之耳。’先君子呼余出拜,先生答拜,先君子跪而相支柱,為不寧者久之。因從先生過陳山人觀頤,信宿其石巖。自是,先生游吳越,必維舟江干,招余兄弟晤語連夕,乃去。”[4](132)作為桐城遺老,這樣關心后輩的成長,對后輩的影響無疑是深遠的。
潘江家中藏書頗多,又獎掖后學。戴名世說:“里中潘木崖先生,博雅君子也,家中多藏書,余往往從借觀,因師事之。”[6](117)對戴名世影響較大。
這些人與吳應箕有著相近的人生價值取向和政治傾向。從年齡上說,除方孔炤之外,吳應箕比他們要長16歲以上,加上方氏、錢氏諸子均是復社成員,而吳應箕是復社的創始人之一,成名較早,自然有著較大的影響力。再說方氏、錢氏諸子中雖也有文名,但都致力經學,不象吳應箕以文名世,而且以教書選文為生,對文章有深入的思考,有更為系統的理論。又因吳應箕操持選政,陳肇曾《吳樓山先生遺集序》云:“自次尾科牘出,天下翕然,奉之為珪璧指南,至有不以名列天衢為榮,以文入選者貴于凌高梯而被丹黼。”(《樓山堂遺文》卷首)所以在他們的交往過程中,雖然說他們的影響是相互的,但就文學思想來說吳應箕對桐城諸子的影響可能要大些。
二、吳應箕的文學思想與桐城派文學思想的關系
如果說從吳應箕與桐城諸子的交往來探尋他對桐城派的影響,由于資料的缺乏,還不能讓人信服,但是從文學思想的傳承中,我們卻可以發現他們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反過頭來看前面的論述,我們就能較為清晰地看到吳應箕對桐城派的影響。
從學術祈向來看,吳應箕認為為學宜由史入經,考經于史,“廿一史者,六經之梯也,雖未能由源及流,溯流以窮源,此或亦讀書之法耳”《樓山堂集》卷十四《復楊維節國博書》),即指明為學之路徑。重要的是吳應箕還將史與文聯系起來,“世有能治二十一史之人而不能治文乎?有治經史以為文之人而其文一如六朝五代之為韓歐所嘔棄者乎?”(《樓山堂遺文》卷一《黃韞生制藝序》),這種實學路徑不僅使文章內容充實、觀點穩實,而且也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學習者易于上手。方苞的“義法”說從史法而來,雖說其直接受萬斯同“事信言文”思想的影響,但萬斯同的老師黃宗羲則明顯受過吳應箕的影響。吳應箕將史法引入文法無疑啟發了后人,方苞在《進四書文選表》中所闡明的為學途徑就與此相一致,他的“義法”說可以說是沿著這條為學之路而演繹歸納出來的理論主張。
從對時文與古文的態度來看,戴名世、方苞與吳應箕都時文與古文寫作的高手,在對待時文與古文的態度上有不少相同之處。吳應箕說“韓歐所謂時文者,……非若今之制舉,義本王者之制,以發明圣人之蘊。嫻于制則下者皆可進取,而由以探測經傳旨趣,雖終身事之而未能盡也。……向使居今之日,則明道者莫制義若也,敢自鄙棄為不足學哉?”(《樓山堂遺文》卷二《陳百史制義序》)雖然他推崇時文,卻能很清楚地看到時文在士子們的眼中是“得之則棄”的仕進工具,投機不僅使士子背心操不然之說,不再從國家功令、圣賢理道上去發明,而且背心競法之弊日甚,所以他主張以古文來改造時文,提出“上下圣賢以研理,出入古今之文以行法”改革措施。雖然戴名世和方苞都反對時文,卻一致主張以古文來改造時文,戴名世說:“其所為時文之法者陋矣,謬悠而不通于理,腐爛而不適于用,……然則何以救之?亦救之以古文之法而已矣。”[6](89)方苞也說:“吾友雨蒼善言古文,……一日,以時文數篇詣余,余責以敝精神于蹇淺。”然而看了以后大為驚詫:“噫!孰謂時文而有是乎?即以是為雨蒼之古文,可矣。”[7](8)特別是他們都有時文選,為別人的時文作過序。吳應箕作為明末房牘選名家,士子常因其一言而名揚士林,錢澄之、潘江等人自然會受到其影響,戴名世、方苞研究改革時文之弊,不能不研究以前的時文理論,方苞在乾隆元年(1736)還奉命選編有明及清大家四書制義的《欽定四書文》,作為天下舉業準的。這本選文的《凡例》中方苞對明代時文的分期問題就吸收了吳應箕“文章之法肇始于洪、永,詳于成、弘之間,莫盛于慶、歷初年,即莫敝于萬歷末季。”(《樓山堂集》卷十七《歷朝科牘序》)的觀點。
從文學理論體系來看,吳應箕提出了“理體”說,以“理”、“體”為基石,以“氣”來貫通“理”、“體”,視“清潔”為至境。錢澄之也提出相似的觀點:“理也者,氣之源也,理明而氣足,氣足而法生。窮理御氣以軌于法,文之瀾所由成也。然則所為持者,非有瀾以待持,乃持之以為瀾也。是宜治其源也:本之六經,以研其精;稽之傳注,以晰其微;博之諸史,經廣其識;輔之百家,以盡其義。如是,而理得焉,而氣至焉,而法備焉。”[2](240)強調了“理”、“氣”、“法”三者兼備。在理論上沒有突破,沒有達到吳應箕的理論水平。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他受了吳應箕的影響,但是作為小吳應箕19歲的應試的士子,對選文名家吳應箕文章理論,特別是時文理論是沒有道理不熟悉的。戴名世主張道、法、辭三者兼備,追求精、氣、神三者渾一,但系統性不足。而方苞提出的“義法”說,有人說它“是對我國古代古文創作經驗的全面總結,它跟以前的各種文派的理論主張相比,具有‘兼收眾美’的集大成之功。”[8](120)實際上在明末已經展開了對古代古文創作經驗的全面總結,吳應箕就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下面我們從幾個方面來論述吳應箕與方苞古文理論的異同,就此分析他們之間的關系或者說吳氏對方氏的影響。
一就其理論基礎來說,方苞的理論基礎是“義”、“法”,具體來說,就是他所說的:“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后為成體之文。”[4](33)他的“義”即是“本經術而依事物之理”,“法”即是文章的法則、結構。而吳應箕說:“夫予往者之論文也,以理以體。理者為圣賢之論,所從出學術之邪正于此分,性道之離合于此辨也;而體者則謂文有一定之章程不可變,有自然之節敘不得亂也。”(《樓山堂集》卷十七《崇禎丁丑房牘序》)在此“體”有兩層意思:一是指創作原則,一是指表現方法。由此我們清晰地看到他們有著相同的理論基礎。雖然在具體論述其理論時,吳氏詳于理,而方氏詳于法,但是都圍繞著本理(或義)言法、因理(或義)立法的原則來展開。
二就其文氣論來說,他們都突出了“文氣”在創作中的作用,吳氏結合理體以論“氣”,方氏結合義法以論“氣”。吳應箕說:“夫予往者之論文也,以理以體。……由今思之,是二說者其跡也。執二者之說,以跡合之,猶易也。察之世運之所趨,庶幾于其言系之者,其惟氣乎。夫昔人之論氣也,辨之清濁之間耳,吾謂莫若審之強弱之際。今天下可謂有氣哉!囗蹴吾疆矣,寇燼吾原矣,囂競長矣,節烈替矣,議任之途相詭,成敗之數不勝矣。竊疑三鼓既竭,莫今昔對比為甚,而靡然者則盡于文見之。夫然文之為風聲也,又何疑哉?且氣不可作而致者也,非不可養而至。腐師俗儒所謂養者發于言則夷易,措之事則和平。試跡其為夷易、為和平者,悅靡靡之可聽,冀庸庸之多福耳。嗚呼!此不知至剛至大者為何語乎,然則予所謂莫今為甚者皆坐是誤也,此屬又烏足與語文哉?是故予不能作天下之事功也,名節也,而風之以各見之文;不能盡救天下之文也,察之于至細之氣。夫剛氣之所發,必不剽也,必不襲也,必不蕪而穢,不矜而肆,不恇而寥落也,必當理,必合體也。推之為忠臣,為介士,為強力有為、為震撓不詘者,必是人,必是言也。非是者,其氣靡也。氣靡者,言離也。剿古人之已說而不情,規先民之成格未能似,猶曰:此體也,此理也。吾謂是大偽不忠,大貪不謹,趨榮勢以遠節烈,隳軍實而長寇讎者,必是言,必是人也。”(《樓山堂集》卷十七《崇禎丁丑房牘序》)主要從風格論、主體論和創作論三個方面來論“氣”,不僅較好地處理了“理”、“體”、“氣”三者的關系,使文章的內容與形式有機地整合為一個生命的活體,而且他的論氣求其強,既吸收韓愈“不平則鳴”理論內核,又對韓愈的“氣盛言宜”的進行了新的理論表述,更重要的是吳應箕不僅論及了“氣”的強弱變化與創造力的關系,還揭示了“氣”的強弱與時間的關系,高揚了“有氣敢言”的斗爭精神,這是值得稱道的。方苞說:“依于理以達乎其詞者,則存乎氣。氣也者,各稱其資材,而視所學之深淺以為充歉者也。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經,而切究乎宋、元諸儒之說;欲辭之當,必貼合題義,而取材于三代、兩漢之書;欲氣之昌,必以義理灑濯其心,而沉潛反復于周、秦、盛漢、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后能清真古雅,而言皆有物。”[4](232)不管他是不是對錢澄之“理”、“氣”、“法”的具體闡發,我認為方苞并沒有為我們提供新的理論觀點,只不過他提供更為具體的明理養氣的操作方法。吳應箕強調至大至剛之氣,而方苞則主張清澄無渣之氣,這不僅是時代精神的必然反映,也是兩人生存方式——由救危救亡之斗士向護道頌世之衛士轉變的直接體現。
三就其審美理想來說,吳應箕追求“清潔”,他說:“蓋弟嘗肆力經史而出入八家矣,又不欲襲取一語,核其體制以歸于清潔,庶幾自成一家,然實未能也。”(《樓山堂遺文》卷四《與沈眉生論詩文書》)而方苞追求“雅潔”。其實方苞既講“雅”,也講“清真”,他在編選四書文時曾說:“凡所錄取,皆以發明義理,清真古雅,言必有物為宗。”[4](232)又說:“古文氣體,所貴澄清無滓。澄清之極,自然發其光精。”[4](245)雖然與吳應箕對“清”的理解有所不同,但都有“清”是“理”的存在狀態的理念,都有“清正”的內核。至于“潔”,方苞的闡述較為詳細,但沒有脫離吳應箕的“清潔”論的理論框架來論“潔”。
雖然方苞沒有直接講明其文學思想受吳應箕的影響,但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吳應箕與桐城派先輩的交往,以及方苞對明清時文的編輯整理,使這種影響成為可能,而方苞的“義法”說與吳應箕的“理體”說在理論體系上驚人的一致,卻以結果的方式確認了這種影響的存在。那么方苞自己卻說受歸有光的影響又是為何?我認為可能是吳應箕是抗清英雄,其書在禁毀之列,不方便指明,所以他選擇了遠承歸有光,而實際上卻是暗承吳應箕。
參考文獻:
[1]吳應箕.樓山堂集,樓山堂遺集[M].//《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續修四庫全書》(1388,138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11-661,1-76.(下文所引吳氏之言同此)
[2]錢澄之.田間文集[M].合肥:黃山書社,1998.《文學劉臣向墓表》載:已卯春,劉臣向應試池郡,案發第一,于是臣向名一時大噪,“池郡吳次尾入見學使,語間盛贊臣向,為學使者得士慶,學使者益大喜,遂國士遇焉。”
[3]吳應箕.留都見聞錄[M].//南京市秦淮區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秦淮夜談.1994(9).
[4]方苞.望溪先生全集[M].//四部備要·集部[M].北京:中華書局,1927-1931.
[5]吳孟復.桐城文派述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6]戴名世.戴名世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6.吳應箕與杜于皇也有交往,吳氏集中有《送杜于皇濬北上》(《樓山堂集》卷二十五)七律一首為證。
[7]方苞.方望溪遺集[M].合肥:黃山書社,1992.
[8]周中明.桐城派研究[M].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
原發表于《安慶師范學院學報》2007年第6期,有的地方作了一點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