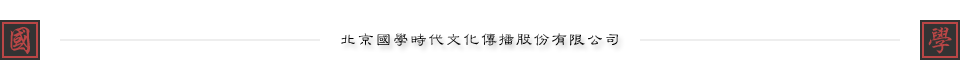京大中文三先生
京都大學(xué)是我一直神往的學(xué)府,這所1897年創(chuàng)建的大學(xué)與更早成立的東京大學(xué)并列為日本最著名的大學(xué)。與東京大學(xué)相比,它更讓日本國民看重的是純粹的學(xué)術(shù)品格。崇尚學(xué)術(shù)自由、思想獨立和批判精神是京都大學(xué)引以為榮的光輝傳統(tǒng),維護大學(xué)自治、維護教師言論自由、維護生態(tài)環(huán)境更是公認的京大師生對日本社會的貢獻。人們常說,東京大學(xué)是政客的溫床,而京都大學(xué)則是學(xué)者的搖籃。京大為日本貢獻了全部四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而東大無與。這是京大又一亮點。若談到漢學(xué),那么京都大學(xué)更有東京大學(xué)無法比擬的驕傲,狩野直喜、內(nèi)藤湖南、桑原騭藏、鈴木虎雄、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貝冢茂樹、小川環(huán)樹、入矢義高……這一串響亮的名字不僅意味著令世界漢學(xué)矚目的豐厚業(yè)績,更意味著一個優(yōu)秀的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標志著日本近代漢學(xué)成立的京都學(xué)派。迄今為止,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一部近代日本漢學(xué)史,一半篇幅要留給京大!以至歐美學(xué)術(shù)界甚至流傳這樣的說法:研究漢學(xué),可以不去中國,但不能不去京都大學(xué)。
京都學(xué)派的傳統(tǒng)以文獻學(xué)研究和實證方法為基礎(chǔ),融文史哲于一體。而在文學(xué)方面,又文學(xué)、語學(xué)兼重,詩詞曲文并舉,創(chuàng)作和批評通擅。前幾輩學(xué)者的文史兼長,博通古今自不必說,即以如今健在的文學(xué)部名譽教授清水茂先生而言,知識面之寬和涉及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之廣,在日本也是罕有儔比的,他能通數(shù)種文字,能做詩詞古文,翻譯過《韓愈詩集》,他的論著上及考訂古文字聲韻,下至評論夏衍《上海屋檐下》,令編譯他文集的中國學(xué)生蔡毅驚訝不已。我讀過先生兩篇字學(xué)論文《說青》、《說黃》,考究這兩個字在中國古代所指稱的實際顏色,征引文獻之廣和涉及各種知識之富,讓我佩服之至。在這么個擁有優(yōu)秀的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的學(xué)府執(zhí)教,誰都會感到自豪,同時感到壓力。
漢學(xué)自古以來原是日本學(xué)術(shù)的主流,明治維新后西洋學(xué)大興,漢學(xué)中衰,雖出現(xiàn)過吉川幸次郎這樣的一代宗師,也未能振起而恢復(fù)到本世紀初的興旺程度。隨著五十年代以后中國經(jīng)濟的落后,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日漸下降,中國文化也日漸失去他的吸引力。近年,由于中國的經(jīng)濟改革和市場開放,在全球范圍內(nèi)掀起一股學(xué)習(xí)漢語的熱潮,許多國家大學(xué)都增設(shè)了中文系,日本也不例外。但與此形成反差的是,漢學(xué)研究卻呈弱化的狀態(tài),一方面漢語老師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高層次的漢學(xué)研究人才卻越來越不好找工作。京大文學(xué)部的中國文學(xué)研究室,也失去以往唯我獨尊的地位,降為一個和其他外國語言文學(xué)專業(yè)一樣的普通專業(yè),長期以來只有興膳宏、川合康三教授和平田昌司副教授三位先生,1997年底才增聘了木津祐子副教授。同年,我受京大研究生院之聘,作為中國文學(xué)專業(yè)客座教授,擔任了一年“中唐文學(xué)研究”的特別講義。一年間與三位先生共事,得到他們不少關(guān)照,也從他們身上學(xué)到不少東西。經(jīng)過一年的接觸,我對三位先生的為人和學(xué)問略有了解。我感到,無論從學(xué)問修養(yǎng)還是從學(xué)術(shù)成就來看,他們都是當今日本漢學(xué)界最優(yōu)秀的學(xué)者之一。
從表面上看,三位先生性格、風(fēng)度相差極大,很少相似之處(如果有的話,那大概是對學(xué)問的神圣態(tài)度),一如他們的服飾風(fēng)格:興膳先生常穿深色服裝,川合先生服裝顏色多變,平田先生多穿淺灰西裝。相比之下,興膳先生較肅穆凝重,沉默寡言;川合先生則平易隨和,略無崖岸,說話較快,表情豐富;平田先生嚴謹持重,有板有眼,話不多而言必中肯。但三人都是很有意思的人,而且各有各的有意思之處。
興膳先生有著一雙眼框深陷的眼睛,面部輪廓峭硬如削,不類一般日本人的臉型。《文學(xué)遺產(chǎn)》主編徐公持先生曾戲言“興膳宏先生怕有胡人血統(tǒng)”。說起來,興膳先生的家世還真有個奇異的傳聞。據(jù)興膳先生的學(xué)生木津祐子說,興膳這個姓,在日本極其罕見,它的來歷有個很有意思的“傳說”:明末清初大動亂之際,長崎的大商人受一位出身高貴的中國貿(mào)易伙伴(明遺民)所托,收養(yǎng)了一個嬰兒,實為明廢帝的皇子。孩子長大以后,承襲商人之名,取“末次興善”的“興善”為名。后來豐臣秀吉將“興善”改為“興膳”,延續(xù)至今。興膳先生是九州福岡人,這個地方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與中國的深刻淵源。盡管興膳先生本人對這三百年前的故事總是笑為“傳說”,但周圍的人卻相信他與中國的另一番緣分正在于此。
我第一次見到興膳先生是在1990年的南京唐代文學(xué)會上,我的印象他總是一個人獨往獨來,不太和人搭話,有種難以接近的感覺。當時不止一個人有這種感覺,甚至有種傳聞,說興膳先生很傲氣,不太瞧得起別人。事實證明這是錯覺,其實他是個挺謙虛的人。只不過很注意服飾的鄭重,而且不善寒暄,很少主動和人搭訕,所以就給人崖岸高峻的感覺了。1997年我在中國文學(xué)專業(yè)任教時,以興膳先生無論在學(xué)術(shù)上在年齡上都屬前輩,所以平時說話時、喝酒時,態(tài)度都是恭恭敬敬的,但他卻總是用同事的平等態(tài)度對待我。有件小事給我印象很深。六月參加京都大學(xué)第十二屆中國文學(xué)會,臨開會前,一個學(xué)生在會場上找到我,告訴我興膳先生致開幕詞時要介紹我,怕我聽不明白,特地讓她來轉(zhuǎn)告,讓我留神起立,以免失禮。由這小事,就可見他待人多周到。
據(jù)錢鷗說,興膳先生以前是很嚴厲的,在學(xué)生面前很少露出笑容。但近年他好像變了一些,變得平易親切不少。的確,我也很少看到興膳先生笑,但相信看到他笑容的人一定會覺得很動人。他的笑容有種和平日的嚴肅極不和諧的淳樸,純真得有點像少年。但這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只有和特殊的人,在特殊的時刻,我見到過幾次,印象特別深刻。
那是在酒桌上,和他的學(xué)生們,還有我,一起在他熟悉的居酒屋(日式酒館)喝酒。興膳先生是日本學(xué)術(shù)界有名的海量,據(jù)說從來沒人見他醉過。我呢,酒量不算大,但屬于“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一流,倒也能湊興,所以在國內(nèi)學(xué)術(shù)界薄有虛名。日本大學(xué)的活動以研究室為基本單位,每年四月新生入學(xué)有“迎新會”,十二月祝新年有“忘年會”,加平時送同學(xué)出國留學(xué)之類,都是全研究室?guī)熒诰频陼纭>┒即髮W(xué)中文研究室在吉川幸次郎先生主持時,就有師生一起喝酒的傳統(tǒng),至今不輟。我在一年中,每逢這種機會都能和興膳先生一起喝酒,但因為座次是抽簽決定的,所以常不能坐在一起。有一次正巧與興膳先生坐一起,就導(dǎo)致我一年間惟一的一次酩酊大醉的經(jīng)歷。那天是送綠川英樹同學(xué)赴南京大學(xué)留學(xué),興膳先生特別高興,我們不停地互相勸酒,頻頻干杯。酒單上凡是我沒喝過的酒他就點,小一兩的杯子,不知干了多少,到三次會唱歌時我就不支了。那時興膳先生因路遠,已先打道回府,并不知道。從那以后,我知道了日本酒的利害。
但更有意思的兩次喝酒,是跟興膳先生到他常去的酒館喝酒。日本人喝酒喜歡上熟悉的酒館,店家對常客(日語叫常連)也特別親切。興膳先生常去的酒館在有名的酒店街木屋町,老板娘和興膳先生同鄉(xiāng),也是福岡人。兩次都是興膳先生請客,一次是沾錢鷗的光,為祝賀她拿到博士學(xué)位,另一次則是重逢敘舊。在這樣的酒館喝酒,興膳先生就像是換了一個人,親切、隨和、平易,但語調(diào)仍保持那認真,指著新上的菜告訴我:“這是蘿卜啊!”語氣詞很強調(diào)。當想起什么問題,他知道簡單但有點趣味時,他提問的同時就露出了那種少年式的淳樸笑容。這樣的機會不很多,所以我相信很少人看到。更少人知道的是興膳先生會唱歌,而且唱得相當不錯。第一次,在居酒屋喝了以后又去酒吧,那兒有卡拉OK,興膳先生唱了《寅次郎的故事》主題歌“男人辛苦”。讓人難以相信的是他竟會唱不少毛主席語錄歌,那是六十年代他在北京學(xué)的。有一次我和幸福香織隨便說到,這位興膳先生的門生竟驚訝得像是聽到海外奇談。酒館里的興膳先生彷佛是另一個人,不,應(yīng)該說是他的另一半,由此我看到一個學(xué)者、老師以外的興膳先生,一個認真、友善、愛喝酒、心地淳樸的男人。
其實平時我和興膳先生很少交談,我知道日本的大學(xué)老師都很忙,所以沒事我是不找他們聊天的。興膳先生給我的印象不善寒暄,偏偏我也是不會寒暄的人,所以平時在學(xué)校遇到只是點頭致意,不多說話。有兩次興膳先生送我書送我酒,也是放下東西,匆匆說兩句話就走。我也感覺,有時面對興膳先生不知說什么好,尤其當我清楚地意識地這一點的時候,就更不自然了。只有喝酒的時候例外,那時說什么都很有意思,唉,酒真是個好東西。
興膳先生是日本研究中國文學(xué)最著名的學(xué)者之一,他的《文心雕龍》和六朝文學(xué)研究著作早已譯成中文,研究古代文學(xué)的學(xué)者耳熟能詳,但他學(xué)術(shù)中另外一些內(nèi)容就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了。興膳先生走上研究中國文學(xué)之路,是很偶然的,說來有趣。1957年他考入京都大學(xué)文學(xué)部,當時一年級新生是宇治校舍學(xué)習(xí),周圍很荒涼。開學(xué)式學(xué)部長吉川幸次郎先生來作了講演,內(nèi)容是杜甫詩,吉川先生對《倦夜》“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兩句的分析,深深打動了他。那天恰巧是他的生日,本來他還沒想定讀什么專業(yè),吉川先生的講演立時讓他作出了決定。這段經(jīng)歷他曾在懷念吉川老師的文章里敘述。
興膳先生是《文心雕龍》第一部日文全譯本的譯者,他的翻譯至今被視為經(jīng)典譯本。他翻譯這部名著時,年僅二十八歲。這份業(yè)績奠定了他的學(xué)術(shù)地位。迄今為止他已出版了《詩品》、《文心雕龍》、《文鏡秘府論》的日譯,還有專著《陸機·潘岳》、《文學(xué)理論》、《中國的文學(xué)理論》、《隋書經(jīng)籍志詳考》(合著)、隨筆集《異域之眼》等,可以說是著述豐富。人們都知道興膳先生中文好,而他法文之好,卻鮮有人知道。興膳先生青年時代就對本世紀中葉新思想的發(fā)源地——法國十分憧憬,后來他在1986年、1994年兩度赴法國講學(xué),終于圓了昔日的法國夢。他到法國講學(xué),不是講日本文學(xué),也不是用日語講課,而是用法語講中國文學(xué)。這就好比要我們用日語去講法國文學(xué),或是用英語去講日本文學(xué),大概不是件容易的事吧?他曾翻譯過不少法國漢學(xué)論著,最新出版的是弗朗索瓦·朱利安的《無味的禮贊》(與小關(guān)武史合譯,1997年)。朱利安是當今法國研究中國思想和文學(xué)最活躍的學(xué)者之一,我讀過他的《迂回和進入》中譯本,是一部杰作。
我對興膳先生的了解還是有限的,畢竟接觸較少,相比之下,我更熟悉川合先生。他的性格、風(fēng)度和學(xué)術(shù)特點都與興膳先生截然不同。就從服飾上說,興膳先生任何時候都是西裝筆挺,即使喝酒時也保持端正的儀表,從不失態(tài)。有次炎夏之夜在討論會后的懇親會上,他的領(lǐng)帶有點松弛,竟令舉座皆驚,相視詫異。而川合先生穿著雖也講究,卻要呈現(xiàn)為隨意的效果,所謂極絢爛而歸于平淡,就是那種追求。興膳先生哪怕在酒館,仍然看得出是名教授。一次喝酒時旁邊坐下兩個喝得半醺的男子,一聊起來,一個是錢鷗任教的同志社大學(xué)出身,他頗帶敬畏地問錢鷗,那位是你老師吧?又和另一位嘀咕些什么,看神情是覺得興膳先生是個人物。的確,興膳先生就有這個氣度。但川合先生就不同了,出了大學(xué),大概少有人能看出他是名教授。長長的頭發(fā),西裝總敞著,很少打領(lǐng)帶,說起話來眉飛色舞,那風(fēng)度實在不太像是教授,倒像是藝術(shù)家。我第一眼看到他,就有這種感覺,說不出為什么。后來看到音樂雜志上一張小澤征爾指揮時的照片,才猛省,原來他的發(fā)型和表情很有點像小澤征爾。就為他的發(fā)型和裝束,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情形就頗為滑稽。
那是1997年1月16日,我由北京飛往大阪,川合先生驅(qū)車到關(guān)西機場來迎接。我們只是通信,沒見過面,他怕我認不出他來,事先寄下兩張近照。不想我啟程時照片還沒收到,到了關(guān)西機場只好憑著感覺找。本來我倒是看過他在中唐文學(xué)會上的一個中景,但走到接機大廳,四顧并沒有那照片上模樣的人。大廳里暖氣很熱,我滿頭是汗,便脫下棉衣,守著行李車顧盼尋覓。當時我穿牛仔褲、運動鞋,大概是一副老學(xué)生模樣。始終沒有人過來搭話,只有個裹著件黃色風(fēng)衣,長發(fā)覆頸,五十歲上下的男子坐椅子上等人,他不時看看我,我也不時看看他,顯然都不像是各自的目標。眼看大廳里人已散盡,再沒有像川合先生的人了,我走向那個男子,他也起身迎過來,我試探地問你是不是在等中國來的人,他問你是不是蔣寅先生,那情形真可以套句唐詩:對面相看不相識,試問客從何處來?當時雙方的好笑可以想見。日后得知,他寄給我的照片正是穿那件黃風(fēng)衣的,為了讓我好認,他硬是忍著熱沒敢脫。
川合先生是個興趣廣泛的人,喜歡談天,喜歡釣魚,喜歡音樂,他的客廳、書房和研究室都有音響,我每次到他研究室,音響都放著古典音樂,而開車時則放流行歌曲,常是若干年前流行的歌手,像中島美雪、五輪真弓、松谷任由實之類。我喜歡五輪真弓就是從坐他的車開始的。
川合先生性格爽朗,沒有老師的架子,所以學(xué)生都喜歡跟他接近,有什么心事也愛找他說。在中唐文學(xué)會里,他是發(fā)起人之一,年齡、地位也最高,自然會處于領(lǐng)袖位置,但他的言談舉止根本看不到一點領(lǐng)袖和長者的派頭,無論在什么場合都是普普通通的一員。每逢讀書會,他就開著他那輛子彈頭面包車,把我?guī)У骄蹠木┒寂哟髮W(xué)。散會時就帶上順道的朋友和學(xué)生,聽著流行歌曲,開車回家。日本的大學(xué)教授都很忙,不光課多,還要擔任不少教務(wù)工作,做研究得擠時間,和中國教授比,那是夠緊張的。但川合先生從來就好整以暇,給人游刃有余的感覺,課沒少上,論文沒少寫,還少不了各種應(yīng)酬,他都應(yīng)付自如。他實在是個很干練的人,這從他的灑脫不拘的外表有時看不出來。
川合先生的學(xué)問就像他的為人,灑脫而通達。他治學(xué)不像一般日本學(xué)者喜歡守著一個問題挖深井,他的知識面和興趣都非常寬,善于思考和把握問題,他的論著涉及的面相當廣,既有《隋書經(jīng)籍志詳考》(與興膳先生合著)那樣的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研究,也有《中國的自傳文學(xué)》那樣獨開生面的探索。他豐富的文學(xué)史知識——西方的和東方的——使他能從一些細微的地方聯(lián)想到許多相關(guān)的問題,并作出綜合性的分析。他的中唐文學(xué)研究能從廣闊的歷史文化和文學(xué)史背景中把握具體問題,使具體問題的闡釋達到不尋常的深度,而那些個案研究得出的具體結(jié)論反過來又充實了他對中唐文學(xué)的宏觀認識,這樣不斷地反復(fù)和互相滲透,他對中唐文學(xué)的把握就越來越全面而深入,當他將自己的基本看法濃縮在《文學(xué)的變?nèi)荨刑莆膶W(xué)的特質(zhì)》這篇短文里發(fā)表時,我們就獲得一些新鮮而富有啟發(fā)性的觀點。他將中國學(xué)者視中唐為古代詩史轉(zhuǎn)折點的看法推廣到整個古代精神史和文學(xué)史,認為中唐在古代文人精神和意識的許多方面都有特別的意義。他在《中國的自傳文學(xué)》中,首先就文人的自我意識問題對上述看法作了初步的闡述。這部著作出版后在日本學(xué)術(shù)界廣受好評,友人蔡毅的中譯本不久即可問世,相信他高瞻遠矚的視野和獨到的文本解讀,會讓中國學(xué)者對許多名作產(chǎn)生新的看法。
從和川合先生的日常交談中,我能感受到他的藝術(shù)感覺和悟性,他對理論思考的重視和對學(xué)術(shù)潮流的敏感,在日本學(xué)者中是很少見的。他和松本肇教授合編的《中唐文學(xué)的視角》體現(xiàn)了日本新一代學(xué)者的嶄新學(xué)術(shù)品格,那就是多層次、多視角地審視文學(xué)現(xiàn)象,并加以綜合研究,在此基礎(chǔ)上形成對文學(xué)史和文化史的全面認識。目前,川合先生又主持了一個關(guān)于中國古代文學(xué)史觀念的合作研究項目,這個選題無疑是站在學(xué)科前沿的,與近年中國大陸的“文學(xué)史學(xué)”遙相呼應(yīng)。陳寅恪先生曾在《陳垣燉煌劫余錄序》里說:“一時代之學(xué)術(shù),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xué)術(shù)之新潮流。治學(xué)之士,得預(yù)于此潮流者,謂之預(yù)流。其未得預(yù)者,謂之未入流。”川合先生正是一位“預(yù)流”的學(xué)者,他對學(xué)術(shù)潮流的敏感,使他的研究總是站在學(xué)術(shù)的前沿。
要說川合先生的學(xué)術(shù)研究,特點是很多的,但在日本學(xué)者中顯得最突出的一點,就是當初讓松本肇強烈地感覺到的一種獨特的個性——一種堅定地將文學(xué)作品作為“文學(xué)”來把握的眼光,他認為這是迄今在日本的中國文學(xué)研究中不曾看到的,它讓人體會到一種論“文學(xué)”的快樂。的確,我讀日本學(xué)者的論文也感到,它們經(jīng)常在清理問題周圍的材料方面花費很多篇幅,而正式進入問題時,往往剛觸及問題核心便草草收束,給人序幕剛拉開就匆匆落幕的印象。當然,這也許與外國人對文學(xué)語言的微妙之處難以把握有關(guān)。但川合先生的論文不是這樣,他研究韓愈文章的敘事、白居易詩的語言、李賀詩的比喻,都能抓住文學(xué)表現(xiàn)的核心,深入闡述作家作品的藝術(shù)心理和藝術(shù)特征,并將他們放到中唐文學(xué)的總趨勢中來認識。這是真正意義的文學(xué)研究。學(xué)生們聽川合先生的課,也總是從中領(lǐng)略到文學(xué)的魅力。蔡毅譯完《中國的自傳文學(xué)》,不無遺憾地對我說,川合先生的文筆如行云流水,特別靈動,譯成中文絕對難以傳達原文的風(fēng)神。我也譯過川合先生的文章,深有同感。
與興膳、川合兩位先生不同,平田先生的專攻是中國語言學(xué)。我曾聽朋友稱贊平田先生是天才,雖然他給人的印象和通常人們對天才的聯(lián)想不太吻合,但我相信朋友的話一定是有根據(jù)的。起碼就現(xiàn)代漢語說,我敢說平田先生是日本學(xué)者中修養(yǎng)最好的人之一。你跟他說話,一般是不太會意識到自己在和外國人說話的,他不光熟練地掌握漢語的正確表達,而且能說地道的口語、方言和一些俗話、俏皮話,最難得的是能體會中國人對漢語的感覺,這是很不容易的。有次在學(xué)校遇到他,正好我剛讀了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就和他說起我的感覺。我覺得陸鍵東太愛用“生命”、“歷史”、“命運”、“文化”、“靈魂”之類的字眼了,有點大而無當,他說陸鍵東的語言很像電視片的解說詞,兩人會心大笑。陸鍵東的語言實際上就是《河觴》的文體,人稱“蘇曉康體”。那不就是電視片的解說詞么?我不知道他是否想到了《河觴》,但對語言的那種感覺是中國人也要佩服的。
平田先生是京都大學(xué)中文專業(yè)第一個到南京大學(xué)留學(xué)的學(xué)生,他的專攻是漢語,很留意方言,曾做過南通方言、吳方言、閩北方言研究,但用力最深的還是安徽徽州方言,1998好文出版社刊行了他主編的《徽州方言研究》,其中休寧方音詞匯語法部分是他多年研究的成果。平田先生的語言研究與傳統(tǒng)的路子,與一般中國學(xué)者的路子都不同,常著眼于語言與文學(xué)的關(guān)系(這一點和南京大學(xué)的古代漢語研究有些接近),更推廣到與文化的關(guān)系。比如他的漢語史研究,著重研究方言、韻書與科舉制度的關(guān)系,又研究早期佛經(jīng)翻譯文本對印度韻律的處理,以究明四聲論是否與梵贊有關(guān),都是中國學(xué)者較少涉及的。1997年11月,我參加他主持的“紀念王國維逝世七十周年詞曲說唱文學(xué)微型討論會”,聽他對休寧方言“笑話兒”中兩種敘事的分析,覺得很有意思。他根據(jù)實地錄音的《賣油郎獨占花魁》的講述,研究了敘事中文言白話夾雜,文語口語夾雜的現(xiàn)象:文言和文語都出現(xiàn)在描繪的部分,白話和口語都出現(xiàn)在敘述部分,與話本小說的文體相似。這無論對民間故事流傳方式及形態(tài)的研究還是對休寧方言研究,都是富有參考意義的。他報告中不時用休寧話敘述故事,維妙維肖。
平田先生雖以語言學(xué)為專攻,但他關(guān)注的經(jīng)常是語言背后的文化內(nèi)容,也許語言只是他接近文化,進入文化研究的一個門檻。所以他的方言研究常與地域文化相關(guān),論著中處處顯示出超越語言的省察和對文化的關(guān)注,他對送灶這一北方習(xí)俗南漸過程的考察便是一例。他為研究徽州方言,幾乎每年都要到休寧去做調(diào)查。他對休寧和它懷抱的文化傳統(tǒng)深有感情,看到當?shù)厝瞬鹣路课萁ㄖ系拇u雕、金屬造型等,放在家門口當文物賣,他十分痛惜。要知道,那都是明清時代遺留下來的徽式傳統(tǒng)建筑啊!他痛感,徽州文化正在沒有文化的徽州人手中敗落,為之悲哀而又無奈。我總覺得,平田先生在三位先生中雖然最年輕,卻最有傳統(tǒng)的文人情調(diào),他思考問題和評價歷史人物格外帶有一種人文的關(guān)懷。我曾以為他是經(jīng)院學(xué)究氣很濃的學(xué)者——初和他接觸或看一兩篇論文,是會有這種印象的,但逐漸熟悉就不是那種感覺了。如果你讀過《學(xué)人》第十輯上的《讀陳寅恪〈四聲三問〉》,一定會同意我的看法。他對陳寅恪兩次亡國體驗的揭示和剖析,足見他對陳寅恪理解之深,那第二次亡國體驗迄今未見中國學(xué)者中有人意識到。
平田先生其實也是個風(fēng)趣的人,雖然他給人的感覺是對任何事情都很認真,說話語調(diào)平緩,一板一眼,但仔細琢磨,他的話里都有味道。而且認真一旦成為風(fēng)格,在某些場合,反差的效果就會使那認真轉(zhuǎn)化為一種幽默。比如,他會在一個四川學(xué)生的錄音電話里留言:“我是平田。我有辣的辣椒,你如想要,請來電。”十分地道的公文體。過幾天,他又來電話:“辣的辣椒來了。”平田先生平時對學(xué)生是很嚴厲的,教訓(xùn)起來決不留情面,你想,當你聽熟了的那個認真嚴肅的聲音從電話那端傳來,不是和你談學(xué)業(yè)或工作,而是告訴你,他馬上就要有辣的辣椒時,你會是什么感覺?反正我聽說這個段子時,是樂個不止。平田先生的幽默是抑制的,正像他大笑時笑得瞇起眼睛,皺緊眉頭,但聲音卻壓在鼻腔里。
一年的時間很快過去,和三位先生剛熟悉便又分別,分別的一年也很快過去。其間我參加中唐文學(xué)會,再度見到三位先生,已是一回生兩回熟的故人了。我這個人天性懶惰,說得好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沒事很少聯(lián)絡(luò),也疏于問候。但對三位先生的記憶和印象卻日深一日,正所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既然“心乎愛矣,遐不謂矣”,遂涉筆成文,聊寄暮云春樹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