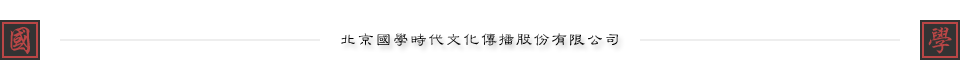《現(xiàn)代學(xué)林點(diǎn)將錄》:給“知道分子”的一份厚禮
作者簡介:李廷華,原籍湖北宜昌,1951年出生于重慶,長期從事文藝創(chuàng)作及文化學(xué)術(shù)研究,國際書法家協(xié)會理事。
一
近年能夠讓人把卷必盡之書,當(dāng)推胡文輝《現(xiàn)代學(xué)林點(diǎn)將錄》,作者因懶讀外語,大學(xué)本科未畢業(yè),卻多年沉浸書齋,將百年來學(xué)術(shù)脈絡(luò)學(xué)人著作學(xué)人關(guān)系理會如數(shù)家珍。自從《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風(fēng)行以來,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的通俗化功莫大焉。若余英時在“陳寅恪研究的反思與展望”一文里所云:很多人并非十分了解陳寅恪的學(xué)術(shù),就是因?yàn)椤蔼?dú)立精神、自由思想”而對他產(chǎn)生敬意。此敬意實(shí)非同小可,它將半個世紀(jì)以來的學(xué)術(shù)中心和邊緣幾乎調(diào)換了位置。現(xiàn)在的讀者,生活在信息網(wǎng)絡(luò)間,某方面的專才固然時時在各種大學(xué)里制造,然欲得自家身心之修養(yǎng),做一個“知道分子”即成必然。《點(diǎn)將錄》作者說:他做的學(xué)問,不是吃豬肉而是看豬跑,此種大觀之趣,豈不正入“知道分子”青眼?將眾多博學(xué)鴻儒斯文之輩拉往梁山泊好漢行列里坐上一把交椅,過去已有不少人做過,做得最精彩的可能還是今人,是書串綴諸多學(xué)人逸聞,近掌故之學(xué),評論自具一家之眼,且縱橫間每見幽微,會心處可撩識者掀髯。點(diǎn)評當(dāng)世人物,反響盈睫,為撰文著書之便宜,而物議紛然,又易生杯葛。《點(diǎn)將錄》先在報章連載又得出版,顯然注意到盡量避免麻煩。若王先謙與裘錫圭,二者年歲相距近一百年,天上人間,因距離而得自由。此書寫法取淺易文言,箋短墨珍,于具體人物評鑒中顯一代學(xué)術(shù)之端倪,不言體系,而條貫自在,隱約間有錢鍾書為文意味,又于每篇后以七言絕句為結(jié),提綱挈領(lǐng),莊諧互見,才士風(fēng)雅,實(shí)稱難能。
二
當(dāng)代學(xué)術(shù)史在很大成分上是學(xué)人的思想改造史和精神扭曲史,《點(diǎn)將錄》于此關(guān)節(jié),頗能著墨。以啟功為例,若欲了解啟功學(xué)術(shù)思想之變衍,與其師陳垣聯(lián)系,更得明晰。陳垣由顯宦而學(xué)術(shù),為歷史學(xué)界泰斗,堪與陳寅恪南北望,然心氣之差,迥若霄壤,其致楊樹達(dá)函,勸其“不法高郵法韶山”,實(shí)以自謂謂人。陳寅恪聞之對楊氏戲言云:自家出生長沙,倘攀緣亦有自也。狂狷之氣必顯。亦可反襯援庵夫子及門下雖與時俱進(jìn),終難免白首之羞。
《點(diǎn)將錄》于馮友蘭之學(xué)術(shù)成就,謂為“哲學(xué)界一人”,對其人生“四重境界”說則侃切論之:“設(shè)論固可謂道貌岸然,玄之又玄,然而反觀馮氏自身的人生實(shí)踐,亦不過隨波逐流之輩,一生更不脫‘應(yīng)帝王’情結(jié)。則其人去‘道德境界’尚遠(yuǎn),猶在‘功利境界’中也。”“名實(shí)雙行”于吾華文人漸成風(fēng)習(xí),名班大老豈任無咎?于茲更見“獨(dú)立精神、自由思想”之可貴。作者立論,固以著作成就為標(biāo)準(zhǔn),人格道義之價值,亦不懸置。如吳宓,抗戰(zhàn)期間在華西與陳寅恪、李方桂、蕭公權(quán)同稱“四大名旦”,作者以為四人學(xué)問成就不可同日而語,又在注釋中說:“惟吳氏在學(xué)問雖無足道,但其日記,詩集于世事與心事皆能直書無忌,實(shí)為現(xiàn)代知識分子最寶貴的精神檔案。”吳宓之學(xué)問是否“無足道”還可商量。余英時謂五十年代以后,大陸學(xué)者堅(jiān)持獨(dú)立精神自由思想者當(dāng)首推陳、吳二公。錢鍾書晚年最后文章乃為《吳宓日記》寫序,深情感慨,為其一生文字僅見。不亦可參乎?作者注重《吳宓日記》之價值,亦當(dāng)有會心之發(fā)焉。
作者廣搜學(xué)人逸聞,以饋?zhàn)x者,其中取舍,固已甚大膽,于某些人物,似還有手下留情處,比如湯用彤,其《魏晉南北朝佛教史》之價值,學(xué)界故無異詞。作者說湯用彤因患腦溢血而“得免與世周旋”,觀《吳宓日記》,湯氏之不幸去世,因醫(yī)院外街頭游戲隊(duì)伍高喊口號,老先生在病床上躍起跟隨高呼,急癥而不治。可謂周旋到底也。凡此,皆堪謂時代哀歌,學(xué)人痛史。
三
《點(diǎn)將錄》于學(xué)人比較評述間,亦梳理脈絡(luò),以見世紀(jì)文化流向。將余英時列于三十六地煞星之首,可見推崇之意。余氏學(xué)術(shù),于考據(jù)、義理二途融匯為之。乾嘉以來,考據(jù)之學(xué)大盛,多論以清學(xué)為宋學(xué)之反動而徑庭。余氏則詳為辨析,認(rèn)為清學(xué)亦宋學(xué)之繼承,此雖在前人已有道及,然泯宋學(xué)與清學(xué)于無跡,得考據(jù)與義理為一身,余氏實(shí)得其大觀(讀其《方以智晚節(jié)考》,對任道斌之《方以智年譜》資料詳盡卻不能點(diǎn)出方氏自沉乃出抗清心志,竟直斥任著為“有眼無珠”)。 考據(jù)、義理皆不能盡其意,余氏又經(jīng)常對社會話題公開發(fā)表意見,蓋出學(xué)人終必盡社會責(zé)任之義也。
《點(diǎn)將錄》謂李方桂與王力為“海內(nèi)外最有影響的兩大古音體系”而李更為“精審”。點(diǎn)睛之余,又施渲染之墨,言其岳父徐樹錚之不凡(參觀馮玉祥《我的生活》,馮氏對徐殺之不足,更加痛罵,似為一不赦之巨奸)。《點(diǎn)將錄》引述罕見之籍謂徐氏“僅率一旅之孤軍,迫使外蒙古取消自治,承認(rèn)中華民國主權(quán),一時震動朝野”,并有著作《建國詮真》等,顯然徐氏非一赳赳武夫,其中底細(xì),有興趣者還可探究。然搜書不到海外,又豈能得其大觀?《點(diǎn)將錄》以窮搜而遍覽,廣讀者以見聞,良可贊矣。
容庚在淪陷期間任職偽北大,勝利后傅斯年堅(jiān)不聘請,謂若聘請此等教授即無以對流離大后方者,其說廣被人口,而容氏亦不示弱,發(fā)表公開信認(rèn)為“政府無力撤退全體淪陷區(qū)人民,即得寬容其生存”。女作家蘇青文字被援例,亦具同理。以后,學(xué)府大批胡適、傅斯年、曾經(jīng)真正落水之周作人亦跟隨痛罵,而容庚則教育學(xué)生對傅斯年之成績不可忽視,文人之所謂骨氣,當(dāng)從一生終始幽微處考量。
聞一多于西南聯(lián)大時云:“在今天抗日戰(zhàn)爭時期,誰還熱心提倡寫舊詩,他就是準(zhǔn)備作漢奸!汪精衛(wèi)、鄭孝胥、黃秋岳,哪一個不是寫舊詩的赫赫名家?”此真可謂偏激之言。當(dāng)時國民黨于右任、賈景德等,共產(chǎn)黨毛澤東、朱德等、社會賢達(dá)郭沫若、柳亞子等,無不作舊詩。聞一多先學(xué)美術(shù),曾為北京美專教務(wù)長,后專治古典詩歌,又關(guān)心政治,先右后左,不幸遇難后聯(lián)大師生悼念捐款,吳宓拒捐,因其與聞氏素不睦也。此《吳宓日記》中親述,可參觀。
一書之中,議論明賅,材料豐富之外,倘字里行間更呈現(xiàn)可以深入之學(xué)術(shù)話題,則讀者呼快矣。胡道靜對沈括《夢溪筆談》之推崇,以為較司馬遷《史記》更有價值,為宋代則惟一。《點(diǎn)將錄》作者認(rèn)為“推崇因至過當(dāng)”,予讀者繼續(xù)尋繹宋代文化學(xué)術(shù)之成就很大空間,如沈括與蘇軾之比較,或即可破胡氏之論。又如,吳梅以曲學(xué)擅名,擬之“鐵叫子”至為恰切,將吳梅之學(xué)與王國維比較,連類書畫等學(xué)術(shù)門類而謂吳梅之學(xué)為本色當(dāng)行,其價值即不同也。又于注釋中引述其日記,說明在溥儀立滿洲國,及日本于全面侵華前分割華北等政治問題,遠(yuǎn)離政治之吳梅均有其獨(dú)特看法。“此真是世俗所謂‘漢奸’論調(diào)矣,以其出語奇兀,世所罕知,特附見于此”。學(xué)術(shù)、讀書最終是無禁區(qū)的。多年來讀書人的眼光在逐漸開闊,也逐漸細(xì)微,很多歷史問題在逐漸清晰,也愈加復(fù)雜,辯幽索微永遠(yuǎn)是學(xué)術(shù)的責(zé)任和動力,也是學(xué)人之興趣及功課。《點(diǎn)將錄》于茲會心多,亦引讀者解頤頻。
四
當(dāng)下文風(fēng)澆漓,強(qiáng)不知以為知者多矣,一書之著,以知識豐富而益讀者,為基本道德,《點(diǎn)將錄》于知識之豐富性即學(xué)習(xí)錢鍾書之“充類至盡”,論列間不吝連類舉引,幾成百年學(xué)人關(guān)系淵源之大觀,又似著作觀點(diǎn)異同之引得,實(shí)為讀書用心之真收獲。
以梁山泊好漢之綽號形于現(xiàn)代學(xué)人,固為有趣,亦稱難事,當(dāng)年汪辟疆作《光宣詩壇點(diǎn)將錄》,將陳衍列于七十二地煞之列,即招致不滿。具體評價中,言康有為詩“傷摹擬”,亦被其耿耿多時,蓋南海自命詩超蘇黃,學(xué)術(shù)更有哥倫布開創(chuàng)新大陸之功也。近世見劉再復(fù)言《紅樓夢》而大貶《三國》、《水滸》,謂為“中國人的地獄”。若以學(xué)人評論之事,任其以梁山好漢排座次必不為也。故知“點(diǎn)將”之行,實(shí)以趣味漫漶學(xué)術(shù)也,恰切者少,而難配者多。若以中箭虎擬陳夢家甚切,以丑郡馬謂周祖謨亦恰,他若因善雕刻而擬聞一多為玉臂匠,以研曲而位吳梅以鐵叫子,以善書而稱啟功圣手書生,以能研究能創(chuàng)作譽(yù)錢鍾書雙槍將,尚各得其位,余者則多難湊泊。女將三員,只得馮沅君一人膺母夜叉之位,一丈青則遺芮逸夫,母大蟲贈汪寧生,此雖玩笑細(xì)故,無從認(rèn)真,然現(xiàn)代學(xué)人,果不能再尋繹女性二人而充梁山泊快樂之場乎?是所以作《點(diǎn)將錄》亦勉為其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