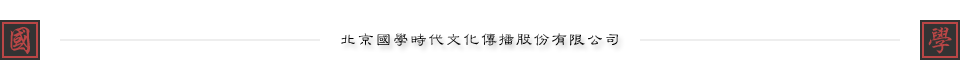被屏蔽的民國(guó)文學(xué)史需重寫(xiě)
如果要問(wèn)民國(guó)詩(shī)人,能夠勉強(qiáng)數(shù)得出來(lái)的,也只有“柳老”、“郭老”等寥寥幾人而已
說(shuō)到舊體詩(shī)詞,受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人們一度以為“唐詩(shī)”、“宋詞”、“元曲”以下,皆不足論,后來(lái)漸漸覺(jué)得清詩(shī)清詞也達(dá)到了非常高的水準(zhǔn)。然而民國(guó)呢?人們心目中可稱(chēng)之為詩(shī)家的民國(guó)人物有幾?
民國(guó)時(shí)期當(dāng)然也是有詩(shī)家的。猶記上世紀(jì)七八十年代束發(fā)讀書(shū),語(yǔ)文課本中自然已是白話(huà)文一統(tǒng)天下,但多少也會(huì)收錄幾首舊體詩(shī)詞,一般都是毛澤東和他人唱和的作品。從此留下了一個(gè)近乎頑固的印象:近現(xiàn)代人中,只有毛澤東和與他唱和的“柳老”、“郭老”才寫(xiě)得了舊體詩(shī)詞。
那時(shí)的求知欲真叫一個(gè)饑渴,剛剛背誦了課本中的“山舞銀蛇,原馳蠟象”,便四處搜尋《毛主席詩(shī)詞》。村里缺乏藏書(shū)的家庭,那所鄉(xiāng)村學(xué)校也沒(méi)有圖書(shū)室,碰巧一位當(dāng)過(guò)知青的老師偏偏有一冊(cè)《毛主席詩(shī)詞》,這位老師碰巧又對(duì)我有所偏愛(ài),慷慨允諾我可以借讀一周。就這樣,以一周的時(shí)間,我手抄了一本《毛主席詩(shī)詞》,現(xiàn)在還和其他七八本讀書(shū)筆記一起躺在我家書(shū)柜的最深處,也算是給自己當(dāng)年的勤奮留下了一個(gè)見(jiàn)證。
有意思的是,自己當(dāng)年的這個(gè)印象其實(shí)相當(dāng)普遍。曾經(jīng)問(wèn)過(guò)幾個(gè)多少還保留了一點(diǎn)讀書(shū)興趣的同齡人,說(shuō)起唐宋元明直至晚清的著名詩(shī)詞家,差不多都爛熟于心,但如果要問(wèn)民國(guó)詩(shī)人,能夠勉強(qiáng)數(shù)得出來(lái)的,也只有“柳老”、“郭老”等寥寥幾人而已。
感謝出版界近年來(lái)推出了許多民國(guó)詩(shī)詞專(zhuān)集,類(lèi)似《民國(guó)舊體詩(shī)史》、《民國(guó)詞史》等總結(jié)性的著作也連綿不絕。
原來(lái),民國(guó)詩(shī)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除了胡漢民、譚延闿等政要,民國(guó)時(shí)每一個(gè)有根底的學(xué)者,因?yàn)槎荚?jīng)受過(guò)系統(tǒng)的舊學(xué)訓(xùn)練,不但幾乎人人能夠做舊體詩(shī)詞,而且質(zhì)量都很高。王國(guó)維、陳寅恪、錢(qián)鐘書(shū)、錢(qián)仲聯(lián)等最近幾年方有大名的詩(shī)家除外,隨便舉幾個(gè)剛有專(zhuān)集出版而尚未為一般讀者熟知的人物,如《忍寒樓詩(shī)詞歌詞集》的作者龍榆生,《玄隱廬詩(shī)》的作者潘伯鷹,《還軒詞》的作者丁寧,誰(shuí)的作品不是格律謹(jǐn)嚴(yán)、技巧純熟?讀《陳垣來(lái)往書(shū)信集》,意外發(fā)現(xiàn)了譚家菜的創(chuàng)始人譚祖任的兩首七律,情韻深厚堪為老手,但其存留的作品很可能也就只有這兩首了。盡管如此,譚祖任還是幸運(yùn)的,其他至今無(wú)人知曉的民國(guó)詩(shī)人正不知凡幾。
與上述詩(shī)人對(duì)照,“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然不能算詩(shī)家應(yīng)有之吐屬。柳亞子先生負(fù)有重名,據(jù)說(shuō)是“慨當(dāng)以慷,卑視陸游陳亮”,但那厚厚兩巨冊(cè)的《磨劍室詩(shī)詞集》證明這種評(píng)價(jià)實(shí)在只是泛泛之語(yǔ)。以我個(gè)人的私見(jiàn),柳詩(shī)容易誤導(dǎo)后世的一個(gè)最大缺點(diǎn)就是詩(shī)歌功能的畸變。詩(shī)歌本為抒寫(xiě)心靈之載體,而在柳氏這兒,因?yàn)樗贵犹唬煊谠?shī),做個(gè)七言八句毫不為難,于是詩(shī)歌幾乎成為日常交際應(yīng)酬之工具,大多數(shù)作品只能說(shuō)是“用韻語(yǔ)說(shuō)話(huà)”了。
多翻幾本民國(guó)學(xué)者的詩(shī)詞集,就知被遮蔽的民國(guó)詩(shī)人太多。舊體詩(shī)詞也是文學(xué)之一種,民國(guó)以來(lái)的文學(xué)史不認(rèn)真重寫(xiě)怎么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