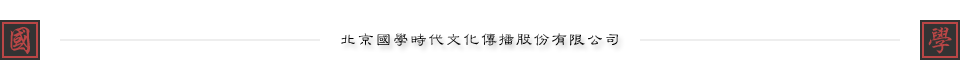唐傳古樂(lè)譜和與之相關(guān)的音樂(lè)文學(xué)問(wèn)題
內(nèi)容提要:唐傳古樂(lè)譜研究是本世紀(jì)國(guó)際漢學(xué)的重要課題。本文在回顧這一課題的學(xué)術(shù)史的基礎(chǔ)上,對(duì)《從古樂(lè)譜看樂(lè)調(diào)和曲辭的關(guān)系》一文涉及的幾個(gè)問(wèn)題作了重新討論。本文認(rèn)為:唐傳古樂(lè)譜基本上是器樂(lè)譜,不應(yīng)隨意夸大它的音樂(lè)文學(xué)價(jià)值;唐代曲拍有豐富多樣的表現(xiàn)形式,不存在一個(gè)普適于諸多樂(lè)曲的曲拍—句讀對(duì)應(yīng)規(guī)則;為古譜配辭須達(dá)到詞、曲在段式、句式、拍式等方面的一致,以及詞組語(yǔ)調(diào)和樂(lè)譜音調(diào)之間的諧和,而不能忽略譜中的樂(lè)理。本文并介紹了一種結(jié)合文獻(xiàn)、文物、民間遺存,建立音調(diào)與歷史的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的研究思路。
作者簡(jiǎn)介:王小盾,1951年生,上海師范大學(xué)、揚(yáng)州大學(xué)教授;陳應(yīng)時(shí),1935年生,上海音樂(lè)學(xué)院教授。
唐傳古樂(lè)譜和長(zhǎng)短句詞的起源,是本世紀(jì)中國(guó)音樂(lè)學(xué)、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研究的兩個(gè)重要課題。前者意味著古譜學(xué)的全面突破,后者則是中國(guó)詩(shī)體史研究的一個(gè)關(guān)鍵,故曾引起廣泛注意。最近,葛曉音、戶(hù)倉(cāng)英美兩位教授在《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1]上發(fā)表《從古樂(lè)譜看樂(lè)調(diào)和曲辭的關(guān)系》一文,重新提到這兩個(gè)問(wèn)題,表明還有探討它們的必要。此文試圖在古樂(lè)譜中找到一些“詞樂(lè)相配規(guī)則”,并以此為依據(jù)去考察唐代聲辭配合的規(guī)則、齊言和雜言曲辭的音樂(lè)根源、同調(diào)異體的成因,實(shí)際上提出了把這兩個(gè)問(wèn)題結(jié)合起來(lái)加以解決的思路。這思路是具有創(chuàng)新意義的,正因?yàn)檫@樣,我們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慎重對(duì)待,作進(jìn)一步的證實(shí)或否證。另外,文中批評(píng)了中國(guó)的兩類(lèi)學(xué)者──唐代音樂(lè)文學(xué)研究者和中國(guó)音樂(lè)史研究者,認(rèn)為“由于古樂(lè)譜的解讀比較困難”,前一類(lèi)學(xué)者“始終未能深入到古樂(lè)譜的內(nèi)部去探索樂(lè)調(diào)與歌辭相配合的規(guī)則,因此不少論證仍停留在推測(cè)和駁論上”;后一類(lèi)學(xué)者則“對(duì)于保存在日本的唐代樂(lè)譜所知甚少,也不能將中日雙方所有的資料文獻(xiàn)融會(huì)貫通,加之譯譜中的技術(shù)障礙較多,更無(wú)暇顧及聲辭配合的研究”。這些批評(píng)涉及學(xué)術(shù)史上的是非,亦應(yīng)加以明辨。有鑒于此,我們擬以此文,對(duì)唐傳古樂(lè)譜和與之相關(guān)的音樂(lè)文學(xué)問(wèn)題──樂(lè)譜的發(fā)現(xiàn)和研究、其性質(zhì)及其配辭的可行性、其曲拍規(guī)則以及所謂“半逗律”──作一綜合討論。
一、唐傳古樂(lè)譜的發(fā)現(xiàn)和研究
“唐傳古樂(lè)譜”指的是記錄了唐代樂(lè)曲的古譜。除本世紀(jì)初在敦煌莫高窟發(fā)現(xiàn)的敦煌樂(lè)譜(今存法國(guó)國(guó)家圖書(shū)館)之外,它們大部分保存在日本。其中包括由南朝梁丘明所傳的唐寫(xiě)本《碣石調(diào)·幽蘭》古琴文字譜,也包括《天平琵琶譜》(抄寫(xiě)于747年前)、《五弦琵琶譜》(抄寫(xiě)于842年)、《南宮琵琶譜》(成書(shū)年代不詳,“南宮”指的是日本貞保親王,生于870年,卒于924年),以及記錄日本所傳唐曲的《博雅笛譜》(源博雅編,成書(shū)于966年)、《仁智要錄》箏譜(藤原師長(zhǎng)編,約成書(shū)于1171年)、《三五要錄》琵琶譜(藤原師長(zhǎng)編,約成書(shū)于1171年)、《鳳笙譜》(約成書(shū)于1201年)、《新撰笙笛譜》(約成書(shū)于1303年)。作為“唐傳古樂(lè)譜”,這些古譜所錄的曲目往往見(jiàn)于唐代文獻(xiàn)和敦煌寫(xiě)卷,或見(jiàn)于唐宋時(shí)期的集部書(shū),有與之同名的唐宋詩(shī)詞作品。毫無(wú)疑問(wèn),它們具有重要的學(xué)術(shù)價(jià)值;所以從本世紀(jì)30年代開(kāi)始,受到學(xué)術(shù)界密切關(guān)注。
這種關(guān)注之成為事實(shí),乃得力于某種機(jī)緣,亦即敦煌樂(lè)譜的發(fā)現(xiàn)。最初發(fā)現(xiàn)敦煌樂(lè)譜的人是法國(guó)的伯希和。1910年左右,這些樂(lè)譜被伯希和劫往巴黎;但在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里,其性質(zhì)卻是隱晦不明的。直至1937年初夏,由于一個(gè)偶然的機(jī)會(huì),日本學(xué)者林謙三見(jiàn)到了來(lái)自法國(guó)的十一張敦煌樂(lè)譜照片,遂根據(jù)閱讀同類(lèi)古譜的經(jīng)驗(yàn),判斷這是一批琵琶古譜。他于是在平出久雄的協(xié)助下,把它們和《天平琵琶譜》、《五弦琵琶譜》作了比較研究,分別于1938年、1940年發(fā)表了《琵琶古譜之研究──<天平>、<敦煌>二譜試解》、《國(guó)寶五弦譜及其解讀之端緒》二文,并譯出七首樂(lè)譜[2]。1955年,他進(jìn)一步用英文發(fā)表了專(zhuān)題論文《中國(guó)敦煌古代琵琶譜的解讀研究》以及P.3808二十五首樂(lè)譜的譯譜[3]。1957年,此文經(jīng)過(guò)修訂,改名為《敦煌琵琶譜的解讀研究》,由潘懷素譯成中文在上海音樂(lè)出版社出版。1969年,林氏再次修訂此文和譯譜,編入他所著的《雅樂(lè)──古樂(lè)譜的解讀》一書(shū)[4]。在這本書(shū)中,林謙三還發(fā)表了《天平琵琶譜<番假崇>的解讀》和《全譯五弦譜》二文。
林謙三是在1976年逝世的。當(dāng)其在世之時(shí),英國(guó)學(xué)者畢鏗(L.E.R.Picken)亦開(kāi)始了唐傳古譜研究。40年代,畢鏗曾作為生物學(xué)家,以英國(guó)議會(huì)科學(xué)使團(tuán)成員的身份來(lái)到中國(guó),在結(jié)識(shí)了幾位琴家之后,與中國(guó)古代音樂(lè)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當(dāng)他為《新牛津音樂(lè)史》撰稿時(shí),就解譯了姜白石的俗字譜歌曲、減字譜琴歌《古怨》以及《事林廣記》中的俗字譜樂(lè)曲。此后,他把中國(guó)古譜研究變成自己的專(zhuān)業(yè)。1972年,在赴日本搜集和復(fù)制了大批資料之后,他在劍橋大學(xué)組建了以研究唐傳古樂(lè)譜為中心的課題組。德國(guó)的沃帕特(R.F.Wolpert)、新西蘭的曼瑞特(A.J.Marett)、瑪卡姆(E.J.Markham)、美國(guó)的康迪特(J.Condit)、日本的三谷陽(yáng)子、澳大利亞的尼克森(N.Nickson)等先后參加了這一課題組的研究活動(dòng)。課題組研究的唐傳古樂(lè)譜,有《五弦琵琶譜》、《博雅笛譜》、《仁智要錄》箏譜、《三五要錄》琵琶譜、《鳳笙譜》、《新撰笙笛譜》等。有關(guān)研究論文陸續(xù)刊載在由畢鏗主編的《亞洲音樂(lè)》第一至第六輯。自80年代起,畢鏗又在課題組譯譜的基礎(chǔ)上,致力于編寫(xiě)多卷本《唐宮遺音》[5]。這一時(shí)期,澳大利亞的耐爾森(S.G.Nelson)、羅珂麗(C.Rockwel)、日本的峰雅彥、英國(guó)的韋滿(mǎn)易(M.Wells),也投入了唐傳古樂(lè)譜研究[6]。
中國(guó)學(xué)者對(duì)于古樂(lè)譜的研究并不遲于外國(guó)。約在二百多年前,在發(fā)現(xiàn)元末陶宗儀的《白石道人歌曲》手抄本之后,詞學(xué)界即曾出現(xiàn)研究姜白石歌曲的熱潮。方成培《香研居詞麈》(1777)、戴長(zhǎng)庚《律話(huà)》(1833)、張文虎《舒藝室余筆》(1862)等專(zhuān)著,都對(duì)姜白石用俗字譜記寫(xiě)的詞調(diào)歌曲作了研究和詮釋。到本世紀(jì),學(xué)者們進(jìn)一步致力于把姜白石的全部歌曲譯成工尺譜。任二北的《南宋詞之音譜拍眼考》(1927)、唐蘭的《白石道人歌曲旁譜考》(1931)、夏承燾的《白石道人歌曲旁譜辨》(1932)、楊蔭瀏和陰法魯?shù)摹端谓资瘎?chuàng)作歌曲研究》(1957)以及丘瓊蓀的《白石道人歌曲通考》(1959),逐步完善了翻譯姜白石十七首俗字譜歌曲、一首琴歌和十首律呂字譜歌曲的工作。其后姜譜的研究者尚有饒宗頤、趙尊岳等人。盡管諸家在譜字音高和節(jié)拍節(jié)奏等方面尚未達(dá)到一致的看法,但他們對(duì)姜譜的翻譯和研究,畢竟為唐傳古樂(lè)譜研究奠定了基礎(chǔ)。
在中國(guó)學(xué)者中,最早注意到敦煌樂(lè)譜的是王重民和任二北。如果說(shuō)王重民在《敦煌曲子詞集》(1950)中只是表示了把敦煌樂(lè)譜、舞譜“被諸管弦,施于步伐”的愿望,那么,任二北《敦煌曲初探》(1954)便做了許多具體的論證工作。在《曲調(diào)考證》一節(jié),他考訂了敦煌樂(lè)譜中的《傾杯樂(lè)》、《西江月》等曲;在《后記》中,他論證了敦煌樂(lè)譜諸樂(lè)調(diào)和同名曲辭之間的關(guān)系“非一字一聲”。此外,他提出了“譜內(nèi)例以‘、’為眼,以‘□’為拍”,《伊州》等“乃大曲之譜”的著名判斷。正是這些見(jiàn)解,到1982年葉棟等人重新翻譯敦煌樂(lè)譜二十五曲[7]之時(shí),成為新一輪樂(lè)譜研究熱潮的理論依據(jù)。這些情況,陳應(yīng)時(shí)在《敦煌樂(lè)譜論著書(shū)錄解題》和《敦煌樂(lè)譜研究五十五年》二文[8]中作了詳細(xì)介紹。
關(guān)于中國(guó)學(xué)者對(duì)于其它唐傳樂(lè)譜的研究,則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jì)。在黎庶昌、楊守敬刻印于1883年的《古逸叢書(shū)》中,即有傳存于日本的唐寫(xiě)本《碣石調(diào)幽蘭》琴譜。此譜后在楊宗稷《琴學(xué)叢書(shū)》(1911─1919)中被譯為減字譜和工尺譜;至五十年代,又被查阜西、管平湖、姚丙炎、徐立蓀、吳振平等人譯為五線(xiàn)譜[9]。80年代,陳應(yīng)時(shí)、吳文光、戴曉蓮、王德塤、戴微等人相繼加入《碣石調(diào)·幽蘭》文字譜的研究行列[10]。與此同時(shí),何昌林開(kāi)始了對(duì)《天平琵琶譜》、《五弦琵琶譜》的研究,陳文成解譯了《博雅笛譜》中的《泛龍舟》曲,葉棟、關(guān)也維等人研究了《五弦琵琶譜》和《仁智要錄》箏譜,陳應(yīng)時(shí)《論唐傳樂(lè)譜中的節(jié)拍節(jié)奏》一文中則有解譯《天平琵琶譜》、《五弦琵琶譜》、《博雅笛譜》、《仁智要錄》諸譜樂(lè)曲的實(shí)例[11]。
上述古譜研究,事實(shí)上已成為二十世紀(jì)學(xué)術(shù)史的重要景觀。研究者們考訂了樂(lè)譜的指法和譜字,確認(rèn)了樂(lè)器的定弦和樂(lè)曲的定調(diào),使諸敦煌樂(lè)譜譜字音高的翻譯問(wèn)題獲得解決。不過(guò),由于這些譜式往往沒(méi)有明確的節(jié)拍節(jié)奏符號(hào),或存在這類(lèi)符號(hào)而未有足夠資料證實(shí)其具體涵義,故唐傳古樂(lè)譜的節(jié)拍節(jié)奏問(wèn)題,仍是爭(zhēng)論中的問(wèn)題。在這種情況下,能否依據(jù)古譜研究的一家之說(shuō),就斷言“樂(lè)理”如何、曲辭與節(jié)拍的對(duì)應(yīng)規(guī)則如何呢?這是有待商議的。但有一點(diǎn)可以肯定:所謂中國(guó)學(xué)者“對(duì)于保存在日本的唐代樂(lè)譜所知甚少,也不能將中日雙方所有的資料文獻(xiàn)融會(huì)貫通”的認(rèn)識(shí),并不符合客觀事實(shí)。
二、唐傳古樂(lè)譜的配辭問(wèn)題
在中國(guó)樂(lè)譜史上,唐代是一個(gè)特別的時(shí)代。見(jiàn)于記載的唐前樂(lè)譜,除《碣石調(diào)幽蘭》外,只有《禮記》鼙鼓譜、《漢書(shū)藝文志》“聲曲折”和《隋書(shū)經(jīng)籍志》著錄的三種琴譜、篳篥譜。而現(xiàn)存的唐傳樂(lè)譜,卻至少有九種之多;見(jiàn)于唐人詩(shī)文和歷代書(shū)目的樂(lè)譜,則不可計(jì)數(shù)。因此可以說(shuō),唐代是樂(lè)譜正式登上歷史舞臺(tái)的時(shí)代。但唐代樂(lè)譜和宋元明清各代留存的樂(lè)譜——例如《風(fēng)雅十二詩(shī)譜》、《白石道人歌曲》、熊朋來(lái)《瑟譜》、《魏氏樂(lè)譜》、《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等歌曲譜——不同,一概不配歌辭,僅適用于古琴、五弦琵琶、四弦琵琶、笛、箏、笙等樂(lè)器演奏。因此又可以說(shuō),唐代是器樂(lè)譜的時(shí)代。
唐代器樂(lè)譜的繁盛,是同胡地器樂(lè)曲的大批輸入有關(guān)的。李×詩(shī)云:“梵樂(lè)奏胡書(shū)。”王建詩(shī)云:“旋翻曲譜聲初起。”花蕊夫人《宮詞》:“盡將篳篥來(lái)抄譜。”《酉陽(yáng)雜俎》卷十二:寧王“讀龜茲樂(lè)譜”。這都是唐樂(lè)譜具有胡樂(lè)淵源的證明。因?yàn)椤昂鷷?shū)”、“龜茲樂(lè)譜”反映了西域樂(lè)譜在中土的流行;篳篥原是胡樂(lè)器[12];而所謂“翻”,則可以理解為在歌曲與器樂(lè)曲之間、或在一種器樂(lè)譜與另一種器樂(lè)譜之間的轉(zhuǎn)換,實(shí)際上是不同文化之間的翻譯。[13]考慮到唐代樂(lè)譜作為器樂(lè)譜、作為外來(lái)樂(lè)譜的性質(zhì),我們應(yīng)當(dāng)慎重地對(duì)待為其配辭的工作。也就是說(shuō),我們不妨嘗試在這些無(wú)歌辭樂(lè)譜中尋找“詞樂(lè)相配規(guī)則”,但倘若進(jìn)一步,以此作為推求某些普遍規(guī)律的依據(jù),那么就顯得輕率了。
學(xué)術(shù)史上的事實(shí)是:為了擴(kuò)大古代歌曲研究的資料范圍,也為了探討敦煌樂(lè)譜的音樂(lè)風(fēng)格,音樂(lè)研究者審慎而積極地為敦煌樂(lè)譜作了詞曲組合試驗(yàn)。這種試驗(yàn)的可行性也可以用上文說(shuō)的“翻”字來(lái)證明。劉禹錫詩(shī):“聽(tīng)唱新翻《楊柳枝》。”《樂(lè)府詩(shī)集·近代曲辭·水調(diào)》:“笛倚新翻《水調(diào)歌》。”花蕊夫人《宮詞》:“新翻酒令著詞章。”可見(jiàn)有些唐代器樂(lè)譜曾用于歌曲伴奏,也有一些器樂(lè)曲脫胎于歌曲。根據(jù)以下兩點(diǎn),我們且可進(jìn)一步找出這類(lèi)可歌之譜的存在:
(一)在今存的唐傳古樂(lè)譜中,有不少曲名即為唐代的曲子辭名。它們或見(jiàn)諸《教坊記》等唐代文獻(xiàn),或有同名歌辭尚存。例如《五弦琵琶譜》中有《王昭君》、《夜半樂(lè)》、《何滿(mǎn)子》、《六胡州》、《如意娘》、《天長(zhǎng)久》、《秦王破陣樂(lè)》、《飲酒樂(lè)》、《圣明樂(lè)》、《武媚娘》、《弊契兒》、《韋卿堂堂》、《三臺(tái)》等名,敦煌P.3808樂(lè)譜中有《傾杯樂(lè)》、《西江月》、《心事子》、《伊州》、《水鼓子》等名。
(二)在部分唐傳古樂(lè)譜中,有不少樂(lè)曲是帶“換頭”的上下片結(jié)構(gòu),與曲子詞的體式相合。如P.3808譜中的《又慢曲子西江月》,譜中“重”字之前為上片,之后為下片。若把上下片的譜字都分成(1)和(2)兩部分,那么可以發(fā)現(xiàn),上下片(1)的譜字各不相同,而上下片(2)的譜字幾乎完全相同:
上片(1):一幾、てロス└て ケハクロ 七、てケて? ス幾ロスエ、一てミ一ロエ幾、てクハ
下片(1):└ヒ 七ロて七ヒ、- ク⊥ロエ、 -ミ幾、└ミロヒ七、てクハクロ七、てク√丁
上片(2):スロて、ヒ?guī)住ⅴ攻ā⒁互砥撺摇ⅴ撺尧?てロ七ヒ、幾ヒ 丿? 幾 斗 幾丿 重
下片(2):スロて、ヒ?guī)住ⅴ攻ā⒁互砥撺摇ⅴ撺移?てロ七ヒ、幾ロ丿丁 (幾└ヒ丿)…
這種譜字的異同很值得尋味。可以推測(cè),各片前半譜字的較大差異,即是所謂“換頭”。而出現(xiàn)在各片曲尾的譜字小異,則可以理解為以分解和弦作上片結(jié)聲與以和弦作下片結(jié)聲的區(qū)別。白居易《琵琶行》所謂“曲終收撥當(dāng)心劃,四弦一聲如裂帛”,正是對(duì)和弦(琵琶掃弦)的描寫(xiě)。至于劃線(xiàn)的部分,則可看作張炎《詞源》所云“前袞、中袞六字一拍,要停聲待拍,取氣輕巧;煞袞則三字一拍,蓋其曲將終也”的實(shí)例。因?yàn)樯掀腿幕九氖揭粯樱瑸榱鶄€(gè)譜字一拍(“ロ”為拍號(hào));下片則為三個(gè)譜字一拍(其中有兩個(gè)“ロ”號(hào))。也就是說(shuō),在《慢曲子西江月》曲將終時(shí),同樣的六個(gè)譜字,由上片的一拍變成下片的兩拍,是用漸慢的速度來(lái)唱奏的。這正是可歌之譜的表征。?
在唐傳古樂(lè)譜中,還有一個(gè)類(lèi)似的譜式,此即《五弦琵琶譜》中的《飲酒樂(lè)》。這支樂(lè)曲同樣有上下片,有“換頭”。而且,它上下片曲尾無(wú)變化,所有譜字在“換頭”之后完全相同,因而采用了省略記譜的方法(譜例一)。這一例進(jìn)一步說(shuō)明:上述兩譜是歌曲《西江月》、《飲酒樂(lè)》奏于琵琶的樂(lè)譜。換言之,我們的確可以在一定范圍內(nèi),討論唐傳古樂(lè)譜的音樂(lè)文學(xué)價(jià)值問(wèn)題。
譜例一:譜中“換頭”二字之前為歌曲的上片。“同”字前表示歌頭:譜字開(kāi)端至前一“同”字為上片的歌頭,“換頭”至后一“同”字為下片的歌頭。因下片歌頭之后的部分與上片旋律完全相同,故不再記譜。
最先注意到唐傳古樂(lè)譜的音樂(lè)文學(xué)價(jià)值的人仍然是任二北先生。他在《敦煌曲初探》中列出了同見(jiàn)于敦煌樂(lè)譜和敦煌曲子詞的樂(lè)曲,并對(duì)這些曲調(diào)的來(lái)源作了考證 (第455頁(yè))。后來(lái)林謙三在《天平、平安時(shí)代的音樂(lè)》一文[14]中,亦把敦煌曲子詞中的《西江月》、李賀《堂堂》詩(shī)同敦煌樂(lè)譜、《五弦琵琶譜》中的相關(guān)樂(lè)曲組合成可供演唱的聲詩(shī)歌曲。這種以同名的曲譜、詩(shī)歌組合成歌曲的做法,相當(dāng)于對(duì)古董文物的修復(fù),可使業(yè)已失傳的古代歌曲重新復(fù)活,是一件有意義的工作。故在林謙三之后,又有葉棟、趙曉生、唐樸林、陳應(yīng)時(shí)、關(guān)也維、席臻貫、莊永平、洛地、韋滿(mǎn)易等人嘗試了類(lèi)似的詞曲組合[15]。但由于各家譯譜和所取詞曲組合的原則不同,故結(jié)果大異。茲以“О”代表譜字、“|”代表原譜中的拍號(hào)“□”,把各家關(guān)于《又慢曲子西江月》上片詞曲關(guān)系的理解圖示如下:
??? 敦煌樂(lè)譜?? О О О| О О О? О О О| О О О? О О О| О О О О О
??? 林謙三???? 女 伴 同? 尋 煙 水,今 宵 江? 月 分 明。
??? 葉? 棟???? 云 散 金???? 波??????? 初 吐,煙 ???? 迷??? 沙? 諸????????? 沉
??? 趙曉生???? 女??? 伴? 同????????????? 尋? 煙 水,???????????? 今??? 宵
??? 唐樸林?????????? 女? 伴?????????? 同 尋? 煙 水,???????? 今???? 宵?????? 江
??? 陳應(yīng)時(shí)???? 女??? 伴? 同 尋 煙? 水,???????? 今 宵???? 江 月? 分??? 明。
??? 關(guān)也維???? 云??? 散??????? 金???? 波 初???? 吐,?? 煙??? 迷? 沙??? 諸
??? 席臻貫?????????????? 女??? 伴???? 同 尋 ?? 煙 水,?? 今 宵? 江??? 月 分
??? 莊永平???? 女 伴 同? 尋 煙 水,??????????????????? 今 宵 江? 月 分 明。
??? 洛? 地???? 春 風(fēng) 淡? 淡,? 落? 英 千 尺。晴 蜂 來(lái)? 往 平 郊,桃 杏 妙 香 飄
??? 韋滿(mǎn)易???? 月 映 長(zhǎng)? 江??????? 秋??????? 水,????? 分 明 冷? 進(jìn)?????? 星
??? 敦煌樂(lè)譜?? О| О О О О О? О |? О О О О О О| О О О? О О
??? 林謙三???????????????????????? 舵??? 頭 無(wú) 力 一 船 橫,?? 波 面? 微 風(fēng)
??? 葉? 棟???? 沉。?? 棹?????? 歌? 驚??? 起??? 亂??? 棲 禽,?? 女??????? 伴
??? 趙曉生???????? 江??? 月??? 分? 明。? 舵 頭??? 無(wú)??? 力? 一??? 船
??? 唐樸林???? 月???? 分?????? 明。舵??? 頭??? 無(wú)??? 力 一???? 船??????? 橫,
??? 陳應(yīng)時(shí)???????? 舵??? 頭 無(wú)???? 力?????? 一??? 船??? 橫,波??? 面? 微
??? 關(guān)也維???????? 沉??? 沉。????? 棹??? 歌 驚??? 起??? 亂? 棲??? 禽,
??? 席臻貫???? 明。舵??? 頭??? 無(wú)? 力,? 無(wú) 力??? 一 船 橫,波??? 面? 微
??? 莊永平???? 舵? 頭 無(wú) 力?????????????????????? 一 船 橫,????????? 波 面
??? 洛? 地???? 擲。畫(huà) 橋 煮 酒 青? 簾,有柳 外 數(shù) 聲 長(zhǎng) 笛。曾 記 去? 年
??? 韋滿(mǎn)易???????? 河。???? 淺 沙? 頂????????? 上 白??????? 云??? 多,雪 散
??? 敦煌樂(lè)譜?? О | О? О? О О О? О (|) О? О? О? 重 (О? О)
??? 林謙三???? 暗?????? 起。
??? 葉? 棟???? 各?????? 歸? 南??? 浦。
??? 趙曉生???? 橫, 波????? 面 微???? 風(fēng)???? 暗????? 起。
??? 唐樸林???? 波?????? 面? 微??????? 風(fēng)???????????? 暗????????? 起。
??? 陳應(yīng)時(shí)???? 風(fēng)?? 暗????? 起。
??? 關(guān)也維???? 女?? 伴????? 各??????? 歸???? 南????? 浦。
??? 席臻貫???? 風(fēng), 波????? 面 微 風(fēng)???????? 暗? 起。
??? 莊永平???? 微?? 風(fēng)? 暗? 起。
??? 洛? 地???? 時(shí), 紫? 陌? 朱 門(mén) 花? 下???? 舊? 相? 識(shí)。
??? 韋滿(mǎn)易???? 幾?? 叢???????? 蘆 葦。
由此可見(jiàn),中國(guó)音樂(lè)史專(zhuān)家的確努力進(jìn)行了詞曲組合的工作;關(guān)于他們“無(wú)暇顧及聲辭配合的研究”的說(shuō)法,并不符合事實(shí)。但利用唐傳古樂(lè)譜和現(xiàn)存同名詩(shī)詞作品來(lái)組合成符合歷史真相的歌曲,這仍然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所有對(duì)唐傳樂(lè)譜的詞曲組合,只能說(shuō)是一種試驗(yàn);可供試驗(yàn)的也只有《西江月》、《堂堂》等為數(shù)不多的幾支樂(lè)曲。在這種情況下,現(xiàn)存樂(lè)譜不可能用作進(jìn)一步推論的“切實(shí)的證據(jù)”。比如,“按這些已知的規(guī)則來(lái)判斷敦煌譜中其他已無(wú)存辭的曲子可配齊言還是雜言”,就是一件沒(méi)有道理的事情。因?yàn)槟切镀放贰ⅰ队致印贰ⅰ队智印贰ⅰ都鼻印贰ⅰ队旨鼻印访髅魇羌兤鳂?lè)譜;從它們的佚名特點(diǎn)看,很可能是西域傳入的樂(lè)曲。這些樂(lè)譜談不上配漢語(yǔ)辭的問(wèn)題。而《伊州》等曲在譜中不止一曲,很可能是大曲的不同選段。我們知道,大曲由器樂(lè)曲、歌曲、舞曲組合而成。唐大曲一般以器樂(lè)曲緩奏為“散序”,以節(jié)拍穩(wěn)定、伴有歌唱的部分為“中序”或“排遍”,中序之后有稱(chēng)作“破”或“急”的舞曲,此外有送曲。因此,這些選段不可能都是應(yīng)歌之曲。至于《長(zhǎng)沙女引》的“引”、《急胡相問(wèn)》的“急”,則表達(dá)了它們作為器樂(lè)引曲、作為急舞之曲的身份。此二曲是否可歌?亦是頗足懷疑的。
三、關(guān)于唐代曲子辭句讀與曲拍的對(duì)應(yīng)?
以上,我們討論了唐傳古樂(lè)譜的性質(zhì)及其配辭的可行性問(wèn)題。現(xiàn)在,我們擬進(jìn)一步討論唐代曲子辭句讀與曲拍的對(duì)應(yīng)規(guī)則。這一規(guī)則在《從古樂(lè)譜看樂(lè)調(diào)和曲辭的關(guān)系》(以下簡(jiǎn)稱(chēng)《關(guān)系》)一文中表述為曲拍和“半逗律”的對(duì)應(yīng),亦即樂(lè)譜拍號(hào)(“□”)和半逗詞組(五、七言詩(shī)句依中部小頓劃分的兩個(gè)單元)首字的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一文的核心,就是講這個(gè)規(guī)則。
在《隋唐五代燕樂(lè)雜言歌辭研究》、《唐代酒令藝術(shù)》二書(shū)中,王昆吾詳細(xì)討論過(guò)唐代曲拍。對(duì)節(jié)拍節(jié)奏的強(qiáng)調(diào),是唐代新音樂(lè)的特點(diǎn),也是曲子這種新興音樂(lè)體裁得以存在的重要條件。前者表現(xiàn)為“繁手淫聲”、“掩抑摧藏”、“繁音急節(jié)”、“鏗鏘鼓舞”一類(lèi)音樂(lè)風(fēng)格的流行,以西域鼓版類(lèi)樂(lè)器的大批輸入為物質(zhì)基礎(chǔ);后者表現(xiàn)為曲子歌舞對(duì)“拍”的講究,其條件是以拍板或鼓為曲子歌舞的必備樂(lè)器。盡管梁代傳譜《碣石調(diào)幽蘭》已用“拍之大息”作為樂(lè)章記號(hào),但“拍”之成為普遍行用的音樂(lè)術(shù)語(yǔ),卻畢竟是始于唐代的現(xiàn)象。《樂(lè)府雜錄》稱(chēng)拍板為“樂(lè)句”,《教坊記》以《十拍子》、《八拍子》、《八拍蠻》為曲名,劉禹錫因聲度詞“依《憶江南》曲拍為句”,杜牧詩(shī)云“問(wèn)拍擬新令”,說(shuō)明曲拍的確是度曲度辭的形式要素。
但值得注意的是,正因?yàn)閺?qiáng)調(diào)曲拍,故唐代音樂(lè)節(jié)拍既有規(guī)則明確的一面,又有變化多樣的一面。例如拍有緩急之分:樂(lè)譜、舞譜于“急曲子”、“急段”之外,有“慢曲子”、“慢段”;依拍子命名的曲子,于常調(diào)曲之外有“促拍”或“簇拍”之曲。拍又有用度之分:大曲各段拍數(shù)不同,散序無(wú)拍,歌與排遍緩拍,入破以后急拍。即就歌曲之拍而言,規(guī)則性也是和多樣性并存的。例如敦煌舞譜所載諸曲,均是唐代的流行歌曲,其曲拍制度亦用歌曲之制。其中一種制度是按譜字與節(jié)拍類(lèi)型的關(guān)系作樂(lè)曲分類(lèi),以“慢二、急三、一拍”為基本結(jié)構(gòu)的有《遐方遠(yuǎn)》、《南鄉(xiāng)子》、《驀山溪》等曲,以“慢二、急三、兩拍”為基本結(jié)構(gòu)的有《南歌子》、《鳳歸云》、《別仙子》等曲,以“慢四、急七”為基本結(jié)構(gòu)的有《雙燕子》曲。這說(shuō)明特定歌曲有特定的節(jié)拍規(guī)則。又一種制度是以《浣溪沙》、《浮圖子》、《五段子》作定式打送;所謂“打《浣溪沙》送”,即把許多歌曲按《浣溪沙》定式打?yàn)椤哀哀哀哀皘ООО|ОО|ООО|”(慢四、急三、慢二、急三)拍段。這說(shuō)明同一支旋律可以采用不同的節(jié)拍格式。另一些制度是使用變化方式擊拍,常見(jiàn)的變化有“打八拍心”(拍中有拍)、“三拍當(dāng)一拍”(規(guī)則性地改換節(jié)奏)和逐句“添拍”。這說(shuō)明歌曲的節(jié)拍節(jié)奏往往因表演需要而作有意識(shí)的改變,既有局部改變,也有結(jié)構(gòu)性的改變。[16]又如張炎《詞源》論拍眼,有“官拍”、“花拍”、“艷拍”、“均拍”、“打前拍”、“打后拍”等名稱(chēng),其基本特點(diǎn)是正拍之外有輔拍、規(guī)則拍之外有修飾拍。前面說(shuō)過(guò),敦煌樂(lè)譜所載《西江月》上下片結(jié)尾,正是《詞源》所云“前袞、中袞六字一拍,要停聲待拍,取氣輕巧,煞袞則三字一拍”的實(shí)例;而元稹《元和五年予官不了》詩(shī)所云“含詞待殘拍”,則與“停聲待拍”涵義相同。這意味著,《詞源》所記反映了唐代歌唱的面貌。同時(shí)也意味著,唐代不存在一個(gè)普適于諸多樂(lè)曲的曲拍-句讀對(duì)應(yīng)規(guī)則。《關(guān)系》所云“拍號(hào)既與曲辭句號(hào)相應(yīng),也與曲辭的逗對(duì)應(yīng)”,是得不到史料支持的。
唐代曲拍的變化性特點(diǎn),在其樂(lè)譜上也有明顯表現(xiàn):敦煌樂(lè)譜雖有四字、六字、八字一大拍的規(guī)律,但大拍中的譜字常常臨時(shí)增減。《關(guān)系》說(shuō):“譜字?jǐn)?shù)的臨時(shí)增減畢竟是少數(shù)。”其實(shí)不然。敦煌樂(lè)譜載25曲,除第一、第二曲無(wú)拍號(hào)外,其余23譜都有在大拍中臨時(shí)增減譜字的情況。尤其在各首“曲將終”處的拍子中,常有上文《西江月》那樣的減字。在這種情況下,若依《關(guān)系》所定規(guī)則去處理樂(lè)譜,就會(huì)因削足適履而產(chǎn)生悖繆的辭樂(lè)關(guān)系。請(qǐng)看以下例證:
例一,《關(guān)系》一文為《慢曲子西江月》所配辭的兩處結(jié)句:
上片(2)? スロて、ヒ?guī)住ⅴ攻ā⒁互砥撺摇ⅴ撺尧?てロ 七ヒ、幾ヒ丿? 幾斗 幾丿 重
(舵)頭????? 無(wú)??? 力??? 一? 船?? 橫。? 波?? 面?? 微 風(fēng)暗 起。
下片(2)? スロて、ヒ?guī)住ⅴ攻ā⒁互砥撺摇ⅴ撺?七 てロ 七ヒ、幾ロ丿( 幾└ヒ丿)…
連????? 天??? 江浪 浸? 秋星,誤入??? 蓼?? 花叢? 里。
這是《又慢曲子西江月》“換頭”以后的部分。既然其上下片的譜字一致,那么,正如其它使用換頭的曲子詞一樣,其文辭格式也應(yīng)該是一致的。但為了牽合半逗句讀與拍號(hào)(譜中的“ロ”)的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打亂了本應(yīng)一致的辭式。
例二,《關(guān)系》一文為《慢曲子伊州》所配辭的兩處結(jié)句:
上片(2)? …… 丿ロ一幾、てミヒ、てロ七ヒ、幾ヒ丿 幾ロ斗、幾丿重
??????????????????? 歸? 雁??? 來(lái)時(shí)??? 數(shù)?????? 附???? 書(shū)。
下片(2)? …… 丿ロ一幾、てミヒ、てロ七一、幾ロ丁(幾└ 七丿)クロ丁
??????????????????? 歸? 雁?? 來(lái) 時(shí)??? 數(shù)? 附?? 書(shū)。
這里的問(wèn)題和上例一樣:《伊州》曲上下片譜字幾乎完全相同,但《關(guān)系》卻在基本相同的曲調(diào)之中(劃線(xiàn)部分)配置了不同格式的曲辭。其緣故也是因?yàn)樯掀摹爸行柫忠慌摹保谙缕鄳?yīng)部位變成了“煞袞則三字一拍”。《關(guān)系》的考慮是:若上片“數(shù)附書(shū)”三字按下片的方式配譜,則在“書(shū)”字之后會(huì)多出一個(gè)拍號(hào)和許多個(gè)無(wú)辭可配的譜字;若將下片三字按上片的方式配譜,則“數(shù)”“附”二字各占一個(gè)拍號(hào),而“書(shū)”字又要落在帶拍號(hào)的和弦(琵琶掃弦)之上。于是,為牽合拍號(hào)規(guī)則,它再次作了勉強(qiáng)的修改。可見(jiàn)所謂“曲拍和半逗的對(duì)應(yīng)”,并不是自然的法則,而是一個(gè)人為的法則。
例三,《關(guān)系》一文兩處配辭的對(duì)比:
《西江月》上片(2):て ロ 七 ヒ、幾 ヒ 丿 幾 ロ……
??????????????????????????? 波??? 面???? 微 風(fēng) 暗 起。
??? 《伊? 州》上片(2):て ロ 七 ヒ、幾 ヒ 丿 幾 ロ……
??????????????????????????? 數(shù)?????????? 附????? 書(shū)。
這是兩支樂(lè)譜的上片結(jié)尾部分。它們旋律相同,譜字相同,但《關(guān)系》卻配上了不同格式的文辭:《西江月》配六字句,兩個(gè)“半逗”;《伊州》配三字句,一個(gè)“半逗”。這種安排就不僅造成了音調(diào)的不自然,而且有違于《關(guān)系》自定的句讀與拍號(hào)相對(duì)應(yīng)的規(guī)則了。事實(shí)上,在《關(guān)系》為敦煌樂(lè)譜所配的兩篇歌辭中,這種違規(guī)的現(xiàn)象并不稀見(jiàn):?
《西江月》上片:女伴|同尋煙|水,今宵|江月分|明。舵頭|無(wú)力一|船橫,波|面微風(fēng)暗起。
《西江月》下片:撥棹|乘船無(wú)|定止,楚|詞處處聞|聲。連|天江浪浸|秋星,誤入蓼| 花叢里|。
《伊州》上片: 清風(fēng)|明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余。征|人去日殷|勤囑,歸|雁來(lái)時(shí)數(shù)|附書(shū)|。
《伊州》下片: 清風(fēng)|明月苦|相思,蕩|子從軍十|載余。征|人去日殷|勤囑,歸|雁來(lái)時(shí)數(shù)|附書(shū)|。
這里的曲辭關(guān)系有兩個(gè)明顯的矛盾:其一,它非但不合作者的“半逗律”(例如“波面微風(fēng)暗起”句間無(wú)頓逗),而且還造成了句讀上的破句(如“誤入蓼|花叢里”)。其二,按作者的解釋?zhuān)鞍攵骸敝傅氖钦Z(yǔ)氣上的小頓,但這里的拍號(hào)卻基本上不體現(xiàn)語(yǔ)氣停頓。這表明,所謂半逗規(guī)則在實(shí)踐中是難以實(shí)行的。
關(guān)于唐代曲子辭句讀與曲拍的對(duì)應(yīng),在目前,還是一個(gè)缺少資料、無(wú)法用歸納法來(lái)解決的問(wèn)題。正因?yàn)槿绱耍覀儜?yīng)當(dāng)像《關(guān)系》所說(shuō)的那樣注意樂(lè)理。但樂(lè)理是什么呢?不是樂(lè)譜符號(hào)的表面秩序,而是支配這些符號(hào)的、同演唱實(shí)踐相聯(lián)系的音樂(lè)邏輯。從這一角度看,《關(guān)系》的配辭方案同樂(lè)理是有隔閡的。因?yàn)樗此我院笤~譜的觀點(diǎn)看待敦煌樂(lè)譜,把演奏之譜看成了填詞之譜,把樂(lè)工之譜看成了詩(shī)家之譜。其中有三個(gè)問(wèn)題特別值得一提:
其一,既然敦煌樂(lè)譜不是填詞之譜,那么,就不能按一字一聲的觀點(diǎn)來(lái)看待它的譜字。也就是說(shuō),并非每一個(gè)譜字都可以配上歌詞,也不是每一個(gè)譜字都有必要付諸歌唱。上文說(shuō)到《西江月》下片曲尾以四弦一聲的琵琶掃弦作結(jié)聲,即是一證。這個(gè)掃弦由1 1 5 1四個(gè)音(或可看作1 5 1三個(gè)不同音高的音)組成,在四條弦上幾乎同時(shí)奏出。一個(gè)人是無(wú)法唱出同時(shí)發(fā)聲的幾個(gè)音的,故只能把它看作前一個(gè)音的延長(zhǎng)。同樣的道理,上片曲尾是琵琶掃弦的分解。它不是同時(shí)奏響的,而是先后奏出的1 5 1 1 2 1 1。這個(gè)分解了的掃弦,其作用也和下片的掃弦一樣,是對(duì)前一音的延長(zhǎng)。故后六個(gè)譜字是不必配詞歌唱的。然而,這個(gè)掃弦的分解譜字卻被《關(guān)系》配上了《西江月》的“微風(fēng)暗起”四字和《伊州》的“附書(shū)”二字:
1? 5? 1? 1? 2? 1? 1???????????? 1? 5? 1? 1? 2? 1? 1
微 風(fēng) 暗 起???????????????????? 附?????? 書(shū)
只要我們?cè)嚦幌拢椭肋@種安排違反了樂(lè)理。因?yàn)檫@里包含了幾個(gè)連續(xù)的五度、四度和八度大跳音程,即使勉強(qiáng)唱出來(lái),其效果也是非常別扭的。
其二,聲與辭的配合,不可簡(jiǎn)單理解為拍號(hào)與句逗的配合。存在于詞曲之間的邏輯,既包括詞和曲在段式、句式、拍式等方面的一致,也包括詞組語(yǔ)調(diào)和譜字音調(diào)之間的諧和。若不講這一道理,就會(huì)產(chǎn)生倒字現(xiàn)象。在《關(guān)系》所提供的兩首詞曲組合譜中,這種倒字現(xiàn)象是大量存在的。例如按研究者普遍采用的譜字音高,《關(guān)系》所配辭的唱法是:?
???????? 6? 3? 6? 6?? 7? 1? 3
???????? 江 月?? 分??????? 明?? (依旋律線(xiàn),“平入平平”唱成了“上平上平”)
???????? 6? 4? 5? 6? 5? 4
???????? 一 船? 橫??????????? (依旋律線(xiàn),“入平平”唱成了“上平去”)
???????? 6? 7? 6? 6? 1? 1
???????? 無(wú)??? 定 止?????????????? (依旋律線(xiàn),“平去上”唱成了“去平去”)?
???????? 6? 4? 5
???????? 浸 秋 星????????????? (依旋律線(xiàn),“去平平”唱成了“上平平”)?
???????? 2? 1? 7? 6? 6? 5? 1
???????? 十????? 載 余???????? (依旋律線(xiàn),“入上平”唱成了“平上去”)
顯而易見(jiàn),這些安排也有違于中國(guó)古代聲樂(lè)“字正腔圓”的原則。
其三,唐傳古樂(lè)譜中的拍號(hào)是一種節(jié)拍符號(hào)。它的功能和姜白石譜、《魏氏樂(lè)譜》中的“打號(hào)”、“拽號(hào)”并不相同。“打號(hào)”、“拽號(hào)”附加在譜字下方,有延長(zhǎng)譜字時(shí)值的作用,因此是一種節(jié)奏符號(hào)。但拍號(hào)相當(dāng)于現(xiàn)代樂(lè)譜中的小節(jié)線(xiàn)的拍子符號(hào)。它附于譜字右側(cè),與譜字時(shí)值的長(zhǎng)短無(wú)關(guān),主要功能是用于拍子和樂(lè)曲篇幅的計(jì)量。如張炎《詞源》所云“大曲《降黃龍花十六》當(dāng)用十六拍”,即指《降黃龍》摘遍“花十六”的長(zhǎng)度為當(dāng)時(shí)的十六拍,而非指其中有十六個(gè)句逗。這種拍號(hào)尤其不可看作文辭句讀的標(biāo)志。因?yàn)闃?lè)句有別于文句。文人作詞,以句逗區(qū)別字?jǐn)?shù)長(zhǎng)短;而樂(lè)工制譜,主要是行腔,不必依照文辭之句,亦不必循其協(xié)韻之處。故拍可稱(chēng)作“樂(lè)節(jié)”、“樂(lè)句”而不可稱(chēng)作“文句”。張炎《拍眼篇》說(shuō):“一均有一均之拍;若停聲待拍,方合樂(lè)曲之節(jié),名曰齊樂(lè),又曰樂(lè)句。”饒宗頤先生解釋說(shuō):這是指樂(lè)句要與樂(lè)配合。“樂(lè)工制譜,對(duì)于原詞是可以隨時(shí)加上裝飾音,和對(duì)于樂(lè)音自作伸縮處理的。因此,ロ符號(hào)所表示的是樂(lè)句而不是辭句。”[17]? 基于拍號(hào)的這種功能,關(guān)于唐代曲子辭句讀與曲拍的對(duì)應(yīng),只能理解為句讀與節(jié)奏安排相應(yīng),而不能理解為與拍號(hào)相應(yīng)。——倘若果真像《關(guān)系》所想象的那樣,拍號(hào)類(lèi)同于姜白石譜和《魏氏樂(lè)譜》中的“打號(hào)”和“拽號(hào)”,具備延長(zhǎng)音的節(jié)奏功能,那么,我們何必為所謂聲辭配合規(guī)則而辭費(fèi)?何不干脆把所有拍號(hào)都安排在“半逗詞組”的結(jié)束處呢??
四、結(jié)論
綜上所述:唐傳古樂(lè)譜研究是中國(guó)古譜學(xué)的一項(xiàng)重要內(nèi)容。由于敦煌樂(lè)譜的發(fā)現(xiàn),日本、英國(guó)、新西蘭、澳大利亞、德國(guó)、美國(guó)等地學(xué)者都參與了這項(xiàng)研究,使之成為國(guó)際漢學(xué)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一領(lǐng)域,中國(guó)學(xué)者工作的歷史最長(zhǎng)、參加的人數(shù)最多、涉及的古樂(lè)譜最豐富,提供了最多的譯譜方案和配辭方案,是最重要的一支研究力量。而西方學(xué)者的加入,則促進(jìn)了有關(guān)資料、方法與成果的交流。因此,《從古樂(lè)譜看樂(lè)調(diào)和曲辭的關(guān)系》一文對(duì)中國(guó)音樂(lè)史研究者的批評(píng)意見(jiàn)——關(guān)于他們“對(duì)于保存在日本的唐代樂(lè)譜所知甚少”,關(guān)于他們“不能將中日雙方所有的資料文獻(xiàn)融會(huì)貫通”,關(guān)于他們“無(wú)暇顧及聲辭配合的研究” ,違反基本事實(shí),不能成立。
樂(lè)譜在唐代的繁盛,是以西域音樂(lè)的傳入為背景的。西域樂(lè)工和他們所攜帶的樂(lè)器,是這場(chǎng)史稱(chēng)“胡樂(lè)入華”運(yùn)動(dòng)的主要載體。文化交流當(dāng)中的語(yǔ)言阻隔,則使大批西域歌曲轉(zhuǎn)變?yōu)槠鳂?lè)曲。這兩種情況,都造成了西域器樂(lè)曲在唐代的流行。從這一角度看,新樂(lè)譜和因聲度詞之法的產(chǎn)生都是必然的。它們事實(shí)上是對(duì)“胡夷里巷之曲”流傳條件的一種補(bǔ)充:后者彌補(bǔ)了西域樂(lè)曲中失落了的歌詞(沒(méi)有歌詞則不便廣泛流傳),前者則彌補(bǔ)了作為音樂(lè)記錄的歌詞的失落(沒(méi)有記錄則不便記憶與傳授)。正是考慮到音樂(lè)與文學(xué)之間這種發(fā)生學(xué)上的和功能上的共生關(guān)系, 任二北(半塘)先生從二十年代起就致力于對(duì)新發(fā)現(xiàn)的唐代音樂(lè)資料的研究,以解決詞的起源問(wèn)題和戲曲早期形態(tài)的問(wèn)題。在姜白石歌曲研究、敦煌樂(lè)譜研究以及唐代詞樂(lè)關(guān)系研究等方面,他都是導(dǎo)夫先路的人物,是資料和理論的奠基者。《關(guān)系》一文對(duì)他的批評(píng)意見(jiàn)——“由于古樂(lè)譜的解讀比較困難,始終未能深入到古樂(lè)譜內(nèi)部去探索樂(lè)調(diào)與歌辭相配合的原則”,夸大了這批具西域淵源的器樂(lè)譜在音樂(lè)文學(xué)研究上的價(jià)值,沒(méi)有什么實(shí)際意義。
在唐傳古樂(lè)譜的研究中,進(jìn)展最快的是敦煌樂(lè)譜研究。這是由資料條件決定的。從1937年到現(xiàn)在的60年間,研究者們討論了敦煌樂(lè)譜的結(jié)構(gòu)、體裁、譜式、定弦法、譜字和術(shù)語(yǔ),在這些問(wèn)題上取得較明確的結(jié)論。但敦煌樂(lè)譜的宮調(diào)系統(tǒng)問(wèn)題、節(jié)拍節(jié)奏問(wèn)題,卻因未知因素過(guò)多而未能解決。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產(chǎn)生一份具有充分說(shuō)服力的可靠的譯譜。研究者們于是轉(zhuǎn)而尋求其它方面的突破。其中一個(gè)突破發(fā)生在敦煌舞譜研究方面。王昆吾在《唐代酒令藝術(shù)》中,對(duì)舞譜的性質(zhì)、結(jié)構(gòu)原理、節(jié)拍規(guī)則、曲調(diào)來(lái)源、譜字內(nèi)涵及形成過(guò)程作了全面解釋?zhuān)讶〉靡环萦谶壿嫛⒂诂F(xiàn)存各方面資料均無(wú)窒礙的譯譜。另一個(gè)突破則是已故音樂(lè)學(xué)家黃翔鵬的曲調(diào)考證。他曾經(jīng)從五臺(tái)山青黃廟音樂(lè)中鉤稽出《憶江南》、《萬(wàn)年歡》等包含唐代遺存的音樂(lè)作品,從《碎金詞譜》中考訂出作為唐代遺音的《菩薩蠻》譜、《瑞鷓鴣》譜,從《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等文獻(xiàn)中發(fā)掘出宋代《念奴嬌》等曲調(diào)及其樂(lè)調(diào),提出了從民族音樂(lè)型態(tài)學(xué)角度去把握古曲發(fā)展規(guī)律的思路。[18]這一思路目前正由黃翔鵬生前組建的中國(guó)樂(lè)律學(xué)史課題組貫徹實(shí)行。這一群較年輕的學(xué)者,將在確定一定時(shí)代的黃鐘音高、調(diào)式形態(tài)的基礎(chǔ)上,利用現(xiàn)存的傳統(tǒng)音樂(lè)音響資料,考證古代的曲牌、宮調(diào)、譜字,最終建立音調(diào)與歷史的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他們的工作,為全面解決唐傳古樂(lè)譜釋讀問(wèn)題展示了光明而艱辛的研究前景。《關(guān)系》一文的作者可能尚不了解這些情況,所以提出了“不少論證仍停留在推測(cè)和駁論上”、“惜未舉出樂(lè)理證據(jù)”的批評(píng)意見(jiàn)。這種批評(píng),盡管也反映了作者的自我要求,但它只能產(chǎn)生欲速不達(dá)的效果。因?yàn)樗环蠈W(xué)術(shù)規(guī)律,也不符合多聞闕疑的原則。
六十年來(lái),唐傳古樂(lè)譜的研究過(guò)程,同時(shí)是它的學(xué)術(shù)意義不斷增長(zhǎng)的過(guò)程。從較為簡(jiǎn)單的古譜之間的比較研究,現(xiàn)已發(fā)展為音樂(lè)史學(xué)、音樂(lè)文學(xué)、樂(lè)律學(xué)、樂(lè)器學(xué)的綜合研究。而黃翔鵬的工作,則賦予它重視辨?zhèn)巍⒅匾暁v史結(jié)構(gòu)研究這兩項(xiàng)新的意義。所謂辨?zhèn)危傅氖且谘芯恐邪焉鐣?huì)變化造成的表演習(xí)慣的改變、術(shù)語(yǔ)名實(shí)關(guān)系的變化分辨出來(lái);所謂歷史結(jié)構(gòu)研究,則指研究字面符號(hào)之后的樂(lè)學(xué)形態(tài)以及其他深層內(nèi)涵。這使作為研究對(duì)象的唐傳樂(lè)譜的各種形式因素,都處在較為復(fù)雜的關(guān)系之中,亦即使唐傳古譜研究成為宏觀研究、微觀研究交叉關(guān)注的對(duì)象。在這種情況下,那種不顧及樂(lè)譜性質(zhì)、演奏技法、旋律進(jìn)行,僅依靠簡(jiǎn)單猜測(cè)而提出的配辭方案,事實(shí)上意味著一種倒退。《關(guān)系》為《西江月》、《伊州》所配的歌辭,之所以有上下片不一致、文句錯(cuò)亂、譜式同而辭式不同、倒字等不符音樂(lè)邏輯的現(xiàn)象以及自相矛盾的現(xiàn)象,正是由于它未顧及樂(lè)理。
從音樂(lè)文學(xué)研究的角度看,唐代音樂(lè)的節(jié)拍節(jié)奏,是最富于魅力的事物。中國(guó)音樂(lè)史由清樂(lè)時(shí)代進(jìn)入燕樂(lè)時(shí)代,曲子、大曲等新音樂(lè)體裁的產(chǎn)生,“近代曲辭”或曲子辭的出現(xiàn), 都有賴(lài)于新的節(jié)拍風(fēng)尚及節(jié)奏觀念的建立。其直接的物質(zhì)基礎(chǔ),則是大批來(lái)自西域的新節(jié)奏樂(lè)器。正如當(dāng)時(shí)音樂(lè)文化的空前豐富一樣,唐代的節(jié)拍節(jié)奏也是空前豐富的。《樂(lè)府雜錄》載唐玄宗命黃幡綽造拍板譜,幡綽說(shuō)“但有耳道則無(wú)失節(jié)奏”;又載宣宗自制《新傾杯樂(lè)》,“內(nèi)有數(shù)拍不均”;又載樂(lè)人用小豆偷記曲拍,或“以手畫(huà)帶記其節(jié)奏”:正表明了拍板節(jié)奏的富于變化,樂(lè)曲節(jié)拍的多樣性,以及以拍齊樂(lè)之不易。至于文辭與樂(lè)拍的配合,則更無(wú)現(xiàn)成的規(guī)則。元稹所謂“因聲以度詞,審調(diào)以節(jié)唱,句度短長(zhǎng)之?dāng)?shù),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zhǔn)度”,乃指詞曲之配合須考慮句度、聲韻等諸多因素,以音樂(lè)的聲調(diào)為其準(zhǔn)度,非指度詞僅依曲拍。
而根據(jù)張炎“停聲待拍”之說(shuō),字聲之起,亦未必在拍上。《關(guān)系》一文所創(chuàng)的曲拍與半逗詞組相對(duì)應(yīng)的規(guī)則,亦即定拍號(hào)在句首、句末及詞組第一字之上的規(guī)則,乃和這些記載相左。
此外,這個(gè)聲辭對(duì)應(yīng)規(guī)則是通過(guò)循環(huán)論證得出來(lái)的,以并不成立的配辭方案為依據(jù)。它既無(wú)資料支持,又不符唐代曲拍豐富多樣的面貌,顯而易見(jiàn)是站不住腳的。《關(guān)系》一文的所有論證,既然是建立在這一規(guī)則之上的,那么,這些論證同樣不能成立。
盡管如此,我們?nèi)匀徽J(rèn)為,《關(guān)系》是一篇有積極意義的文章。它重新強(qiáng)調(diào)了中日學(xué)者的交流與合作,主張結(jié)合樂(lè)譜進(jìn)行音樂(lè)文學(xué)研究,這些意見(jiàn),有利于打破學(xué)科之間的分割以及學(xué)術(shù)空間的分割。它所介紹的“半逗律”,亦可在漢語(yǔ)傳統(tǒng)中找到淵源。例如自荀子《成相歌》起,“三三七”便是民間歌謠的常見(jiàn)格式,說(shuō)明在七言中部有一個(gè)隱藏的“半逗”。而騷體詩(shī)句中的“兮”字,則明顯意味著語(yǔ)氣上的停頓。《后漢書(shū)》載有許多七言謠諺,如所謂“道德彬彬馮仲文”、“天下中庸有胡公”、“關(guān)西夫子楊伯起”,以腰韻的形式證實(shí)了半逗的存在。《宋書(shū)·樂(lè)志》所載魏鼓吹曲《舊邦》,流傳下來(lái)的格式是四、三、四、三式(如“舊邦蕭條,心傷悲;孤魂翩翩,當(dāng)何依”),說(shuō)明當(dāng)時(shí)人的習(xí)慣是把七言句斷為兩句。這種半逗律,自然會(huì)在唐代歌唱中有所表現(xiàn)。但它是否會(huì)成為關(guān)于聲辭配合方式的決定因素呢?這就有待于深入研究了。王運(yùn)熙先生曾經(jīng)證明:在漢魏六朝,一個(gè)七言句相當(dāng)于三、四、五言的兩句。[19]可見(jiàn)《關(guān)系》以五言為兩個(gè)半逗詞組的看法未必正確。從京劇和元明清三代戲曲曲藝的習(xí)慣看,七字句一般唱為“二、二、三”式,十字句一般唱為“三、三、四”式。可見(jiàn)對(duì)半逗律的歷史地位應(yīng)作謹(jǐn)慎的估計(jì),它并不是永恒的規(guī)律,在宋以后曾被“三逗律”代替。不過(guò),此文提出了半逗律概念,也就提出了吟誦節(jié)律與歌唱節(jié)律如何對(duì)應(yīng)的問(wèn)題,提出了漢語(yǔ)傳統(tǒng)同新音樂(lè)的關(guān)系的問(wèn)題。這是具有啟發(fā)意義的。除此之外,它還給了我們一個(gè)更大的啟發(fā),即:只有不割斷歷史,正視前人的成果,我們才能真正推動(dòng)學(xué)術(shù)前進(jìn)。因?yàn)橐坏┻M(jìn)入新的學(xué)科領(lǐng)域,這種正視,就是學(xué)術(shù)規(guī)范的最基本的保證。
注釋?zhuān)?/strong>
[1]《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1999年第1期。
[2] 日本《月刊樂(lè)譜》第27卷第1期(1938年)和《日本音響學(xué)會(huì)志》第2號(hào)(1940年)。前文有中譯本,載上海音樂(l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音樂(lè)藝術(shù)》1987年第2期;又載饒宗頤編《敦煌琵琶譜論文集》,臺(tái)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1年版1-35頁(yè)。
[3] 載日本《奈良學(xué)藝大學(xué)紀(jì)》1955年第5期。
[4] 林謙三:《雅樂(lè)──古樂(lè)譜的解讀》,日本音樂(lè)之友社1969年版。部分篇章有中譯本,載《中國(guó)音樂(lè)》1983年第3期、《交響》1987年第2期。
[5] 此書(shū)英文名為 Music from the Tong Court .第一卷由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第二卷起均由劍橋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現(xiàn)已出版六卷。
?
[6] 參見(jiàn)耐爾森:《五弦譜新考──五弦琵琶的柱制及其調(diào)弦法》,載日本《東洋音樂(lè)研究》第50號(hào)(1986年),中文摘譯本載《音樂(lè)藝術(shù)》1992年第1期;羅珂麗:敦煌樂(lè)曲二十五首譯譜,載《澳大利亞音樂(lè)學(xué)》(1997年)第20卷;峰雅彥:《<三五要錄>所記載的演奏樣式》,載《音樂(lè)藝術(shù)》1987年第4期;韋滿(mǎn)易:《敦煌琵琶譜<西江月>》,載歐洲中國(guó)音樂(lè)研究會(huì)機(jī)關(guān)刊物《磬》第7號(hào),中文摘譯本載《音樂(lè)藝術(shù)》1995年第2期。
[7] 載《音樂(lè)藝術(shù)》1982年1-2期。又葉棟:《唐代音樂(lè)與古譜解讀》,陜西省社會(huì)科學(xué)院出版發(fā)行室1985年版。
[8] 分別載《敦煌琵琶譜論文集》和《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1993年第5期。后文有日譯本,載《音樂(lè)之源──中國(guó)傳統(tǒng)音樂(lè)研究》,日本春秋社1996年版157-186頁(yè)。
[9] 載《古琴曲集》,音樂(lè)出版社1962年版1-24頁(yè)。
[10] 陳應(yīng)時(shí)的研究論文有:《琴曲<碣石調(diào)幽蘭>的音律》,載《中央音樂(l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1984[10] 陳應(yīng)時(shí)的研究論文有:《琴曲<碣石調(diào)幽蘭>的音律》,載《中央音樂(l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1984年第1期;《琴曲<碣石調(diào)幽蘭>的徽間音》,載《中央音樂(l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1986年第1期;《再談琴曲<碣石調(diào)幽蘭>的音律》,載《中央音樂(l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1999年第1期。吳文光打譜的《幽蘭》五線(xiàn)譜譯譜載《中國(guó)藝術(shù)研究院首屆研究生碩士學(xué)位論文集》(音樂(lè)卷),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1987年版。戴曉蓮和陳應(yīng)時(shí)合作打譜的《幽蘭》五線(xiàn)譜譯譜載《中國(guó)民族音樂(lè)大系古代卷》,上海音樂(lè)出版社1989年版。王德塤的研究論文有:《<碣石調(diào)幽蘭>卷子的抄寫(xiě)年代》,載《音樂(lè)藝術(shù)》1993年第1期;《百余年間 <幽蘭>古譜之研究述評(píng)》,載《貴州民族學(xué)院學(xué)報(bào)》1993年第1期;《六家<幽蘭>打譜中的“卻轉(zhuǎn)”與“轉(zhuǎn)指”》,載《星海音樂(l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1993年第1-2期合刊;《<碣石調(diào)幽蘭>抄卷的結(jié)構(gòu)研究》,載《星海音樂(l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1994年第3-4期合刊;《<碣石調(diào)幽蘭>文字譜編碼標(biāo)點(diǎn)校注本》,載《中國(guó)音樂(lè)學(xué)》1995年第1期;《<碣石調(diào)幽蘭>卷紙譜指法集注》,載《音樂(lè)學(xué)習(xí)與研究》1997年第1期。戴微的研究論文有《琴曲<碣石調(diào)幽蘭>譜研究》,載《今虞琴刊(續(xù))》1996年版。
[11] 參見(jiàn)何昌林:《天平琵琶譜之考、解、譯》,載《音樂(lè)研究》1983年第3期;《唐傳日本<五弦譜>之譯解研究》,《西安音樂(l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1983年第4期、1984年第1期連載。陳文成:《關(guān)于<泛龍舟>》,載《音樂(lè)研究》1984年第2期。葉棟:《敦煌壁畫(huà)的五弦琵琶及其唐樂(lè)》,載《音樂(lè)藝術(shù)》1994年1-2期;《唐代音樂(lè)與古譜解讀》,陜西省社會(huì)科學(xué)院出版發(fā)行室1985年版;《唐傳十三弦箏曲二十八首》,《交響》1987年1-2期。關(guān)也維:《五弦琴譜研究》,載《音樂(lè)研究》1992年第2期;《<仁智要錄>箏譜解譯》,載《音樂(lè)研究》1995年第5期。陳應(yīng)時(shí):《論唐傳樂(lè)譜中的節(jié)拍節(jié)奏》,載《民族音樂(lè)研究》第二輯,香港大學(xué)亞洲研究中心1990年版。
[12] 見(jiàn)岸邊成雄等:《唐代の樂(lè)器》,日本音樂(lè)之友社1967年版34頁(yè)。
[13] 參見(jiàn)王昆吾:《隋唐五代燕樂(lè)雜言歌辭研究》,中華書(shū)局1996年版47、154、287等頁(yè)。
[14] 此文系林謙三為日本哥倫比亞唱片公司同名獲獎(jiǎng)唱片所寫(xiě)的說(shuō)明書(shū)。此唱片錄制了林氏解譯的13首古樂(lè)譜。見(jiàn)林謙三著《雅樂(lè)──古樂(lè)譜的解讀》,49-123頁(yè)。
[15] 葉棟:《唐代音樂(lè)與古譜解讀》。趙曉生:《<敦煌唐人曲譜>節(jié)奏另解》,《音樂(lè)藝術(shù)》1987年第2期。唐樸林:《<敦煌琵琶曲譜>芻議》,《音樂(lè)藝術(shù)》1988年第1期。陳應(yīng)時(shí):《敦煌樂(lè)譜新解》,載《音樂(lè)藝術(shù)》1988年1-2期;又載饒宗頤編《敦煌琵琶譜》,臺(tái)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0年版。關(guān)也維:《敦煌古譜的猜想》,載《音樂(lè)研究》1989年第2期。席臻貫:《敦煌古樂(lè)》,敦煌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113-137頁(yè)。莊永平:《敦煌樂(lè)譜的詞曲組合》,《中國(guó)音樂(lè)學(xué)》1993年第1期。洛地:《敦煌樂(lè)譜<慢曲子西江月>節(jié)奏擬解》,《中國(guó)音樂(lè)學(xué)》1993年第2期。韋滿(mǎn)易見(jiàn)前頁(yè)注。
[16] 參見(jiàn)王昆吾:《唐代酒令藝術(shù)》第六章,知識(shí)出版社1995年版、東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
[17]饒宗頤:《三論□·及其涵義之演變》,載《敦煌琵琶譜》,臺(tái)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0年版。
[18]黃翔鵬:《逝者如斯夫——古曲鉤沉和曲調(diào)考證問(wèn)題》,載《文藝研究》1989年第4期;《兩宋胡夷里巷遺音初探》,載《中國(guó)文化》第四期(1991年);《念奴嬌樂(lè)調(diào)的名實(shí)之變》,載《音樂(lè)研究》1990年第1期。
[19]王運(yùn)熙:《七言詩(shī)形式的發(fā)展和完成》,載《復(fù)旦大學(xué)學(xué)報(bào)》1956年第2期;又載《樂(lè)府詩(shī)述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