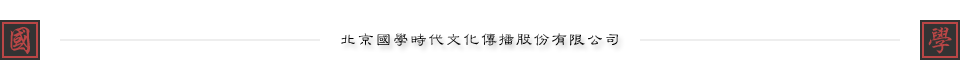禪宗北宗及其禪法
現在所說的禪宗,一般是指由慧能開創而在唐末以后成為禪宗主流的南宗禪。然而從禪宗發展歷史考察,在唐末以前曾有過南北二宗并行傳播的時期,而且至少在弘忍去世(公元674年)到“安史之亂”(755-763年)結束之前,北宗曾在以長安和洛陽東西兩京為中心的廣大北方地區十分盛行。唐開元二十年(732),慧能的弟子神會在靠近洛陽的滑臺(在今河南滑縣東)與北宗僧人辯論,宣稱南宗慧能曾從弘忍受祖傳袈裟,是禪門正統,禪法主頓;北宗沒有祖傳袈裟,“師承是傍,法門是漸”(宗密《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竭力為南宗在北方傳播開辟地盤。由于神會的努力,南宗禪曾在洛陽一帶興盛過較短的時期。但畢竟北宗勢力過于強大,神會受到北宗勢力的誣陷被流放外地。直到“安史之亂”之后,由于神會主持戒壇度僧斂錢支援軍需有功,受到朝廷的支持,南宗的正統地位逐漸得到朝廷的確認。此后南宗才發展成為禪宗的主流派,北宗逐漸衰微。
在本世紀從敦煌文書中發現大量早期禪宗文獻之前,人們對北宗的歷史和禪法所知甚少。在發現敦煌禪籍后的六、七十年以來,由于國內外學者的相繼研究,豐富了早期禪宗的歷史,為人們了解北宗以及南北二宗的分歧和爭論提供了比較可靠的文獻資料。
本文參考傳統佛教史書、碑文和敦煌禪籍對北宗主要代表人物以及北宗禪法進行介紹。
一、曾為“兩京法主,三帝門師”的神秀及其弟子普寂
在弘忍的弟子中,以神秀、法如、慧安和慧能最為有名。其中作為北宗代表人物的是神秀及其弟子普寂、義福。他們由于受到朝廷的崇信,使北宗禪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盛行于以東西兩京為中心的廣大北方地區。
由于他們在佛教界擁有顯赫的地位,死后都有當時的著名儒者為他們撰寫碑文傳記:黃門侍郎張說(玄宗時任中書令)為神秀撰寫《唐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載《全唐文》卷二三一),曾任戶部員外郎和括州、淄州、滑州三州剌史的李邕為普寂撰寫《大照禪師塔銘》(載《全唐文》卷二六二),先后任尚書左丞和洛州剌史的嚴挺之為義福撰寫《大智禪師碑銘》(載《全唐文》卷二八○)。此外,在敦煌禪籍《傳法寶紀》之中載有神秀的傳,在《楞伽師資記》和《舊唐書》卷一九一的〈方伎傳〉中載有他們三人的傳。《宋高僧傳》的卷八和卷九分別載有神秀和普寂、義福的傳(注1)。
(一)神秀和東山法門
神秀(?-706),俗姓李,陳留尉氏縣(在今河南省)人。童年出家,對老莊、《尚書》、《周易》以及其它經史和佛教的大小乘經論、戒律都有深入的研究。二十歲受具足戒,從此“銳志律儀,漸修守慧”(《傳法寶紀》)。
在神秀四十八歲時,聽說弘忍禪師在蘄州東山傳授達摩禪法,乃前往投師。見弘忍“以坐禪為務,乃嘆伏曰:此真吾師也”。(《宋高僧傳.神秀傳》)此后,一邊從事寺中的砍柴擔水等雜務,一邊從弘忍求道受法。如此度過六年。神秀因為在理解禪法要義和修行方面表現突出,受到弘忍的稱贊,據神秀的同門玄賾所著《楞伽人法志》記載,弘忍曾對玄賾表示,在他死后能夠傳授他的禪法者只有10人,其中神秀最為優秀,說:“我與神秀論《楞伽經》,玄理通快,必多利益。”是說神秀對于《楞伽經》是有深入的理解的。《宋高僧傳》的〈神秀傳〉載,弘忍曾對神秀贊譽說:“吾度人多矣,至于懸解圓照,無先汝者。”“懸解”意為從迷惑煩惱中擺脫出來,實指對禪理的深入領會;“圓照”是指通過禪觀體悟真如自性的修行。張說《大通禪師碑銘》載,弘忍曾贊嘆:“東山之法盡在秀矣。”道信、弘忍的東山禪法是繼承達摩以來重視《楞伽經》的傳統,把通過禪觀修行達到心識的轉變作為對修行者的基本要求。因為神秀在這方面有卓越的表現,故受到弘忍的贊許是可以理解的。
《傳法寶紀》記載,神秀曾一度還俗(原文:“后隨遷適,潛為白衣”),在荊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的天居寺隱居10年,不為世人所知。唐高宗儀鳳年間(676-679)經由荊楚高僧數十人舉薦,神秀正式得到朝廷允許受度出家,被派到當陽(在今湖北)的玉泉寺擔任住持。玉泉寺是隋天臺宗創始人智顗所開創的寺院,曾在此宣講《法華玄義》、《摩訶止觀》等著作。與神秀生活在同一個時代的弘景(因避宋太祖之父趙弘殷之諱,一般寫為恒景。634-712)在唐初曾跟道宣的弟子文綱學習戒律,后到此寺修持天臺止觀(詳見《宋高僧傳》卷五〈恒景傳〉)。可以認為,玉泉寺是有講習天臺宗教義傳統的寺院。神秀在此也可能習學天臺宗的教義,但他向弟子傳授的主要是“東山法門”。神秀的名聲日著,前來從他受法的人很多。《傳法寶紀》記載,在弘忍的另一位弟子法如去世之后,“學徒不遠萬里,歸我法壇,遂開善誘,隨機弘濟,天下志學,莫不望會”。
武則天在光宅元年(684)臨朝執政,5年后改國號為周,稱“神圣皇帝”,后稱“天冊金輪大圣皇帝”。她在篡唐為周的過程中曾利用佛教。《大云經》、《寶雨經》中的“女身”菩薩為王的記載,成為她決心登基當皇帝的重要依據。一些御用和尚曾迎合她的意向撰寫《大云經疏》,宣稱她是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為國主。武則天在稱帝后,特別尊崇佛教,改變以往把道教置于佛教之前的政策,“令釋教在道法之上,僧尼處道士女冠之前”(《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本紀〉)。她下令在各地建造大云寺,在洛陽城北造大佛像,召請各地名僧進京講經說法。當時受到她崇信的高僧有翻譯八十卷本《華嚴經》的于闐僧實叉難陀、有從印度求法而歸的義凈、有翻譯《寶雨經》的印度僧菩提流志,還有華嚴宗的正式創始人法藏、禪宗僧神秀、慧安等人。
久視元年(700)武后派使者迎請神秀入東都洛陽。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宋之問為隆重迎接神秀,特寫《為洛下諸僧請法事迎秀禪師表》上奏,贊美神秀“契無生至理,傳東山妙法,開室巖居,年過九十,形彩日茂,宏益愈深”;說兩京和各地的很多信眾都曾受到神秀的教示,在信徒中擁有很高的聲望;建議以“法事”迎神秀入城,“焚香以遵法王,散花而入道場”(《全唐文》卷二四0)。神秀被迎進洛陽之后,立即受到武后的崇高禮遇,張說《大通禪師碑銘》載:
趺坐覲君,肩輿上殿,屈萬乘而稽首,灑九重而宴居。傳圣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無臣禮,遂推為兩京法主,三帝國師。仰佛日之再中,慶優曇(按,優曇是一種花名,據說盛世方開)之一現。混處都邑,婉其秘旨。每帝王分坐,后妃臨席,鹓鷺(按,比喻排列有序的百官)四匝,龍象(按,喻稱高僧大德)三繞……
是說神秀見到武后時不必起立致禮,可以乘轎輿上殿,接受皇帝的禮拜,被安置在皇宮內部(內道場)居住。神秀被奉為東西兩京的“法主”,是武則天、中宗和睿宗三位皇帝的“國師”。他德高望重,佛法高妙,在朝廷受到的優遇無以復加,每當傳禪說法之際,帝王與之并坐,后妃臨席,周圍有大臣、高僧圍繞。武則天下詔在神秀曾住過的當陽玉泉寺建成度門寺,在他的故鄉尉氏縣故宅修建報恩寺。
張說以擅長文辭著稱,雖位居高官,但對神秀執弟子之禮。上引碑文難免有夸張之處,但基本是屬實的。這在其它史書也可得到證明。例如《傳法寶紀》說:神秀受到皇帝的禮敬供養,“授戒宮女,四會歸仰,有如父母焉。王公已下,歙然歸向”;《宋高僧傳·神秀傳》記述:則天太后召神秀入京,“肩輿上殿,親加跪禮。內道場豐其供施,時時問道……王公以下、京邑士庶,競至禮謁,望塵跪拜,日有萬計”。王臣貴族和一般平民百姓之所以對佛教,對被皇帝召請到京城的神秀等高僧表現出如此熾熱的崇拜感情,不僅是因為當時佛教信仰十分興盛,更重要的是由于則天武后和皇室對佛教的特殊崇信,造成了一種強大的能夠左右人們精神和輿論的社會氛圍。
在《楞伽師資記》的〈神秀傳〉中有一段記載對了解東山法門和神秀的禪法很有參考價值。曰:
大足元年,召入東都,隨駕往來,兩京教授,躬為帝師。則天大圣皇后問神秀禪師曰:所傳之法,誰家宗旨?答曰:稟蘄州東山法門。問:依何典誥?答曰:依《文殊說般若經》一行三昧。則天曰:若論修道,更不過東山法門。以秀是忍門人,便成口實也。
說明神秀是繼承道信和弘忍的禪法的。道信在其《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中明確地表示他的禪法一是依據《楞伽經》重視心性的法門,一是依據《文殊說般若經》的“一行三昧”的禪法。何謂一行三昧?南朝梁曼陀羅仙翻譯的《文殊說般若經》對這種禪法作了解釋,說修這種禪法是叫人在禪觀中從觀想一佛開始,到觀察法界的真如實相,最后達到對世界空寂和一切平等無有差別的認識。道信提倡的“守一”、“觀心”禪法,弘忍提倡的“守心”禪法都貫徹著這種思想。后面將要介紹的神秀的“觀心”禪法就是這種禪法--“東山法門”的發展。
唐中宗即位后,對神秀繼續崇信。神秀幾次提出回歸玉泉寺,都得不到允準。神龍二年(706)二月二十八日在洛陽的天宮寺去世。因為神秀從不講自己的年歲,故死時歲數不詳。《大通禪師碑銘》、《傳法寶紀》都估計神秀壽過百歲。然而《傳法寶紀》講神秀十三歲時因為“王世充擾亂”,河南、山東發生饑疫,便到滎陽義倉請糧。如果把此時僅限定在王世充稱帝之年,即唐武德二年(619),那么,神秀當生于隋大業二年(607)。前面所引宋之問《迎秀禪師表》說神秀“年過九十”應詔赴洛陽,此年是久視元年(700)。據此計算,神秀當生于隋大業七年(611)之前。這樣,我們可以推算神秀的生年或在公元607年,或至遲不會晚于611年。神秀死后,皇帝派人吊哀,賜謚“大通禪師”之號。歧王李范、張說、徵士盧鴻各撰碑銘。敕宣太子洗馬盧正權護送神秀遺體歸當陽玉泉寺,在度門寺置塔安葬。在葬送過程中,沿途士庶送葬者很多。睿宗時又賜錢三十萬對安葬神秀的寺塔進行擴建。
神秀的弟子當中著名的有普寂、義福、景賢等人。據《景德傳燈錄》卷四,神秀的弟子還有五臺山巨方、河中府中條山智封、兗州降魔藏、壽州道樹、淮南都梁山全植等16位禪師。
據《楞伽師資記》記載,神秀從弘忍“受得禪法,傳燈默照,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不出文記”。明確地說神秀沒有著作。可是,就在此書和《大通禪師碑銘》當中都對神秀所傳的禪法作了詳略不同的記述,說明在當時重視文史的社會環境中確實有人把他傳授的禪法作了一些記錄。現存的《觀心論》被認為就是由神秀的弟子或信徒對神秀的禪法所作的記述。
(二)普寂和北宗
據有關史料考察,雖然南北二宗的主要代表人物分別是神秀和慧能,但他們在世的時候,盡管在禪法主張上有分歧,卻沒有發生公開的激烈爭論。慧能在離開弘忍以后,直到上元三年(676)才正式出家受戒,此后到曹溪傳法,在先天二年(713)去世(注2)。現存《六祖壇經》中有慧能批評北宗禪法的話,但還不足于證明兩方已經發生分開論爭。《舊唐書》卷一九一和《宋高僧傳》的〈神秀傳〉所載神秀曾向武則天上奏請召慧能入京,并親自作書邀請,也許是有根據的。因為當時應詔入京的還有資州德純寺的智詵、安州壽山寺的玄賾、隨州大云寺的玄約、洛州嵩山會善寺的慧安等禪僧。他們都是弘忍的弟子。在慧能婉言推辭而未赴京的情況下,神秀再次奏請則天武后召慧能入京是可能的。
南北二宗發生分開的激烈論戰是在神秀、慧能二人先后去世之后。慧能的弟子神會北上,與北宗僧人進行爭論,最后受到北宗的迫害。當時正是北宗的首領普寂以禪門七祖自任,受到朝廷尊崇,聲勢顯赫的時候。因此可以把普寂和神會二人看作是南北二宗公開爭論時兩方的代表人物。
普寂(651-739),俗姓馮,遠祖居住長樂信都(在今河北冀縣),后世移居蒲州河東(在今山西蒲州鎮)。普寂年輕時曾習儒學,到大梁(今河南開封)、許昌一帶求學,博習《書經》、《周易》等和史籍,然而對此不滿足,決定出家探究佛教。后從大梁的壁上人學《法華經》、《唯識論》、《大乘起信論》等,又從東都端和尚受具足戒,跟南泉的景和尚學習戒律。后來前往嵩山少林寺尋訪法如禪師,但尚未到達,聽說法如已死。接著便改往當陽玉泉寺投奔神秀為師。他在神秀門下學習和修行七年,按神秀的吩咐讀過宣講般若空理的《思益梵天所問經》和宣述如來藏自性清凈心的《楞伽經》。神秀對他說:
此兩部經,禪學所宗要者。且道尚秘密,不應眩曜。
由此可以看出北宗是把這兩部經的思想作為自己禪法的重要理論依據的。
神秀在久視元年(700)應詔入東都,推薦普寂正式受度為僧。長安年間(701-704)普寂被派往嵩山南麓的嵩岳寺,在此修行和傳法,逐漸出名。神龍二年(706)神秀去世之后,唐中宗派考功員外郎武平一到嵩岳寺宣詔,在對神秀的德行作了稱贊之后,命普寂繼承神秀“統領徒眾”。其中有曰:“其弟子僧普寂,夙參梵侶,早法筵,得彼髻珠,獲茲心寶。但釋迦流通之分,終寄于阿難;禪師開示之門,爰資于普寂。宜令統領徒眾,宣揚教跡,俾夫聾俗咸悟法音。”(李邕《大照禪師塔銘》)在《宋高僧傳》的〈普寂傳〉中說:中宗“特下制,令普寂代本師統其法眾。”對于這里所說的命普寂“統領徒眾”、“代本師統其法眾”,只能理解為是繼承神秀統轄屬于神秀法系的僧眾,也就是北宗僧團。唐玄宗開元十三年(723),普寂應詔住入洛陽的敬愛寺。開元十五年(727)唐玄宗本西上長安,詔義福隨駕,而特命普寂“留都興唐寺安置”。自此,他以興唐寺為中心向僧俗信眾傳授禪法,引導學人通過“攝心”坐禪,“總明佛體”,“了清凈因”,擺脫煩惱達到覺悟。于是,聞者斯來,得者斯止。自南自北,若天若人,或宿將重臣,或賢王愛主,或地連金屋,或家蓄銅山,皆轂擊肩摩,陸聚水咽,花蓋拂日,玉帛盈庭……(《大照禪師碑銘》)
通過以上所述,普寂在當時地位之高,名聲之大,財勢之雄厚是可以想見的。
開元二十七年(739)七月對弟子明確誨示:
吾受托先師,傳茲密印,遠自達摩菩薩導于可,可進于璨,璨鐘于信,信傳于忍,忍授于大通,大通貽于吾,今七葉矣。尸波羅蜜(按,即戒)是汝之師,奢摩他(按,即止、禪定)門是汝依處。當真說實行,自證潛通。不染為解脫之因,無取為涅槃之會。”(《大照禪師碑銘》)
是向弟子宣述自達摩以來的傳法世系,自認為是繼菩提達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之后的第七世,以他為首的北宗當然是繼承達摩禪法的正統法系。又說應當重視持戒和修習禪定,做到斷除煩惱的“不染”和舍棄取舍意向的“無取”就能達到解脫。由此可以看到北宗禪法的一些特色。禪宗重視傳法世系,而最早提出禪法祖統說的正是北宗。此前,在法如(638-689)死后有人寫的《中岳沙門釋法如禪師行狀》已經提出從菩提達摩至弘忍-法如的傳法世系,然而是以法如作為繼承達摩禪法的第七世。普寂是神秀的嗣法弟子,自然要出來修改北宗內部已有的這種說法,把神秀作為直承弘忍的第六世,而自許為第七世傳人。由于普寂在當時所處的顯赫地位和在佛教界的巨大影響,這種說法在北方十分盛行。李邕《嵩岳寺碑》(《全唐文》卷二六三)和下面將要介紹的北宗史書《楞伽師資記》都是以神秀繼承弘忍,以普寂繼承神秀的。但是,以法如為第六世傳人的說法仍有影響,例如在比《楞伽師資記》稍后的北宗史書《傳法寶紀》中就是以法如為第七代祖的。
此年八月二十四日,普寂在興唐寺去世,享年八十九歲。河南尹裴寬是普寂的在家弟子,表奏上聞,詔謚普寂“大照禪師”之號,令歸葬嵩岳寺。普寂的弟子有惠空、勝緣等,其侄堅意曾任嵩岳寺寺主。唐密宗高僧、著名天文歷法學家一行(673-727)也曾從普寂受傳禪法。洛陽大福先寺僧道璇(702-760)曾從定賓學律,從普寂學禪法和華嚴宗教義,在開元二十三年(736)應日僧普照、榮睿之請在鑒真赴日之前東渡日本傳律學、華嚴宗和北宗禪法(日本師煉《元亨釋書》卷十六〈道璇傳〉)。獨孤及(725-777)《舒州山谷寺覺寂塔隋故鏡智禪師碑銘》(載《全唐文》卷三九0)說普寂有門徒萬人,“升堂者六十有三”,有弟子宏正,門人很多,“或化嵩洛,或之荊吳”,影響很大。(注3)
神秀的弟子還有義福(658-736)和景賢(660-723)、惠福(當即《景德傳燈錄》卷四所載的“京兆小福禪師”)。
以上普寂、義福、景賢、惠福是神秀弟子中最有名的四人。《楞伽師資記》在十分簡單地介紹了他們的事跡后,曰:“天下坐禪人嘆四個法師曰:法山凈,法海清,法鏡朗,法燈明。宴坐名山,澄神邃谷,德冥性海,行茂禪林。清凈無為,蕭然獨步。禪燈默照,學者皆證心也。”這是稱頌他們四人所傳的禪法如同山海那樣高深,那樣清凈,如同鏡、燈那樣明亮;他們在名山深谷安心修行,通過禪觀領悟自性,達到清凈無為境地;遠近學者從他們受法,致力自悟心性以達到解脫。
二、北宗的“觀心”、“看凈”的禪法
以神秀、普寂為代表的北宗,繼承從達摩以來的強調通過坐禪達到心識轉變的禪法,特別直接繼承和發展道信的“守一”、“看心”禪法以及弘忍的“守心”的禪法,提出比較系統的以“觀心”、“看凈”為主旨的禪法。
在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從敦煌遺書中發現大量早期禪宗文獻以前,流傳于社會上的禪宗典籍對北宗禪法僅有個別的零散的介紹。隨著國內外學者對敦煌禪籍的深入調查和研究,從中發現不少屬于北宗的史書和傳授禪法的語錄。其中的《觀心論》、《大乘五方便》等文獻,被認為是記述北宗禪法的著作。
(一)神秀、普寂和北宗禪法
從達摩到弘忍都根據大乘佛教佛性論的觀點,認為人生來就具有與佛一樣的本性,稱之為佛性或自性、本心等,它本來是純潔清凈的,只是由于受到情欲惡念的染污才失去它本來的光澤,如果通過專心坐禪修行在內心徹底斷除情欲雜念,就可使清凈本性顯現,達到覺悟解脫。神秀及其弟子普寂等人仍然是按照這種思惟模式提出自己的禪法主張的。
關于神秀、普寂的禪法,在《觀心論》、《大乘五方便》以外的禪宗文獻中也有概要的記載。《楞伽師資記》的〈神秀傳〉記載,神秀生前把自己的禪法歸結為“體用”二字,稱之為“重玄門”、“轉法輪”;引證《涅槃經》中的“善解一字,名曰律師”(出自南本《大涅槃經》卷三〈金剛身品〉,文字有異),說“文出經中,證在心內”;問:“此心有心不,心是何心?”又云:“見色有色不,色是何色?”這里的“體”可解釋為“心”、“真如”、“實相”、“佛性”,“用”則是心的作用,也指真如佛性顯現的萬象,教人借觀想“體用”、“心色”等來體悟心、佛性是萬有之本、之源。張說《大通禪師碑銘》說:
其開法大略,則專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其入也,品均凡圣;其到也,行無前后。趣定之前,萬緣盡閉;發慧之后,一切皆如。特奉《楞伽》,遞為心要。(注4)
是說神秀以《楞伽經》的思想作為禪法的要旨,主張通過坐禪“息想”、“攝心”,摒棄一切情欲和對世界萬象所持的生滅、有無、凡圣、前后等差別觀念,達到與“實相”或“真如”相契合的精神境界。唐本《六祖壇經》所載神秀呈給弘忍的表述自己禪法見解的偈頌是: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注5)
意為眾生皆有達到覺悟(菩提)的素質,先天所秉有的佛性之心如同明鏡一般潔凈,應當勤加修行,不要使它受到情欲煩惱的污染。張說所寫《大通禪師碑銘》最后的銘文中也用“心鏡外塵,匪磨莫照”的句子來稱誦神秀的禪法。
普寂在禪法上繼承神秀。在他最初到玉泉寺投師神秀時,神秀讓他閱讀《思益梵天所問經》(后秦鳩摩羅什譯)和《楞伽經》,說:“此兩部經,禪學所宗要者。”(李邕《大照禪師碑銘》)《思益經》著重講般若的空和中道的思想,《楞伽經》講清凈心性和心識的轉變的問題。普寂長期在洛陽的興唐寺向僧俗弟子傳授禪法,據《大照禪師碑銘》的記載,其禪法要旨是:
其始也,攝心一處,息慮萬緣。或剎那便通,或歲月漸證。總明佛體,曾是聞傳,直指法身,自然獲念。滴水滿器,履霜堅冰。故能開方便門,示直寶相;入深固藏,了清凈因。耳目無根,聲色亡境,三空圓啟,二深洞明。
大意是說,通過集中精神坐禪,斷絕對世界萬有的思念,或在極短時間,或用很長時間,便可進入覺悟的境界。修行者首先要對作為自身覺悟的內在依據的佛性,所追求的最高目標--佛身有所了解,然后向著成佛的目標努力修行,便可自然而然地使愿望得到實現。如同滴水不斷可使器滿,履霜過后隆冬將至那樣,這是個漸進的過程。修習禪定,引發智慧,此為“開方便門”;由此體悟自身本具佛性(或稱如來藏),是覺悟之因;認識諸法性空,心、色(包括耳目、聲色等)俱空,從而達到空、無相、無愿(斷絕欲望意念)的三解脫門境界,洞達人、法“二無我”之深理。
慧能離開弘忍后到南方傳法,開創南宗。他的弟子神會為擴大南宗的影響,到河洛一帶地方傳法,批評北宗所傳禪法是引導人們漸悟的“漸教”,說北宗神秀、普寂的禪法要領是:“凝心入定,住心看凈,起心外照,攝心內證。”(唐獨孤沛《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注6)華嚴宗五祖宗密對華嚴、禪并重,以上承神會自許,在他的禪學著作中對以神秀為代表的北宗禪也有不少的介紹。其《圓覺經大疏抄》卷三之下把北宗禪法的特點概括為“拂塵看凈”。在《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卷二說:“北宗意者,眾生本有覺性,如鏡有明性,煩惱覆之不見,如鏡有塵暗。若依師言教,息滅妄念,念盡則心性覺悟,無所不知,如磨拂昏塵,塵盡則鏡體明凈,無所不照。”他在《禪源諸銓集都序》中則把北宗歸到所謂“息妄修心宗”之內,說此宗主張的禪法是:“須依師言教,背境觀心,息滅妄念。念盡即覺悟,無所不知。如鏡昏塵,須勤拂拭,塵盡明現,即無所不照。又須明解,趣入禪境方便,遠離憒鬧,住閑靜處,調身調息,跏趺宴然,舌拄上顎,心住一境。”
據以上所述,神秀、普寂一系的北宗禪法的基本要點是:(1)重視坐禪,在禪定中“觀心”、“攝心”、“住心看凈”;(2)觀心、看凈是一個心性修行的過程,通過觀空和“息想”、“息滅妄念”(拂塵)等,深入認識自己本具清凈的佛性,并循序漸進地滅除一切情欲和世俗觀念,達到與空寂無為的真如佛性相應的覺悟境界。
敦煌本《觀心論》和《大乘五方便北宗》等早期禪宗文獻的發現,使我們能夠對上述北宗禪法有更集中更系統的了解。
(二)《觀心論》的禪法思想
在敦煌本《觀心論》發現以前,朝鮮和日本存在此論的不同本子。1570年朝鮮安心寺所刊印本題為《達摩大師觀心論》,1908年梵魚寺將此收入所刊《禪門撮要》之中,改題《觀心論》,后署“初祖達摩大師說”。日本的金澤文庫收藏有抄于13世紀鐮倉時代的本子,題為《達磨和尚觀心破相論》。日本《少室六門集》所收的此論稱《破相論》。在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從敦煌遺書中陸續發現此論的不少寫本,1930年矢吹慶輝在其《鳴沙余韻》中介紹了S2595號寫本,后來此校本被收入《大正藏》第85卷之中。此外還有S646、S5532、P2460、P2657、P4646以及由龍谷大學收藏的敦煌寫本(與《修心要論》在同一個抄本)。1932年日本學者神尾壹春在《宗教研究》新九卷五號發表《觀心論私考》,據所發現的異本和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百所載:“《觀心論》,大通神秀作”,論證此論是神秀著。此說逐漸得到日本佛教學術界越來越多的人的承認。鈴木大拙從1935年到1936年對上述敦煌寫本S2595號本、龍谷大學所藏敦煌本、金澤文庫本、朝鮮刊本、《少室六門》所收本,作了五本對校,并在《大谷學報》(15卷4號、16卷2號)以及《校刊少室逸書及解說》(安宅佛教文庫1936年出版)的附錄《達摩的禪法和思想及其他》論文后面發表,后來被收在《鈴木大拙全集》(別卷1)當中。但鈴木反對作者是神秀的說法,認為此論也是達摩口述,由弟子記錄的。(注7)
《楞伽師資記》明載神秀生前“不出文記”,那么《觀心論》有可能是他的作品嗎?正如史書說弘忍生前“不出文記”而有《修心要論》傳世一樣,神秀也許自己不從事寫作,但并不意味著他的弟子沒有機會把他傳授的禪法記載下來并整理成文書。通過后邊的論述不難看出,《觀心論》的思想與現存其他禪宗史書中所零散記載的神秀的禪法主張是一致的。可以認為,《觀心論》是神秀的弟子對神秀傳授的禪法所作的記錄整理而成的,說《觀心論》是神秀述是可信的。
下面主要依據鈴木大拙的《觀心論》五本對校本(以其中的朝鮮本為主),并參照有關神秀的史料對此論的思想進行介紹。
(1)認為“心者萬法之根本”,唯有“觀心”才是達到覺悟的捷徑
《觀心論》開頭載:
問曰:若有人志求佛道,當修何法,最為省要?師答曰:唯觀心一法,總攝諸行,最為省要。(注8)
所謂“觀心”,就是以心作為觀想內容的禪定。神秀認為“觀心”可以統括一切修行,是達到解脫的最簡便易行的方法。
那么,觀心為什么這樣重要呢?《觀心論》解釋說:“心者,萬法之根本也。一切諸法,唯心所生,若能了心,萬行俱備。”認為心既然是世界萬物的本源和依據,那么在禪定中觀想心,了悟心也可以達到一切修行的目的。如同樹根是枝條花果所依附的那樣,心也是人的一切行為的根本,“一切善惡,皆由于心”,甚至說“心是眾圣之源,心為萬惡之主。涅槃常樂,由自心生,三界輪回,亦從心起。心為出世之門戶,心是解脫之關津。”是說人的善惡行為是由自己的心決定的,那么最后是在三界的生死苦海中輪回,還是達到覺悟成佛,也完全是由自己的心決定。因此修行者應當著重內在的心識方面的修行,認為通過坐禪觀心,可以思索并了悟心對善惡、迷悟的決定作用,運用佛教的思想智慧,在心中斷惡修善,促成心識的轉變,最后達到解脫。
大乘佛教是從小乘佛教發展而來的,并且它本身也在不斷發展著。小乘比較重視人生問題,禪觀內容主要是以“四諦”(苦、集、滅、道)為中心,探求如何從生死苦惱中解脫出來的問題。大乘初期的般若類經典進而重視宇宙本體問題,以“諸法性空”、“諸法實相”為重要禪觀內容,論證在精神上超離“空幻”的現實世界而進入“真際”(真如、法身、第一義諦)彼岸境界的問題,但又通過對“中道”、“不二”的論述,宣說出世與入世是相即不二的,菩薩和佛具有在現實世界普度眾生的職責(所謂菩薩道、菩薩行)。稍后的大乘經典《華嚴經》、《大涅槃經》以及《《勝鬘經》、《楞伽經》等經典,開始重視心性問題,提倡在禪觀中以“心”(佛性、真如、如來藏、阿梨耶識、自性等)作為觀想的對境,探究心在宇宙、人生以及解脫中的地位和作用。南北朝末期編譯的《大乘起信論》(或認為是偽書)綜合大乘佛教思想,著重論證心性問題,認為“心”統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此“心”有兩個方面,稱其凈、不動的方面是“心真如門”,其染(污染,指情欲、煩惱、日常生活中的思維)的方面為“心生滅門”,二者又“非一非異”,而通過斷妄修真的止觀修行,斷除一切欲望“妄念”,做到“無念”,“得見心性”,就能達到覺悟。早期禪宗在接受大乘般若、中觀思想的同時,在論證覺悟解脫的場合尤其重視心性問題。這在《觀心論》中有突出的反映。
《觀心論》以不同的論證方式反復告訴人們,如果通過坐禪觀心而達到“了心”,即了悟心對人的行為的主宰作用和在解脫中的決定地位,就能使人正確修行,以迅速地達到解脫。作者在回答“云何觀心,稱之為了”時,講了如下一段話:
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了四大(按,地水火風)、五蘊(按,色受想行識)本空,無我;了見自心起用有二種差別。云何為二?一者凈心,二者染心。其凈心者,即是無漏(按,斷除煩惱的)真如之心;其染心者,即是有漏(按,有煩惱的)無明之心。此二種心,自然本來俱有。雖假緣和合,互不相生。凈心恒樂善因,染心常思惡業。若真如自覺,不受所染,則稱之為圣,遂能遠離諸苦,證涅槃樂。若隨染造惡,受其纏覆,則名之為凡,于是沉論三界,受種種苦。何以故?由彼染心,障真如體故。
開始講四大、五蘊本空的一段的大意是取自《般若心經》,后面講凈心、染心的部分主要是發揮《大乘起信論》中的關于“心真如門”、“心生滅門”的思想。是說如果按照菩薩那樣運用智慧深入思考時,就會認識世界萬物的空幻本質,并能對人的主觀精神和覺悟問題有所認識,即:人的精神有凈、染兩個方面,“凈心”就是沒被生死煩惱污染的“真如之心”,“染心”就是所謂被生死煩惱纏裹的“無明之心”,兩者并存,但互不相生。前者是引發人們修善,使人成菩薩或成佛,超脫生死煩惱的內在原因;后者把人先天具有的“真如之心”遮蓋,是使人受世俗情欲牽引造“惡”,輪回生死世界受種種苦的內因。在此后面還引用《十地經》、《大涅槃經》中講眾生皆有佛性,但被“五陰”、“無明”掩覆的一段話,說如果能“離其所覆”,即斷除無明之心,就能達到覺悟解脫。接著說:“故知一切諸善,以覺(按,此指真如佛性)為根,因其覺根,遂能顯現諸功德樹,涅槃之果,由此而成。如是觀心,可名為了。”可見,觀心的首要目的是“了心”,通過“了心”而引導修行者進行斷惡修善,達到覺悟解脫。
(2)通過“觀心”從內心滅除一切情欲和世俗觀念--“除三毒”和“凈六根”
《觀心論》脫離社會經濟、政治結構和環境來考察人生和內心世界問題,認為人們的精神中有一種先天的道德意識或覺悟基因,此即“真如之心”,亦即佛性,它是人們之所以能夠信奉佛教,能夠達到覺悟成佛的內在根據。同時又把人的生理本能和自然情欲稱為“無明之心”,認為是導致人生一切苦惱和罪惡的本源。又認為,凈、染二心雖然與生俱有,但前者是永恒存在的,只是被后者覆蓋著,而后者是可以通過修行而被滅除的。“觀心”這種禪定不僅是達到“了心”的認識過程,使人能夠思悟心的凈染、善惡、迷悟,而且也是一個斷惡修善,斷滅“無明”,使真如本性顯現,達到覺悟的“修心”過程。可以說,“修心”是屬于直觀內省的宗教道德的修養方式之一。
《觀心論》認為,“無明之心”雖然包括無限數量的“煩惱情欲”和所謂“眾惡”,但皆以貪、嗔、癡“三毒”為本源,而貪嗔癡又通過作為人的感覺與思惟功能的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表現出來。因為“六根”與外境接觸而產生“六識”,即形成感覺和認識,使人對外界有所貪戀追求,發生所謂“惡”的行為,形成種種煩惱,所以把“六根”乃至“六識”都稱為“六賊”。它說:
一切眾生,由此三毒及以六賊,惑亂身心,沉論生死,輪回六趣,受諸苦惱。猶如江河,因小泉源,涓流不絕,乃能彌漫,波濤萬里。若復有人,斷其根源,則眾流皆息。求解脫者,能轉三毒為三聚凈戒,能轉六賊為六波羅蜜,自然永斷一切諸苦。
按照佛教一般的說法,人生來就具有惡的本能,這就是貪、嗔、癡。所謂“貪”既包括普通的生理本能和欲望,也包括貪戀人生和追求物質享受與精神享受的心理趨向;“嗔”是指由于處在逆境和失利、所求落空的情況下產生的不滿或憤怒感情,由此會發生各種爭斗,犯下罪惡;“癡”也就是無明,指不明事理,實際特指不接受或違背佛教教義,稱貪、嗔皆因它而發。佛教認為眾生由此三個方面而導致不斷造惡,輪回生死,不能解脫,故把它們稱為“三毒”。又認為人的行為不外乎身、語、意三個方面,它們以人具有感覺和思維--六根與六識為前提,故把它們稱為“六賊”,謂它們能引導人們造罪,妨礙達到覺悟。《觀心論》所說的觀心過程便是以退治、斷除“三毒”和凈化六根、六識為主要內容。
引文所說的“三聚凈戒”是大乘的戒律,包括:攝律儀戒,指遵守各種戒律規定以防止發生惡的行為;攝善法戒,修善做功德;攝眾生戒,濟度眾生。所謂“六度”即“六波羅蜜”,包括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般若),是大乘佛教修行的主要內容,也被認為是從生死此岸到達涅槃彼岸的方法或途徑。應當指出的是,“三聚凈戒”和“六度”的原義不僅僅包括內在心理上的修行,也包括外在的傳教、行善和修行活動。但是,《觀心論》為強調“觀心”的重要,把它們一律解釋為制服情欲和世俗認識的心理活動。說:
三聚凈戒者,則制三毒心也。制一毒,成無量善聚。聚者,會也。以能制三毒,即有三無量善普會于心,名三聚凈戒。六波羅蜜者,即凈六根,胡名波羅蜜,漢言達彼岸。以六根清凈,不染世塵,即是出煩惱,便至彼岸也,故名六波羅蜜。
對于這樣一種不同于原義的解釋,有人提出質詢:三聚凈戒應是“誓斷一切惡,誓修一切善,誓度一切眾生”,而現在只說是“制三毒心”,豈不是曲解文義嗎?《觀心論》對此強加解釋,說修戒是針對“貪毒”的,此即為“誓斷一切惡”;修定是針對“嗔毒”的,此為“誓修一切善”;修慧是針對“癡毒”的,此為“誓度一切眾生”。這樣一來,便把佛教的戒、定、慧三學說成是直接對治貪嗔癡“三毒之心”的修心方法,又把它們等同于含義本來不同的大乘三聚凈戒了。根據這種解釋,在觀心過程中進行斷除“三毒”的心理活動也就等同于修持三聚凈戒和六度。《觀心論》又說:
以能制三毒,即諸惡消滅,故名之為斷;以能持三聚凈戒,即諸善具足,故名之為修;以能斷惡修善,則萬行成就,自他俱利,普濟群生,故名之為度。故知所修戒行,不離于心。若自心清凈,一切眾生皆悉清凈。故經云:心垢即眾生垢,心凈即眾生凈。又云:欲凈佛土,先凈其心,隨其心凈,則佛土凈。若能制得三種毒心,三聚凈戒自能成就。
這里所引的佛經是《維摩詰經》的〈弟子品〉和〈佛國品〉,強調修心凈心的重要性。這段文字是說,持戒修行都是不脫離內心的精神活動,而如果通過觀心、凈心達到“自心清凈”,就會使眾生清凈,以至使修行者理想中的“佛國”也清凈。從這里可見神秀北宗對觀心的重視程度。
佛教所說的“解脫”,一般是指從流轉“三界”生死輪回中解脫,成阿羅漢或成菩薩成佛。“三界”包括欲界、色界和無色界,除欲界的人、畜生之外,都是在現實的世界不存在的。“輪回”則是說根據眾生生前的善惡行為死后在所謂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這六道(或稱六趣,六種輪回趨向)中轉生。對此,《觀心論》從心性修養的角度進行解釋,說“三界”不在心之外,它們正是貪、嗔、癡“三毒之心”,由此三毒之心,而使人造惡,輪回六趣。因此說:
三界業報,唯心所生。若能了心,于三界中則出三界。
惡業由自心生,但能攝心,離諸邪惡,三界六趣輪回之苦,自然消滅。能盡諸苦,則名解脫。
但能攝心內照,覺觀常明,絕三毒心,永使消亡;閉六賊門,不令侵擾,自然恒沙功德、種種莊嚴、無量法門,一一成就。超凡證圣,目擊非遙。悟在須臾,何煩皓首?
在這里明確表示,通過“觀心”、“了心”、“攝心”就能在現世達到解脫。“悟在須臾,何煩皓首”,也就是即身成佛。縮短從現世到彼岸的距離,是禪宗內部普遍蘊育著的一種新的傾向,然而這種傾向在神秀及其弟子那里沒有得到發展,而在弘忍的另一個弟子慧能及其繼承者所主張的頓悟禪風上得到體現。
為了強調“觀心”對解脫的決定意義,在《觀心論》的不少段落把營造伽藍(寺),鑄造或繪制佛像,燒香散花,燃長明燈,繞塔行道,持齋禮拜等等,統統牽強地解釋為內心的修行活動。例如說:“言伽藍者,梵音,此言清凈處也。若永除三毒,常凈六根,身心湛然,內外清凈,是則伽藍也”;“塔者,身心也。常令覺慧巡繞身心,念念不停,名為繞塔”……這就是說,以往佛教所提倡的修寺造像,燒香禮拜等等功德事業是不必要的,《觀心論》斥之為“立相為功,廣費財寶,多傷水陸,妄營塔像……見有為則勤勤愛著,說無相即兀兀如迷,且貪世上之小樂,不覺當來之大苦。此之修學,徒自疲勞,背正歸邪,誑言獲福。”勸修行者不要執著這種“有為”的外在的功德事業,唯有坐下來“攝心內照”、“觀心”才有可能達到解脫。
(三)《大乘五方便》的禪法思想
《大乘五方便》,也稱《大乘無生方便門》,是唐代相當流行的北宗禪法著作,從敦煌遺書中發現很多寫本。主要卷子有:北京圖書館藏生24,倫敦大英博物館藏S735、S1002、S7961、S2503、S7961,巴黎國立圖書館藏P2058、P2270、P2836。在有的卷子上不止一個寫本,但各種寫本的內容存在很大差異,很難合校成一個完整的本子。其中的S2503上的寫本三、寫本二在1932年經日本學者校勘收入《大正藏》卷八十五,分別題為《大乘無生方便門》和《贊禪門詩》。日本久野芳隆1937年在《富于流動性的唐代禪宗典籍--敦煌出土的禪宗北宗的代表作品》(《宗教研究》新14-1)和1940年在《北宗禪--由敦煌本的發現而明了的神秀的思想》(《大正大學學報》30、31合輯)論文中對P2058、P2270上的幾個寫本作了介紹。此后,宇井伯壽對這三個卷子上的寫本重加校刊,分別用《大乘北宗論》、《大乘無生方便門》、《大乘五方便北宗》和《無題》的標題發表在他的《禪宗史研究》(巖波書店1939年出版)所附的〈北宗殘簡〉中。鈴木大拙對上述各本加以校訂,做成四本校刊本,發表在其《禪思想史研究第三》(《鈴木大拙全集》卷三,巖波書店1968年出版)。整理這四個本子所依據的寫本分別是:第一號本--S2503上的寫本二,第二號本--S2503上的寫本三,第三號本--P2058、P2270上的幾個殘本,第四號本--S2503上的寫本一。這為研究北宗禪法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1)所謂“方便通經”
宗密在其《圓覺經大疏抄》卷三之下把北宗神秀、普寂一系的禪法歸納為“拂塵看凈,方便通經”。
從現存的幾個寫本來看,《大乘五方便》的完本應當包括五個部分,在結構上與宗密在《圓覺經大疏抄》上的介紹是一致的。讓我們首先從整體上對《大乘五方便》的內容略作介紹。何謂“方便通經”?意為借助智慧巧妙地解釋經典,主要是通過對《大乘起信論》、《法華經》、《維摩經》、《思益經》、《華嚴經》五種佛經思想的解釋來論述北宗對覺悟解脫和禪法的主張。
第一是“總彰佛體”,依據《大乘起信論》,主要用所謂“離心離色”、“無念”的思想論證何為佛、覺,何為解脫的問題,引導修行者超脫來自物質世界(色)和精神世界(心),來自個人身心的一切執著束縛,體認心色俱空,舍棄所有的世俗觀念,取消一切好惡、取舍的意念,就能達到與空寂無為的真如相契合的境界,此即覺悟解脫。例如佛有三個含義,一是覺悟,二是使他人覺悟,三功德圓滿。此文則用“離心”、“離念”作解釋,說“離心名自覺,離色名覺他,心色俱離名覺滿”;“離心心如,離色色如,心色俱如,即是如來平等法身”(一號本之1)。
第二是“開智慧門”,依據《法華經》,主要是用“身心不動”和“從定發慧”等的思想論釋開發智慧,解釋《法華經》中的開、示、悟、入“佛知見”(注9)的問題。從實際內容看,是從另一個角度對前一部分思想的發揮。認為通過坐禪入定,使自己的感覺意識脫離對外境的接觸(六根不動),即“身心不動”,就可達到身心“離念”。說這樣在遭遇任何順逆、苦樂的條件時都不會產生是非、愛憎、取舍的感情和意向。例如說“心不動是定,是智,是理;耳根不動,是色,是事,是慧。此不動是從定發慧方便,開智慧門”(二號本之2);“不動為開,聞是示,領解是悟,無間修行是入,開示屬佛,悟入屬修道人”(三號本之2)。
第三是“顯不思議解脫”,依據《維摩經》,主張對一切事物,包括修行本身,不應當加以推測和帶有任何目的性,不要有意地追求什么和舍棄什么,亦即是“無念”。例如說:“以心不思,口不議,通一切法,從諸解脫,至入不二法門”(一號本之3);“瞥起心是縛,不起心是解”(《圓覺經大疏抄》卷三之下)。
第四是“明諸法正性”,引證《思益梵天所問經》的“諸法離自性,離欲際,是名正性”,說修行者擺脫主觀意識和情欲就可達到解脫,得到“諸法正性”。例如說:“心不思,心如;口不議,身如;身心如如,即是不思議如如解脫,解脫即是諸法正性”。據稱達摩和尚曾說:“心不起是離自性,識不生是離欲際,心識俱不起是諸法正性……如是意識滅,種種識不生。”(四號本之4)
第五是“了無異自然無礙解脫”(或簡稱“了無異門”),依據《華嚴經》,論證世界萬物相融無間的道理,人的感覺思惟功能(六根)與外界的一切(六境或六塵)相即不二,清凈與污染也相融無異。宣稱從六根入“正受”(禪定),于六境中起“三昧”(亦即禪定),意為根塵不二。又說:“眼是無障礙道,唯有知見獨存,光明遍照,無塵來染,是解脫道”;“一切法無異,成佛不成佛無異……永無染著,是無礙解脫道。”(三號本之5)
如同《觀心論》一樣,書中不少地方對佛經詞句的解釋是不完全符合原義的,如用離心離念來解釋佛乃至三身佛,用心色不動解釋智慧和“開佛知見”,以及說“智慧是大乘經”,《法華經》、《華嚴經》、《金剛經》等都是“智慧經”等等。這些解釋都是發揮佛經詞義的一部分的含義,目的是為了強調看凈觀空、身心離念禪法對覺悟解脫的決定意義。所謂佛教中國化,其中一個方面就是中國僧人為了適應不同場合的需要對佛經原義作“方便”靈活的解釋,并提出新的主張。在這方面,禪宗僧人的表現尤為突出。
(2)從看凈觀空到“心色俱離”、“身心不動”
在《大乘五方便》中始終貫徹著離色離心和身心不動的思想。何謂離色離心?就是通過坐禪封閉自己的感官和意識,脫離對物質、精神兩方面一切事物和現象的追求、執著,斷除心靈深處的各種是非、美丑、愛憎、取舍等觀念。何謂身心不動?坐禪入定是“不動”;自己的感官和意識(六根、六識)雖接觸外界(六塵),但不發生感覺,不進行思惟(“不起”),不作分別判斷(“離念”),是身心“不動”。書中說,如能達到這樣的境界就得到最高的智慧,就達到覺悟解脫。
那么,如何坐禪,如何達到這種境界呢?
在《大乘五方便》的開頭部分有一段記述引導修行者進入坐禪程序的文字,大意是:禪堂的和尚(簡稱“和”,當是后來被稱為“方丈”或“堂頭和尚”者)命修行禪僧首先下跪合掌,發“四弘誓愿”,然后請十方三世諸佛菩薩,教受三歸依、問答五項能與不能(當即授三聚凈戒),各自懺悔。然后這位和尚對禪僧說:
汝等懺悔竟,三業清凈如凈琉璃,內外明徹,堪受凈戒。菩薩戒,是持心戒,以佛性為戒性。心瞥起,即違佛性,是破菩薩戒;護持心不起,即順佛性,是持菩薩戒。(原文有注:“三說”)
接著,他命禪僧各自“結跏趺坐”,即坐禪。
所謂“菩薩戒”就是大乘戒。在大乘戒中漢地最流行的是《梵網經》,規定有十重戒和四十八輕戒,其卷下的經文上講大乘梵網戒源于盧舍那(報身佛)之心,與所謂佛性等同,是佛菩薩的本源;眾生的身心皆有佛性,也先天秉有此戒,即“佛性戒”;既然十重戒等源自佛身,又與佛性無別,當然是“本源自性清凈”。北宗主持坐禪的和尚在引導禪僧舉行三自歸依、受三聚凈戒、懺悔之后,向眾僧說他們已經“三業清凈”,可以受“凈戒”了。凈戒即“菩薩戒”(即大乘戒),說它是“佛性戒”,“以佛性為戒性”。“戒性”,即相當道宣所說的“戒體”,指的戒律的本體依據,實際是特指受戒人通過受戒儀式在心中形成的對戒法的憶念、信心和持戒的意志。和尚告訴禪僧,要明白大乘戒是以佛性為戒體的,如果在修行中不能控制自己的心識活動(“心瞥起”),就是與空寂的佛性相違背,也就是違犯菩薩戒;相反,如果做到“心不起”,也就是“持菩薩戒”。這樣,便把坐禪觀心看凈與持戒結合在一起了。
《大乘五方便》在記述主持和尚命禪僧結跏趺坐之后,又用問答體記載這位和尚是如何指導禪僧坐禪觀心看凈的。從中可以看到:
(1)在大和尚主持之下,先要舉行發心,發四弘誓愿,禮佛,表示三歸依和攝受三聚凈戒,懺悔的儀式,然后由大和尚引導眾僧坐禪。
(2)禪僧入定觀空看凈,在想象中向四方上下仔細觀看,看到“虛空無一物”,體認一切皆為“虛妄”。
(3)禪僧應在持續不間斷的坐禪看凈的過程中“凈心地”,使心識做到“湛然不動”,最后身心(六根)清凈,達到與真如(‘如’)相契的解脫境界,此即“一念凈心,頓超佛地”。
因為真如佛性的本體為空,是本來清凈無染的,故觀空看凈也就是觀想體認真如佛性的過程,是顯現清凈自性的過程。在《大乘五方便》(四號本)的結尾部分說成佛的根據是“凈心體”,此“凈心體”即是“覺性”(佛性),它猶如“明鏡”,“雖現萬象,不曾染著”。要體悟此“凈心體”而解脫,就應學習坐禪(“使心方便”),“透看十方界,乃至無染,即是菩提路”。
禪宗所謂的“頓教”、“漸教”的重要差別是在于能否靈活運用大乘中觀學說的“相即不二”和《華嚴經》的世界萬有圓融無礙的理論上。就是說,對于空與有,身與心,內與外,染與凈,覺與悟,煩惱與菩提,眾生與佛等等相互對立的方面,能否順應時機巧妙地用相即不二的理論來將二者等同或會通,構成了頓教和漸教的主要區別。神秀、普寂的北宗禪法把身與心,外與內,染與染等等對立的兩方加以嚴格的區別,并以此作為前提,然后把心、內、凈等置于主導地位,提出觀心看凈的禪法,通過嚴格的不間斷的禪觀修行,斷除“三毒心”,凈“六根”,最后才達到解脫。這樣自然帶有“漸次”特色,即修行是按照前后、淺深程序進行的。后來南宗批評北宗的禪法“主漸”,是“漸教”,主要是根據這點。
最后應當指出,北宗的禪法著作《大乘五方便》中已經有某些接近頓教的說法,然而,從整體上看,這種帶有頓教色彩的思想在北宗沒有得到進一步的運用和發展。
注釋:
(1)《傳法寶紀》,據楊曾文編校《敦煌新本六祖壇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附編一所載本;《楞伽師資記》,據柳田圣山《初期的禪史Ⅰ》(日本筑摩書房1983年第三次印刷)的校本。神秀的傳,載《宋高僧傳》卷八,《大正藏》卷50第755-756頁;普寂、義福二人的傳,載《宋高僧傳》卷九,《大正藏》卷50第760頁。以下所引,不另加注。
(2)詳見楊曾文編校《敦煌新本六祖壇經》附編二《〈壇經〉敦博本的學術價值和關于〈壇經〉諸本演變、禪法思想的探討》三之(一)。
(3)《景德傳燈錄》卷四謂普寂有弟子24人,其中第一位惟政禪師的生卒年是公元755-841年,不可能是普寂弟子(普寂卒于739年),故不可信。日本宇井伯壽《禪宗史研究》(巖波書店1939年出版)第六章考證普寂有弟子23人,可以參考。
(4)張說《大通禪師碑銘》,現有不同版本。柳田圣山以《唐文粹》卷六四所收本為底本,校之以常盤大定《支那佛教史跡》第四輯所錄的柘本圖版以及《文苑英華》卷八五六、《張燕公集》卷一四、《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一四、《佛祖歷代通載》卷一二、《全唐文》卷二三一所收本,載在其《初期禪宗史書的研究》(日本法藏館1967年出版)后附之資料二。這里所引的是柳田的校本。
(5)楊曾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敦煌新本六祖壇經》。
(6)請見胡適校編,臺灣胡適紀念館1968年新版《唐神會和尚遺集》;楊曾文校編,中華書局1996年出版《神會和尚禪話錄》。
(7)請參楊曾文《日本學者對中國禪宗文獻的研究和整理》,載《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1期;日本田中良昭、沖本克己等譯編,中央公論社1989年出版《大乘佛教.11.敦煌Ⅱ》的〈解說〉。
(8)朝鮮本在“問曰”之前有“惠可”二字,在“答曰”之前有“師”字。其他各本皆無,今從之。
(9)《法華經》的〈方便品〉:“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于世。諸佛世尊欲令眾生開佛知見,使得清凈故,出現于世;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出現于世;欲令眾生悟佛知見故,出現于世;欲令眾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于世。”這里的“知見”,相當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