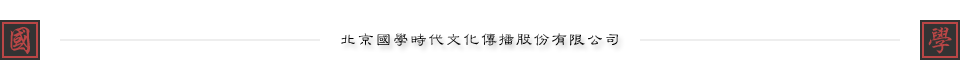鳩摩羅什和中國民族文化——紀(jì)念鳩摩羅什誕辰1650周年學(xué)術(shù)討論會召開
鳩摩羅什出生于龜茲(今新疆庫車、拜城一帶),是我國古代著名的佛教學(xué)者、佛教理論家、佛經(jīng)翻譯家。今年是他誕生1650周年的日子,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文化廳、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亞洲太平洋研究所、中國佛教協(xié)會佛教文化研究所、新疆佛教協(xié)會、新疆龜茲石窟研究所等7家單位聯(lián)名舉辦的紀(jì)念暨學(xué)術(shù)討論會,于1994年9月8日至9月12日在鳩摩羅什的故鄉(xiāng)新疆庫車克孜爾石窟召開,來自中國、日本、德國、韓國以及中國北京、甘肅、四川、陜西和臺灣等地的學(xué)者共140余人參加了會議。與會學(xué)者中有日本的著名學(xué)者鐮田茂雄、小島康譽社長,法國皮諾特教授,德國葛蓮女士,大陸學(xué)者有黃心川、賀世哲、楊曾文、吳震、薜宗正、陳世良、施萍亭、霍熙亮、萬庚育、彭蠡、霍旭初、賈應(yīng)逸、劉錫淦、艾買提江、伊斯拉菲爾和臺灣的釋惠敏等,還有一批學(xué)有專長的中青年學(xué)者和對羅什大師懷有崇敬心情的僧尼參加了會議。新疆文化廳和阿克蘇地區(qū)的行署領(lǐng)導(dǎo)買買提祖農(nóng)和王中俊廳長等出席了會議。中國國家文物局、中國佛教協(xié)會、日本創(chuàng)價協(xié)會名譽會長池田大作先生、敦煌研究院、中國哲學(xué)史學(xué)會任繼愈先生、中國宗教學(xué)會、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南亞中心、長安佛教研究中心、中國玄奘研究中心、中國南亞學(xué)會等發(fā)來賀信,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中央工藝美術(shù)學(xué)院、新疆畫院、新疆藝術(shù)學(xué)院、新疆書法協(xié)會、新加坡國會議員何永良先生等畫家和書法家向會議賀贈 了書畫作品。
本次會議的主題是“鳩摩羅什與中國民族文化”,大會共收到論文38篇,涉及到鳩摩羅什的生平、社會環(huán)境、中印佛教、佛典的翻譯和流傳、西域佛教的歷史與哲學(xué)、佛教洞窟和藝術(shù)等各個方面,有較高的學(xué)術(shù)價值。共有27名專家學(xué)者在會上宣讀了論文,代表們圍繞會議主題做了廣泛深入的探討,取得了一些共識。具體情況介紹如下:
一、鳩摩羅什對中國佛教的貢獻(xiàn) 有鐮田茂雄《東亞佛教與鳩摩羅什》、方立天《鳩摩羅什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地位》、楊曾文《鳩摩羅什譯經(jīng)與中國佛教》、韓金科、李發(fā)良《簡論鳩摩羅什譯經(jīng)活動對全國統(tǒng)一事業(yè)的重要貢獻(xiàn)》、鐘國發(fā)《鳩摩羅什譯經(jīng)與道教的演變》、彭蠡、楊季《君子惟借古以開今》、釋宏林、釋諦性《鳩摩羅什與長安草堂寺》7篇文章。代表們一致肯定鳩摩羅什對中國佛教的貢獻(xiàn)表現(xiàn)在開創(chuàng)中國譯經(jīng)史上新紀(jì)元、培養(yǎng)了一批杰出的佛學(xué)家、促進(jìn)了大乘佛教在中國的全面弘傳、影響了中國佛教學(xué)術(shù)思想發(fā)展的道路、推動了佛教某些學(xué)派和宗派的創(chuàng)立與演變。有的學(xué)者甚至認(rèn)為,由于鳩摩羅什的佛教活動,使全國的佛教界在經(jīng)典的使用上逐漸統(tǒng)一,于是促進(jìn)了佛教界的南北交流,增強了各民族的認(rèn)同,也就間接地對隋唐時期全國統(tǒng)一事業(yè)做出了貢獻(xiàn)。還有人說,鳩摩羅什對中國佛教的促進(jìn)作用,也給中國道教帶來了壓力和啟示,南北朝時出現(xiàn)的道教禮度改革和后出的道教重玄學(xué)說都與鳩摩羅什事業(yè)有間接聯(lián)系。日本學(xué)者談道,鳩摩羅什所譯的經(jīng)典先后傳入到朝鮮、日本等國,在日本知識分子里,認(rèn)為他的譯經(jīng)在古代譯師中最為準(zhǔn)確,因此特別推崇,撰寫贊文加以贊誦。在古代朝鮮和日本還流行著彌勒信仰,而這些都與鳩摩羅什譯的《法華經(jīng)》有重要關(guān)系,所以他對東亞佛教的發(fā)展有著重大的影響。
二、鳩摩羅什與佛經(jīng)翻譯 有譚世保《〈大智度論〉有關(guān)四十二字門解說之研究》、劉賓《鳩摩羅什的譯典在比較文學(xué)研究上的意義》、依斯拉菲爾.玉素甫《鳩摩羅什譯經(jīng)對回鶻佛教的影響》、日本落合俊典《傳到日本的與鳩摩羅什有關(guān)的典籍以七寺一切經(jīng)為中心》、吳震《吐魯番寫本所見鳩摩羅什漢譯佛教經(jīng)籍舉要》、楊富學(xué)《從出土文獻(xiàn)看〈法華經(jīng)〉在西域、敦煌的傳譯》、王欣《新疆博物館館藏吐魯番寫本〈妙法蓮華經(jīng)〉殘卷校勘》、張志哲《鳩摩羅什與佛經(jīng)翻譯》8篇文章。這些文章大部分是談的有關(guān)新疆出土的羅什譯經(jīng)寫本,因之很有特色。維吾爾族學(xué)者指出,從現(xiàn)有的資料來看,《法華經(jīng).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之回鶻文譯本共有4種(有人補充為9種),它們都是在吐魯番附近發(fā)現(xiàn)的。通過與漢文羅什譯本進(jìn)行對照,結(jié)果基本相同,只有個別的地方有出入。又以新疆現(xiàn)存的庫木吐拉石窟和柏孜克里克石窟的觀音畫像相映證,可以說明,觀音菩薩在回鶻人中所受的崇尚程度和《法華經(jīng)》在維吾爾思想史中的地位。漢族學(xué)者指出,據(jù)現(xiàn)存經(jīng)名題記或其內(nèi)容,結(jié)合相關(guān)文獻(xiàn)記載,判定屬于鳩摩羅什譯(含合譯)的吐魯番出土佛經(jīng)約數(shù)十件,以《法華經(jīng)》為最多,且這些抄件以麴氏高昌時期(499640年)為多,通過將這些寫本與《中華大藏經(jīng)》對勘,可以看出羅什的譯本很快就流入西域,而且是現(xiàn)存的較早抄本。有人認(rèn)為,在整個西域出土的梵漢文《法華經(jīng)》數(shù)量最多,其中漢譯羅什本寫卷約人1000余號,而在敦煌也有200余號羅什寫本出土,并且敦煌現(xiàn)存的60余幅《法華經(jīng)》經(jīng)變畫也是根據(jù)羅什本繪制的。在眾多的寫本中,法護譯的《正法華》與喀什本基本相同,羅什本則可能接近小國的寫本。還有人認(rèn)為,以往學(xué)者多限于《涅 》系統(tǒng)的五十字母等之音理次序,而對于《般若》系統(tǒng)的四十二字門等的排列“混亂”不理解以及誤解,因而羅什譯的《大智度論》中有關(guān)四十二字門的解說,有其獨特的寶貴價值。學(xué)者強調(diào),羅什的譯經(jīng)對中國文學(xué)的影響可從兩方面來看,從橫的角度看,他開辟了中國古代文學(xué)承先啟后的時代;從縱的角度看,他代表了古代史上中國文化同外國文化發(fā)生關(guān)系的第一階段,即在中印文學(xué)影響的形成、開端和傳遞中,扮演了極為重要和特殊的角色,因此他對后世文學(xué)的影響是顯著的,后出的中國文學(xué)的文學(xué)理論、詩歌創(chuàng)作體裁都明顯的表現(xiàn)出來。日本學(xué)者說,羅什的譯經(jīng)在天平七年(735)就已經(jīng)全部傳入,此外在日本還流傳有其它屬于羅什名下的作品,其中有的是托名而作,有的情況不明,也有的可能就是羅什本人之作,如名古屋七寺所藏的《馬鳴菩薩傳》在文體上與他寫的《龍樹菩薩傳》、《提婆菩薩傳》極為相似。
三、鳩摩羅什與西域佛教 有賈應(yīng)逸《鳩摩羅什譯經(jīng)與高昌北涼佛教》、郭平梁《鳩摩羅什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劉錫淦《鳩摩羅什與龜茲佛教》、買買提.木沙《古代龜茲著名的佛學(xué)大師鳩摩羅什》、劉元春《鳩摩羅什與西域佛教》、皮諾特《吐火羅語佛教詞匯的表述》5篇文章。代表指出,隋唐時代是龜茲佛教的鼎盛時代,而奠定基礎(chǔ)的就是羅什大師。就羅什本人而言,他從小乘改信大乘的思想變化,實質(zhì)上反映了一場社會變革,對西域的影響是巨大的。他所弘揚的大乘中觀思想,以積極和開放的心態(tài),沖擊了當(dāng)時在西域流行的保守、消極的說一切有部,促進(jìn)了社會文化的交流。羅什一生中在西域弘法43年,是為最得志的時期,所以即使在他離開之后,其對西域佛教的發(fā)展影響仍然存在。西域大乘佛教一直與漢文化有密切的聯(lián)系,羅什走后,中國大乘佛教開始對西域回流,影響越來越大。這在收集整理高昌北涼時期的有關(guān)佛教遺物,對其佛教進(jìn)行探討,也感到它與羅什所譯的經(jīng)典有密切的關(guān)系,例如,吐魯番地區(qū)出土的8件有題記可確定為北涼的佛經(jīng)寫經(jīng),其中有6件為羅什所譯的作品,近總數(shù)的80%,而且都是大乘經(jīng)典。又如在高昌出土的佛塔,上刻《佛說十二因緣經(jīng)》文,與有關(guān)的經(jīng)文對照,疑可能就是“闕”之羅什譯的《十二因緣經(jīng)》。在北涼時期的吐峪溝石窟壁畫中,其內(nèi)容也多是根據(jù)羅什的譯經(jīng)而繪制的。所以,該地盛行抄寫佛經(jīng),大乘經(jīng)典尤為流行,建寺造塔,塑像繪畫,坐禪修行也廣為傳播。這些都和羅什的影響分不開的。羅什的思想及弘法實踐,有利于當(dāng)時西域社會的開放和進(jìn)步,加強了西域與中國內(nèi)地的社會文化交流。法國學(xué)者認(rèn)為,現(xiàn)知的吐火羅語文獻(xiàn)絕大多數(shù)都是佛教文獻(xiàn)的翻譯或改編。于是出現(xiàn)了一些專門為表達(dá)佛教概念而創(chuàng)制的特殊詞句。這些不同的詞句在同一文獻(xiàn)中并存,
四、鳩摩羅什與佛學(xué)思想 有杜繼文《從紀(jì)念鳩摩羅什和玄奘想起的》、唐世民《鳩摩羅什的“畢竟空”哲學(xué)思想》、陳世良《鳩摩羅什從小乘到大乘思想的發(fā)展演變》、薜宗正《鳩摩羅什的彼岸思想歷程及其與此岸世界的溝通從說法龜茲到弘法長安》、釋惠敏《鳩摩羅什所傳“數(shù)息觀”禪法之剖析》、黃夏年《〈成實論〉二題》6篇文章。學(xué)者認(rèn)為,鳩摩羅什雖然著述甚少,而且又已散佚,但是就他現(xiàn)存的著述和弟子的記述,還是可以看出他的哲學(xué)思想。羅什的佛教哲學(xué)即是龍樹的佛教哲學(xué),他在翻譯龍樹的著作時,將自已的一套獨立的佛教哲學(xué)觀念頑強地表現(xiàn)出來。例如他的“畢竟空”思想,是從“實相”和“中道”說起的,在其《注維摩詰經(jīng)》中,作了權(quán)威性的解釋,畢竟空是一切都空,但又不是虛無。羅什將現(xiàn)實世界歸之于言語概念的世界,由此形成了以揭示邏輯矛盾為核心的思維方式,即消極否定的辨證法邏輯。但也有人說,“空”是“總破一切法”,是對中觀論的修正。有人又說,羅什實質(zhì)是以一位宗教改革者的姿態(tài)登上歷史舞臺的。他在青年時期后接受大乘思想,宣傳大乘學(xué)說,促進(jìn)了龜茲國王白純的政治改革。他在晚年又從單一的中觀思想,轉(zhuǎn)而強調(diào)“不應(yīng)執(zhí)著一經(jīng)”,帶有調(diào)合大小乘的思想了。但有人提出異議,認(rèn)為羅什到長安后其思想并沒有改變,而是更加成熟和進(jìn)一步發(fā)展。有學(xué)者考證,羅什的大乘思想適應(yīng)了封閉的綠洲地理環(huán)境和游牧民族國家需要一種統(tǒng)一思想的要求,因之他的大乘思想能夠得以在西域推廣,掀起了一個大乘運動,值得注意的是,羅什被擄走后,小乘有部學(xué)說很快再次流行開來,以后再也沒有發(fā)生大乘運動。反對者認(rèn)為,對西域的佛教應(yīng)做具體分析,和田是小乘地區(qū),龜茲是大小乘并舉,吐魯番是大乘地區(qū)。羅什曾經(jīng)在,內(nèi)地譯介了小乘論書《成實論》,學(xué)者從二個方面分析了此論的部分內(nèi)容,指出該《論》一是破有部的“法體實有”的主張,立自己的“無自性體”的思想;二是破有部的“五位七十五法”,主要破“心數(shù)法”,強調(diào)“心差別”的思想。因此它在認(rèn)識論上接近了大乘般若空思想,在心性論上繼續(xù)走小乘的路數(shù)。臺灣學(xué)者對鳩摩羅什的“數(shù)息觀”做了詳細(xì)的研究,認(rèn)為鳩摩羅什沒有加入當(dāng)時佛教界的出入息爭論之中,其所譯的《坐禪三昧經(jīng)》里,也沒有將修行方法與修行階位加以配合地說明,而且在經(jīng)中的引用的偈,不全部是馬嗚《美難陀》的說法,還有其它作品的影響。此外,該經(jīng)與《瑜伽師地論》也有不同的地方,前者內(nèi)容少于后者。
五、鳩摩羅什與佛教藝術(shù) 有施萍亭《敦煌與鳩摩羅什》、霍旭初《鳩摩羅什大乘思想的發(fā)展及其對龜茲石窟的影響》、朱英榮《鳩摩羅什少年時代的龜茲石窟》、張寶璽《〈法華經(jīng)〉的翻譯與釋迦多寶佛造像》、趙聲良《炳靈寺早期佛教藝術(shù)風(fēng)格》、史曉明《鳩摩羅什與中國早期佛教造像》、項一峰《鳩摩羅什與秦隴石窟藝術(shù)》、徐永明《鳩摩羅什與中國古代美術(shù)審美觀之演變》、胡雋秋《鳩摩羅什與藝術(shù)》、葛蓮《緊那羅鳥的演變》、日本中川原育子《克孜爾第76窟討論》11篇文章。鳩摩羅什與佛教藝術(shù)是否有直接的聯(lián)系,會上有兩種意見,一種認(rèn)為,他與佛教藝術(shù)有直接的聯(lián)系,例如,克孜爾石窟的內(nèi)容初期與禪修有關(guān),正與羅什少年習(xí)禪有關(guān),至羅什改宗大乘,龜茲石窟出現(xiàn)了規(guī)模宏大的大像窟。也有人認(rèn)為,龜茲石窟作為佛學(xué)思想的載體,造就了少年時代的鳩摩羅什,為小乘佛教在龜茲的流行制造了一種氛圍,而小乘佛教在龜茲的統(tǒng)治地位,以及少年鳩摩羅什在小乘佛學(xué)上的成就,又為龜茲石窟的形成與發(fā)展,決定了佛教義理擷取上所遵循的方向和佛教藝術(shù)規(guī)劃時所選擇的內(nèi)容。又如,4世紀(jì)鳩摩羅什父親帶到龜茲一尊 檀瑞像,使龜茲佛教造像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以后 檀瑞像又被羅什帶到內(nèi)地,造立像之風(fēng)盛行于中原。并且“代代相傳,朝野尊崇”,如果沒有羅什的作用,6世紀(jì)以前的中原佛教造像可能會出現(xiàn)另一種情況。另一種意見認(rèn)為鳩摩羅什與佛教藝術(shù)沒有直接的聯(lián)系,他對佛教藝術(shù)只有間接的影響。例如,他所譯的《法華經(jīng)》,因提倡“若人為佛故,建立諸形象,刻雕成佛像,可得無上道”,促進(jìn)了佛教藝術(shù)的發(fā)展,為雕像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豐富多變的素材。學(xué)者還提到,麥積山石窟的三世佛造像都與姚興接受了羅什的大乘思想有關(guān)。石窟中出現(xiàn)的大量“維摩詰經(jīng)變”和“西方凈土經(jīng)變”都與羅什的譯經(jīng)有關(guān)。炳靈寺石窟的造像也有這種情形,因此“鳩摩羅什是使印度佛教藝術(shù)華夏民族化的倡導(dǎo)者、支持者、傳弘者和貢獻(xiàn)者”。此外,對印度的造像風(fēng)格和克孜爾壁畫風(fēng)格向外傳播的問題也進(jìn)行了探討。
這次會議是繼1990年“西域佛教討論會”之后,在西北新疆地區(qū)召開的又一次學(xué)界盛會。也是中國佛學(xué)史上首次召開的鳩摩羅什的專題討論會。會議的特點是,①不同國家和各民族的學(xué)者和僧俗二界人士聚集一堂,尤其是維吾爾族的學(xué)者表現(xiàn)突出,提供了頗有見地的論文,外國學(xué)者和臺灣學(xué)者也表現(xiàn)不凡,發(fā)言很有特色。②學(xué)術(shù)氣氛濃厚,許多代表發(fā)言熱烈,爭論激烈,言不盡性;③論文涉及內(nèi)容廣泛,從佛學(xué)理論到佛經(jīng)校勘,從宗教、歷史到文學(xué)、藝術(shù),學(xué)科齊全。過去國內(nèi)召開佛教會議多是搞佛學(xué)和搞佛教藝術(shù)的脫節(jié),雙方很少坐到一起,這次則是真正地坐在一起,共同切磋,取長補短。會議開幕式上,舉行了鳩摩羅什銅像揭幕儀式。銅像通高4.15米,其中像高3.10米,座高1.05米,神態(tài)安詳,表情凝重,面部為印度和古代龜茲人的特征,展現(xiàn)了鳩摩羅什40歲的形像。其坐姿、衣著、臉部表情、束帛座等都以龜茲文物作為依據(jù),創(chuàng)作態(tài)度非常認(rèn)真。會議的具體組織者新疆龜茲石窟研究所為會議的如期召開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安排了良好的食宿。會后還組織代表參觀了克孜爾石窟、尕哈石窟、庫木吐拉石窟、蘇巴什古寺、森木塞姆石窟、伯孜克里克石窟、高昌古城、阿斯塔那古墓群、交河古城等重要的佛教遺址。代表們對西域的佛教有了更深刻地認(rèn)識,認(rèn)為這些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佛教遺址是研究西域社會、宗教、文化的窗口和基本線索,搞清楚這方面的情況就能更好地把握西域佛教的整體形態(tài),同時也有助于說明佛教傳入中國的情況,因此,有著重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