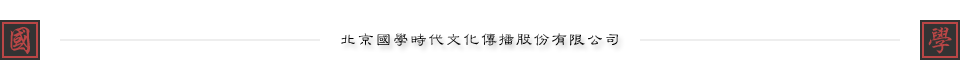建立慈氏學的人:訪韓鏡清教授
當前,我國的佛學研究十分繁榮,專著和論文不斷出版。但在眾多的學者中,有一位老專家卻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已經是87歲的高齡,并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仍然口述著作不綴,有許多年青人至今仍然跟隨他學習佛教,這位老人就是韓鏡清先生。在北京五月繁華似錦的日子里,我們在老人的住所對他進行了采訪,老先生精神攫爍,滔滔不絕地向我們講述了往事……
記者:韓老,據我們所知,你在上中學時就開始接觸佛教,以后又跟湯用彤先生、韓清凈、歐陽竟無、周叔迦等名師學習佛教,你覺得從他們那里學到的最大的收獲應是什么?
韓鏡清:我是1912年10月生于山西沁縣一個原藉北京的官僚家庭。其實當年我在北京四中上高中時最注意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世界哲學史、人生哲學的課。那時的中學就像上大學的預科,設有很多專科的學習課程,對這些課程我都表示出很大的興趣。那時我的思想也比較活潑,不但對哲學、文學情有獨鍾,而且也學習法文、日文、英文等,并且也就在此時,我開始決定讀北京大學哲學系,哲學是談人生宇宙的學問,佛教是屬于人生學里的一種,從那時我就接觸了佛教。我拜著名的常惺法師為師開始,取法名慧清,上大學后就以此為號。但我受他的影響不大,主要是通過閱讀佛教書來學習佛教。
那個社會的人們都或多或少地有些佛教的信仰,我父親就是如此,但我受家庭的影響也不大。父親有一位朋友曾經留學日本,叫王敏公,他信仰佛教,曾經向我介紹了一些佛教的知識。我剛開始學習佛教時是對禪宗感興趣,因為當時這一宗派最有影響,寬街大佛寺有一個流通處,我常到那里去買一些禪宗的書來讀,有時也買一些法相宗的書看。高中時代我比較關心人生宇宙的問題,于是對法相唯識的書漸漸買的多一些了,我之所以要讀北大哲學系,其原因也是在此,總之,是我自己去尋求佛教的知識,我印像中買的第一部佛經是《大乘起信論》。
當時的佛學界有南歐北韓兩家,但他們對我的影響都是間接的,不是主要的。歐陽竟無的書我看了不少,南京的支那內學院在學術界影響比較大,湯用彤、梁淑溟等人都與內學院有關系,當時學術界比較認同的是南方的歐陽。七七事變時,歐陽在南京講《晚年心得》,很多人都到南京,我隨湯先生、蒙文通先生一起到南京,聽了好幾天的課。此前我只是讀過他的書。所以我是私淑歐陽先生。在大學期間我曾聽過韓清凈先生講因明,后來聽《緣起初勝法門經》等。韓清凈在日本人占領北京時曾開過講經會,討論佛教,我曾經去聽過,他對我的影響要多一些。韓先生的書主要是三時學會出版的,我也買了不少,這些書一直保存下來,但是前幾年被香港法相學會的人拿去了。
1932年我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北大各種思潮都流行,對佛教而言,尤其是關于佛教大小乘翻譯的東西講的很多,特別是湯用彤先生拼命把東西方的哲學里只要能夠見到的,就盡量講出來,這是比較難的東西,因為漢文翻譯的也不是很好,不一定能懂。這種風氣對我影響很大。熊十力先生這時也在北大講新唯識論,其態度很明朗,他跟錢穆、蒙文通、湯用彤等幾位先生每隔幾個禮拜就要在熊十力家碰一次頭,討論學術,熊十力先生講中國哲學時的聲音很大,他有時需要一些佛教的資料時,還是由我來提供,例如《新唯識論》,我就曾經幫它出版。我現在保留的書里還有他拿粗筆大批大劃的痕跡。
1936年畢業后我繼續從湯用彤老師讀研究生,又在北京大學史學研究所研究佛教史。第二年他到南方西南聯大,我因家里父母年事已高,就沒有去。這時周叔迦先生也在北大教書,指導我學習大乘佛教。他要我學習藏文,因為他認識一些藏族喇嘛,請他們教我,此外每月還資助我經費,在生活上幫助我,于是我在他的鼓勵下開始我學習藏文,同時在一起學習的還有王森先生,但他對梵文的興趣比我大。自從這時學習藏文后,直接影響了我的后半生。畢業后我曾在私立中國大學哲學教育系、中國佛教學院任教,又在華北居士林及菩提學會從事研究與編輯工作。抗戰勝利后在天津南開大學哲學教育系任教。1949年我在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研究藏語。1952創建中央民族學院時調到少數民族語文系藏語教研組。1950-1953年和1956-1957年先后參加中國科學院西藏科學工作隊語言組和民族語言調查工作隊,兩次入藏進行語言調查和編寫藏語講義。1965年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新組建的世界宗教研究所,直到退休。
記者:在當代中國,有人稱王恩洋先生是專治唯識學的人,但根據我們的了解,你也是只從事唯識學的人,而且尤其對藏傳佛教的唯識學(正確地稱呼是瑜伽行派或有宗)鉆研很深,為什么你要選擇這門學問?
韓鏡清:實際上我在學校沒有人真正講過玄奘法師的唯識學,倒是聽了熊十力的新唯識學,梁漱溟寫過《東西方文化哲學》,牽涉到唯識學問題,當時書是看了,但他已經不在北大了。我在大學寫的畢業論文是《阿賴耶識的由來》。為什么選擇這個題目?恐怕是自己學習的一種設想。把小乘里接近阿賴耶識的說法弄些材料來解剖,當然這時對真正唯識學還是不理解的,到現在才有些地方理解的比較清楚,這也是個過程吧。后來做湯用彤先生研究生,第一學期論文是《凈影八識義述》,有點批判的味道,對佛教唯識學有一點認識。總之正面的唯識學恐怕是我自己學的。課堂沒真正講唯識學。研究生第二學期論文是《大小乘身表業異解》,直接引用頗婆沙翻譯的經論,重要理論是生必有因、滅不待因。
我父親、兄長對同善社、扶乩很信,但它沒把我抓住。我看過佛教的東西不少,尤其現在流行的重點,如禪宗、《起信論》等,一般人都注意,也影響了我,但都沒有引起我特別注意,還是看唯識學的書比較多。如要分析,就是一個原因,當時出版界有南歐北韓的研究,東西不少。這個對我大概有些影響。
我也奇怪,為什么非抓住唯識學不抓別的?對真諦,尤其玄奘法師抓得那么緊,幾十年沒懈怠。1977年元月我退休后開始了第二個閉關時期,集中精力閉門整理《成唯識論》所有疏注,對《成唯識論述記》進行校勘、補充和注釋,至1992年編成240萬字的《成唯識論疏翼》。同時從藏文大藏中翻譯有關慈氏學及因明等方面重要典籍至今已有60余種。而且還寫了《成唯識論疏翼》。
記者:本世紀上半葉在佛學界對唯識學的爭論很激烈,當時歐陽和太虛就唯識法相是一家還是二家,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而你在近年來又對唯識學提出了又一種看法,認為唯識學應是唯了別識學,還提出了慈氏學的概念,請你簡單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韓鏡清:中國佛教首先是個翻譯問題,我們看到的佛陀的言教就是一些譯師從梵文翻過來的漢文,翻譯如果不準確會直接影響到整個佛教的認識。梵文中有兩個詞都被漢地譯師譯為“識”字,一個是講八種識體時專用的Vijn~āna(辨別識),一個是講“唯識”時使用的Vijn~apti(了別識),而在藏譯中兩詞是分開譯的。Vijn~āna(辨別識)是在內外六處兩種色法之間能起的一種辨別作用,很明顯是有能辨別、所辨別兩個方面;而Vijn~apati(了別識)則是講所有的東西都是“分別”或“遍計”,除此之外并沒有所緣境界的存在,只能說在緣起上有能而無所,沒有能所兩個方面的問題。兩者如果混淆起來,唯識學的內容就不同了。
了別識是阿賴耶識種子的顯現,它只有能顯現,根本沒有所顯現的東西,即“唯識無義”,無義就是沒有人我、法我,沒有能取所取,就是沒有自性,沒有凡夫所面對的現實,也就是無我、無常。辨別識承認色根、色境,而了別識是把境界包括在內了。唯了別識,就是只有一個整個的能顯現,其中無所、無義,就是徹底解決所取能取的問題來證真如。世親在《唯識三十頌》里明確講,只有能分別,沒有所分別。在《唯識二十論》中也說得很清楚,提出辨別識是為解決人無我的問題,解決法無我問題就必須要講唯了別識。唯識學不能是唯辯別識,奘譯《唯識三十頌》中第一頌翻譯有誤。辨別識指根境所用,是感性認識。色法離不開根,離不開境,離不開心的顯現。色法受形色的限制,形色是假法。了別識則依他起法是緣起法。大乘不承認遍計所執性,不承認離開依他起而存在的色法,大乘認為所有的存在沒有自性,人們常常認為依他起之外的自性,本性就存在,而此為大乘根本不承認的。大乘經論提到阿賴耶識很重要的頌文都不少,不研究阿賴耶識沒法弄清人生宇宙是怎么回事,怎么死了又生……,里頭是不是有靈魂?根本沒這回事兒,就是阿賴耶識。阿賴耶識還關涉到自然界,不只是內部問題、主觀世界的問題,客觀世界整個跟阿賴耶識有關系。等流因,異熟果,增上因問題都跟阿賴耶識有關系。
?我認為從藏文慈氏學來開發真正的唯識學。這是代替古今中外,全面重新認識唯識學的有效途徑。我所說的慈氏學,是指依印度無著大師的五種著作而建立的學說,因為它是我們了解唯識學的根本所依,只有對慈氏學的根本問題真正看懂、真正理解,才真正能翻譯大乘經典。1993年9月我倡導成立了慈氏學會,從事慈氏學經典的翻譯、校注、研究和出版等工作。
記者:改革開放以后,國內的佛學開始繁榮起來,作為老一輩的學者,你在這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翻譯了不少著作,培養了不少學生。從世紀的眼光來看,你覺得這個世紀的佛學研究應該怎樣評價,未來的佛學研究會朝哪方面發展?
韓鏡清:過去佛學發展有很大的問題,可以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文字結構方面。一是理論結構方面。前者主要在翻譯上出現了問題,后者是對教義的解釋上有問題,所以必須把過去錯誤有所更正。才能使大乘佛教重新興起于世界。
?在亞洲國家,日本比較注重歷史、梵文的研究,并在這兩方面對中國的佛教研究有過影響。但是日本的佛教根本上還沒有離開中國的佛教,仍受中國佛教的影響。日本對真正大乘佛教理論并沒有真正認識,現在大乘佛教真正理論在慈氏學開發上,應該注意三自性,什么是遍計、依他、圓成等問題,必須嚴格認識清楚。歐陽大師《晚年心得》講了兩句話:“萬事東風吹馬耳,一園春色寄猿心。”諸法有它獨到的地方,大氣滂薄,有氣魄,對學問歐陽有特別的見解,兩句詩說明什么事都跟□心有關系。古人有修養的,像王陽明、諸葛亮等“非談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與后來禪宗大師不在之下。對大眾來說,什么是有,什么是無,必須尋求一個最后的解決不可,所以重新好好認識三性的問題。不要隨便談,因為隨便談很容易把有無的概念弄亂了。從我的認識來看,中國佛教的第三個一千年最重要的仍是開發慈氏學。